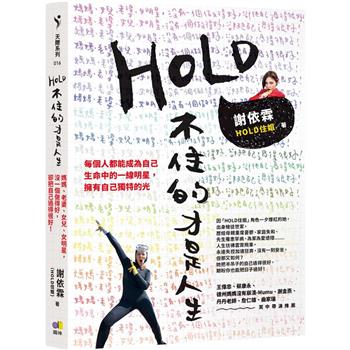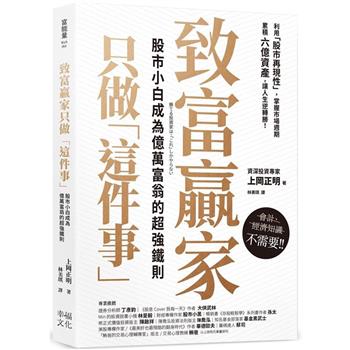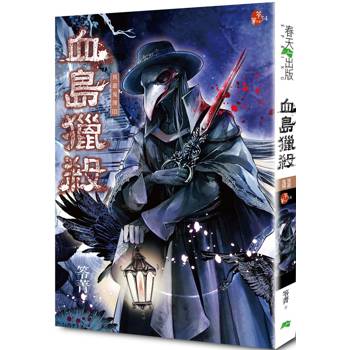序
最近常寫序,大都還是為學術性的專書寫,也都算是和自己專業有關。要替女兒這本書寫序,就總是覺得筆調可能不會很順。不只因為這不是一本學術著作,更因為她寫進書裡的是那種深刻而微妙的祖孫情思,我在母親和女兒深情渦流中若隱若現,有時候就有搭不上又得搭上的奇妙。習慣用艱硬的筆寫學術著作的序,就難得為靈動的文學作品說什麼。但筱葳的流浪是循我母親七十年前的蹤跡而行,又特意去探訪我出生的地方,我自也不能在這本書缺席。
一九八六年我到美國維吉尼亞大學講學,下學期就接正在念小學最後一年的筱葳去遊學。回程全家遊歷佛羅里達、路易斯安那、達拉斯,再經鳳凰城到大峽谷。在大峽谷山崖邊,鼓勵筱葳寫遊記,她沒有回應,我開玩笑說二十年後請我們重遊大峽谷,她答應了。結果遊記還是沒寫半個字。二十年後,我去荷蘭萊登大學講學,既然大峽谷沒去成,就說既然她前幾年去過挪威峽灣,就帶我們去峽灣吧。小姐終於也沒請我們去,倒是我們自己去了。從大峽谷到峽灣,景色壯麗,終究寫不出什麼。然而這一趟追尋奶奶的足跡流浪了三個月,是有探尋的,有深深的祖孫和家族情誼牽連著,每到一處就有感觸,自然要寫出來。果然筱葳有話要說,而且非說不可。
讀完全書,包括媽媽的食譜,深深覺得筱葳寫的是情,不是在寫景。三個月流浪的主要目的不是遊覽山川名勝觀賞風景,而是尋尋覓覓找奶奶的蹤跡和味道,是整理與奶奶三十多年的情,試著將這整個情昇華編織成文,永存起來。
筱葳和奶奶情深如此,當然和我們為留學而把她留給她奶奶照顧有關。她出生才三十四天,我就去美國留學,她還剛滿一歲半,她媽也去美國幫我念博士學位。這一去就四年,她成了典型的「阿媽子」,從出生到會說話懂事,父母大多不在身邊。本來在華人社會祖輩就特別疼愛孫子女,嚴父慈母總是管教者。可是在我們家,由於在女兒最重要而關鍵的銘刻認同時期,我們多不在,奶奶對孫女就更特別寵愛和親密了。到母親走了,筱葳必須整理整理和奶奶的情。在《留味行》中,她和七十年前的奶奶同行,我們深深為筱葳在書中流露出和奶奶的深情震動。
媽媽離世前幾年,我利用每天中午吃母親做的幸福午餐的飯後時間,做了口述歷史訪談錄音,整理出十多萬字的書稿。後來羅久蓉博士摘錄五萬字左右收入中研院近史所出版的《烽火歲月下的中國婦女》一書。這個口述歷史的簡本就成了逝世紀念冊《留雲遊蹤──瞿媽媽一生的故事》的主文,也就是這一小冊子的口述歷史引發及引領筱葳循著奶奶的蹤跡去流浪了三個月。《留雲遊蹤》當初印了三百本在追思會上差不多全送掉了,好多朋友讀了都覺得很感動,最近還有朋友特地寫電子信說她母親讀了也頗有感覺,也許是有很近似的流亡苦難經驗吧!那本書不太可能出版,筱葳說她會放在部落格(ipaway.org)上,把奶奶的口述歷史配上新的圖片。在網路時代,這也是一個很好的辦法。看了《留味行》,可能有讀者對奶奶當年的遊蹤感與趣,就可以上網探個究竟。
瞿海源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作者父親)
自序
大世界的哈哈鏡
上海南京路的大世界戲院有一面哈哈鏡,站在面前瘦的變胖,凹的變凸,哭著像笑。七十幾年前你可以在那鏡子前看著自己哈哈大笑,花花世界無奇不有。如今大世界整棟建築蒙上了綠布關閉了,你走近了只有灰塵,連乞人都繞路。
我的旅程接近尾聲的時候終於到了這個不再歡樂的建築外,整個城市為了「世博」醞釀著,世界想看看新的上海會是什麼模樣,走在南京東路上我發現只有我。
年長的總想退休後環遊世界,年輕的想要遠遠甩開這個世界去看那個世界,或者只在生活的島上繞一圈,彷彿走出去就可以擁有新的鏡子,看見新的自己。在原來的世界看不見找不到的,在失落的鏡子裡都可以尋得,竟像真的一樣。旅行是魔鏡,我們都這麼希望著。
甚至已經離世的奶奶都想旅行,我夢見過兩次。
奶奶在小島上,很清閒的想要打電話,猜測是要撥給我的,可手機太小老人家不會用,就這麼折騰著。島上的風很緩慢,撥手機的動作也不快,一直無法撥成,老人的手指這麼纖細那麼靈活卻不會撥電話,我在夢的這頭看著她乾著急,沒法可想。她要告訴我她很好,夢裡她沒說卻傳達出如此訊息,我朦朧知道她的意思。她要說,她上路了,就在旅程上。旅行有點趣味,她真的很好別擔心。
於是我偶而會忘記她已離世。也許是因為她總沒有打電話來告訴我,她已經離開。
另一天早晨醒來,沒有夢見老人,卻有一個清楚的念頭進入腦袋:「該去走一趟奶奶逃難時走過的路」。念頭很清晰,就是以一句話的形式出現在早晨的夢霧中。前人已上路,我也該上路,無論那路途是什麼,就去走老人走過的路吧。
過世數月的奶奶只留下了一本薄薄的口述歷史,我卻從來沒仔細讀過。爬出被窩,我開始想該怎麼做。早春還很冷,需要出走的熱度卻在心裡像夏天的太陽開始發熱。也許在途中,會遇見小島上的奶奶,路途上的奶奶,或者是夢中的奶奶,把夢外的自己放進夢裡走一回。
想要離開這裡,去遠方,沒那麼多理由。說穿了眼前就是日子復日子,你得去走一趟。去找答案,去問你從哪裡來,要到哪裡去。或者,其實是去找到正確的提問,叩問自己心中真正的思念。
只有一張地圖和一本口述歷史,就要上路了嗎?那到底是什麼樣的一段路程?你期待旅行能帶來什麼嗎?而到底,為甚麼要在七十年後重新去走這趟路呢?難道你以為七十年還會留下什麼痕跡嗎?上海那面照映過老人青春歲月的哈哈鏡,如今早已不在,你當真以為可以在站到涵納流轉歷史的鏡子前(歪曲的),再看見些什麼呢?
但我找不到理由退卻,因為我曾經犯下了一個錯誤。這個錯誤講出來也沒人在意,不講更沒人知道。
許多年前異想天開地對家人宣告我要拍攝紀錄奶奶的故事。這個計畫一直斷斷續續的進行,因為當時的我對於影片製作什麼也不懂,只有胡亂的熱情和衝勁。即使買了攝影機,也紀錄了不少片段,卻總摸不清頭緒如何剪輯。再過了幾年,拍片的朋友說了:「你現在沒事,乾脆來跟我學剪接吧。」算好了荷包儲蓄能承受的時間,像旅行一般上路了。每日像上工一樣去朋友的工作室剪著自己的小短片,如此開啟了拍片人生,轉進了影片製作的行業。當初想做的奶奶紀錄片卻因此也暫時擱下了。
終於著手開始剪輯奶奶的影片,是為了告別式而剪。奶奶在我最忙碌的時節,在睡夢中過世了。暫時擱下的,最後才知道那暫時擱下其實是永遠。她過世一週內,我匆匆讀過先前爸為奶奶做的口述歷史,把奶奶將近九十年的生命擠進十五分鐘的影片中。
影像成了魔法,在密集的剪接期中我盯著螢幕召喚奶奶的神魂。影片的播放是降靈會。一切的靈又因我們觀看而瞬間再現。
影片中一張奶奶逃難的路線示意圖,我特地做運鏡示意逃難方向。就在這張圖上,原本該是順時鐘方向的路線,硬生生被我拐成了逆時鐘。我把這旅途方向由上海一路往西,直達了四川。我讓奶奶走了錯的方向。原來奶奶說了上百次的逃難故事我始終充耳未聞,現在才發現那些故事我知道的那麼少,少到有一天你毫無防備的被自己的無知打了一巴掌。這一巴掌,杳然無形,卻沉沉落在心底。
歷史會讓人記著,人類拖著影子往前走,踩在腳下的都是歷史。但更多時候歷史不存在。
奶奶的故事不再出現我的生活中,一切像是大雨過後太陽揚起,地上又是一片爽朗,毫無雨跡。沒人再問起那逃難之路到底怎麼回事?
窩在早春的被窩裡就著檯燈看著奶奶的逃難路線地圖,手指過每一個老人青春時走過的城市。我可以如此用手指劃過千百回,猜測家中餐桌的某道菜很可能是她戰時流離之際學會的手藝,但我永遠不會知道她走過的路是什麼樣貌,我們吃的菜到底是哪一個地方的菜。除非我重新用腳走過,每一個她到過的城市,穿越每一個她走過的邊境,找到屬於她的味道,並且把味道留下來。於是找出了一張新的地圖,拿出紅筆開始圈出地名。就像賣火柴的小女孩,我想像點一根火柴可以見到逝去的奶奶,邁出的每一腳步,就是一根火柴,那閃爍短暫的光芒,或可讓兩界重逢,讓微弱的庶民歷史激起些許火花。
三個月最後走到上海,才知道大世界的哈哈鏡沒了,上海新認識的友人跟我說,蘋果電腦裡攝影自拍軟體有種效果就是哈哈鏡,打開電腦就有了,你特地繞了那麼大一圈來找?我對他笑了。他打開他的蘋果電腦,幾個人對著視訊攝影機擠眉弄眼,還是彩色的呢,電腦把我們變成了哈哈鏡中的可笑模樣。就這樣,在上海的黃埔江邊小宅裡,我照到了哈哈鏡。
但終究旅途並不是為了尋得那面鏡子,旅人慢慢懂得了,走在旅途中你就已經入夢了,成為鏡子裡的影子,成為古老故事的一部分,你是故事的延續。生死不是兩界,而是一條線。旅途的最終換來的是哈哈一笑。然後你會明白這不是為了思念,而是告別。在夢中在鏡子中重新認識老人以及那整個屬於她的時代,好好地記住,然後說再見。
後記
書的開頭提到,本來想為奶奶拍攝紀錄片,因為沒有做到才想透過旅行知道更多,用文字紀錄下來。其實,在紀錄片想法還沒展開之前,我還有另一項小計畫,就是要整理奶奶的食譜故事,想自寫自拍自畫自編自印,想像中是本小小的書,就是一篇篇食譜和我們自己拍的照片。這個計畫在網路出現之後,化成在自己部落格開一個分類放置這些食譜故事文章,便宜了事。那本食譜故事書就自我交差了。
等到這本書與編輯談定了,一直想的是把食譜故事依著記憶的地理地圖夾在旅途之中,我早就忘記當初想手作的那本簡單的只有食譜和圖片的小書。直到截稿那一天,姑姑和表姐說,那天是奶奶農曆生日,我無奈地說但我沒空上山給她上香,只好在家裡趕稿紀念她。下午,接到編輯來電,說他與美編感覺可以把文字與圖片拆成兩本製作,文字收了所有旅行文章,圖片那本則加上食譜故事編成彩色一本。當下我很喜歡編輯的決定。
第二天醒來,我更發現按照編輯的作法,如此我們就有了一本當初我想做卻沒有做的一冊食譜故事書。十年前想像的那本食譜故事小冊子,在我早已忘記當初的小計畫許久以後。
很多事情最後都會回到初始的原點,一個心意剛剛萌芽的樣貌,再繞回你眼前,讓人照見自己。經過將近十年延宕,那個想像竟然變成實際的面貌出現,此時已過萬重山,能夠帶著一切變化回到原本的心,是一種福氣。
這也是給奶奶的生日禮物,十年前的小心意演變至今,變成眾人的努力,化解了我的惰性,終於成冊。在能開電腦書寫之前,已經打過多場自我內心戰,既害怕直接面對逝去的生命又不願放過自己。在這段面對生死課題的時間裡,大安社大的老子課同學們以及夏惠汶博士(我們都稱夏杯杯)的陪伴,是很大的支持。花蓮的蘋蘋阿姨一家願意不時收留我,知道有時朋友不需要說話,只需要一起吃吃飯,聽聽太平洋的聲音。有陪伴老人經驗的寶鍊跟我分享心情,我們各自懷念與老人家相處的時光。然後在自立互助會晏珊、文綺、冠宇的督促下,才產出了首批稿件。
書有大半是在奶奶原來的臥室寫就,她也在這房離世。奶奶走了之後大床撤走後,搬進了大書桌,變成我的工作房,工作書寫都在這裡。一開始她經常入夢,隨著時間過去越寫越多,我獨自寫到哭寫到笑,她入夢的機率變少了,我明白時間到了,透過旅行與書寫漸漸長大,有了新的方法記憶過去,奶奶也放心走了。
思考書名的時候,與家人編輯討論良久,沒有定論。終於有一天,我突然想到,奶奶的名字「留雲」多麼美,多有情。雖然雲無法留住,味道總可以吧,我的旅行也正是想要尋找並留下味道的一趟旅行,取其「留」意,就有了「留味行」三個字。不僅留住味道,也用書名記憶奶奶的名字。
大家都問,出去前後變了嗎?旅行的人彼此詢問,留在原處的人也問。回到生活,一切都變了又一切都沒變。在離去與返回的這段缺口改變的人事物,並沒有因為你不在而強度削減。而獨自行走時的歷程,對別人來說也都是缺口。「你到底看見了什麼?感受了什麼?改變了什麼?最喜歡哪裡?你還是不是原來的你?」
我很難回答這些問題。
旅行或寫作,都只是為了拖時間。拖慢人會淡忘的慣性,想讓自己多知道一些關於祖輩的過往,能夠記憶深一點長一點。旅行過程在東張西望,希望吸飽了故事帶回家蒸餾出幾滴陳釀;寫作的過程中,也是東張西望,只要看到一丁點相關的書籍、故事、照片,都興奮的不得了。但這些,也只能讓我稍微接近老人家老故事。人能夠與更大的歷史譜系連結,意識到在時間空間中自己渺小的位置,再回到現實生活小世界裡,人還是會有些變化。最大的變化,就是接受了死亡也是自然。在旅途中的放空之後,終於心裡空出空間,能有餘裕地看待這些原本自然的事情。
奶奶過世當天早上email告訴一位老友蕭大哥。蕭是位編劇,當時已經搬回台東種菜,像大哥又像叔叔,是一位重要的朋友。他不多久回覆一封不算短的信,其中幾句當下安定了我:
「然最要緊的還是你
聽聞間似你與她最密切
那就是你送她囉。
關於我想說的生命
是因為有種切膚之痛
那人不是因為死而消失
而是我們看不見」
是的,是我們看不見。但死亡並不是消失,在之後的三四年內,我深切的體會。所有片片段段,路上的、過往的、新的老的記憶,都重組交織被書寫成新的故事。這樣,我們就可以重新看見了吧。
信裡蕭大哥還有一句,我從此記在心裡,也是帶在路上不忘的話:
「彼此都在流浪。
親之再親,都只擦肩而過。」
在更大的時間裡,一輩子的相處也只是擦肩。我們先來後到,都是旅人。而我的旅行與書寫,無非就是想延長這擦肩的細節與感受。如果幸運,有人讀了有些感受,也回去珍惜自身的擦肩緣份。而最幸運的是我,我因此有了專心書寫專心做菜的一段時光。
老人家煨著小火的爐子,終於熄了。
該我點上爐子,繼續煨一鍋暖暖的好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