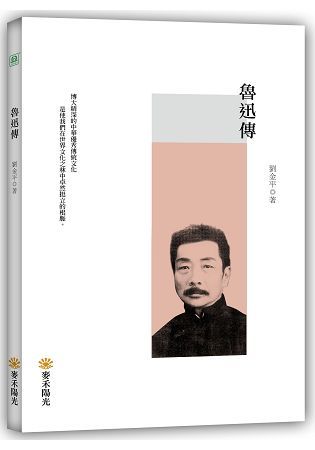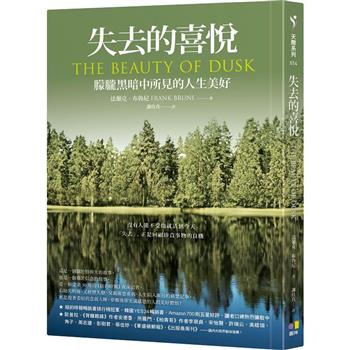一、紹興:黃金世界和在人間
有誰從小康之家而墜入困頓的麼,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
——魯迅《呐喊•自序》
在我們每個人的生命過程中,總會有許許多多個這樣的時刻:它們與我們相距遙遠,以至於在很長的時間裡我們都對其一無所知;然而,它們卻以對時代氛圍的深刻展露沉澱了下來,最終共同編織成了某種命運交響曲;也許唯有在我們的生命終結之後,後來者的目光才能穿過漫漶的歷史煙雲,洞察出它們之於我們的全部意義。
而對於魯迅,1881年便可以成為這樣的一個時刻,而且關乎源起,儘管對動盪不安的整個中國近現代史而言它似乎並無多少值得特別書寫之處。這一年發生的大事屈指可數:
首先在西北,通過二月與俄國簽訂的《伊犁條約》收回了被強占的伊犁[此处插图,图注:魯迅],這是中國步入近代以來少有的一次軍事和外交勝利;
繼而在西南,中法在越南關係日趨緊張,終於在兩年後釀成戰爭;
最後在華北,唐山至胥各莊的運煤專線開通,它也成為了中國自辦的第一條鐵路,背後則是清中央政府和一些封疆大吏掀起的洋務運動。
由此,一幅粗線條的近代中國圖景現身了:一方面是外人入侵,禍起四境;另一方面則是一代代志士仁人前仆後繼、殫精竭慮的自救嘗試。
然而這樣粗線條的寬幅圖景終究也只能作為遠景,作為一顆多年後才能顯示出其深刻意義的楔子。如果我們將鏡頭橫移,聚焦於浙東古城紹興的新台門周家,近景無疑是一個普通中國仕宦人家的欣喜——這一年的9月25日,周家大公子降生了。這種欣喜是很可理解的,因為在傳統社會,只有男丁才能帶來延續家族榮光的希望,正像在古老而躁動的華北大地上奔馳的第一列中國人自己的火車那樣——這個男孩,終究也將成長為新時代的火車頭,帶著他命運中所有的顛沛和曲折驅馳而去。
男孩的祖父周福清正在北京做官,消息很快報送過去,他便以當時拜訪自己的一個朋友的姓氏給長孫命名為“阿張”,隨後又找了一個諧音字命名為“樟壽”。不管如何,這畢竟是個有著美好寓意的名字:像樟樹般盛大而長壽。於是,小樟壽便在紹興城一天天成長起來。
紹興是一座有點兒古怪的城市。堯舜的王道事業和勾踐的臥薪嚐膽是這片土地上流傳著的最早傳說,王羲之和他的朋友們也曾在這裡流觴曲水,不過這些都已是久遠幽緲的往事了。風流俱散,到了魯迅出生的時代,紹興名聞全國的是兩樣特產,一是師爺,二是黃酒,它們深刻影響了魯迅祖父和父親的性格,也構成魯迅自身獨特的故鄉體驗。
明清兩代,雖有其他地方的讀書人也做師爺的,不過最出名、規模最大的卻是紹興人。職業特色漸漸融入了當地的文化基因中,也形成了冷峻、尖刻的文風和多疑、善罵的性格,這一點從徐渭、張岱、章學誠等人身上都可以看出。周福清正是這樣一位愛罵人的老人,對外是恃才傲物、滿腹牢騷,對家裡人則經常毫無遮攔地破口大罵。比如他常說夢見什麼人反穿皮馬褂來告別,意思是說那人死後要變成豬羊;又曾說這人後來孤獨窮困,老了只能在一處後悔——這是更為惡毒的,因為古代文人描寫“冥土旅行”說閻王給極兇惡之人的判罰是不給孟婆湯,讓他坐在地獄裡回憶過去的榮華與威力,這刑法是比火燒和狗咬更為殘酷的。小樟壽固然聽不懂其中太多深意,但祖父的威嚴和憤怒還是能體味出來的,因此對這位老人也就多少藏有了幾分畏懼。不過,從小盡力逃避卻難免耳濡目染的這些尖刻和怨恨最終還是化為一股潛流留了下來,構成了日後他多疑、尖銳文風的最初源頭。
祖父因京官的身分較少居家,父親周伯宜是一直在身邊的,卻也同樣不好親近。現在看來他的形象已頗為模糊,只知道性情沉默,卻嗜好喝酒,常常一個人喝悶酒。這酒不是我們現在常喝的經過二度蒸餾的白酒,而是果酒,可以多飲而慢醉。紹興黃酒在果酒中又以清冽悠醇而標格獨出,既沒有葡萄酒的膩味也沒有高粱、大麯的辛辣,是很陶醉人的,也可見父親大概不像祖父般狷介張揚。紹興人大多好酒,魯迅後來的文章中常常寫到小酒店的情趣:無論咸鹹亨或德興,大抵是一間門面,靠牆的櫃子上放些酒瓶,門口是曲尺形的櫃檯,上設半截柵欄陳列各種下酒菜,店的後半是雅座,也不過就是些狹板桌條凳罷了;這些千篇一律的小酒廊,卻是下層讀書人和各種引車賣漿者流的好去處。當然,還有歸鄉的遊子。與父親和同鄉人一樣,魯迅也是好酒的,雖然酒量不大。他後來在《在酒樓上》寫自己上了一石居,叫堂倌來“一斤紹酒,十個油豆腐,辣醬要多”時,是否會理解自己幼時不敢親近的父親呢?同樣的沉默而苦悶,他來到了父親的年紀。
如果說關於祖父和父親的記憶大多是苦澀,那麼童年裡祖母蔣老太太、母親魯瑞帶來的就是純粹的愛的滋養了。蔣老太太溫和、慈祥,更要緊的是會講故事。到了夏夜,小樟壽就常常躺在院落裡那株大桂樹下的小板桌上乘涼,祖母搖著大蒲扇坐在桌旁,於是期待中的故事會便開始了。有時候桂樹上會突然傳來沙沙的趾爪的爬搔聲,抬頭便看見一對閃閃的眼睛,使人暗暗吃驚。於是祖母就開始講“貓是老虎先生”的故事了。傳說中那老虎本來是什麼也不會的,就投到貓的門下拜師學藝。貓把撲、捉、吃的方法都教了它,於是老虎想,本領都學會了,只有老師比自己強了,於是要殺掉貓。待它撲向貓的時候,貓卻一跳上了樹——原來它早料到徒弟的叛逆,獨獨沒教它如何爬樹,於是老虎便只能蹲在樹下了。“這是僥倖的,幸而老虎性急,否則從桂樹上就會爬下一隻老虎來。”小樟壽想。不過這故事還是令他害怕起來,於是竟急著要進屋睡覺去了。
除了貓的徒弟老虎,“水漫金山”也讓小樟壽不安。白蛇娘娘和許仙的一段奇情本是多可讚美呀,那法海和尚偏要放下經卷,橫來招是搬非,將白蛇娘娘裝在一個小小的缽盂中,還在上面造起一座鎮壓的雷峰塔來。從此,法海的殘忍和白蛇娘子的淒慘命運都像那座重重的雷峰塔壓在了心頭。他雖然還不太懂得多少封建禮法之類的抽象概念,心中的悵惘和仇恨卻是足夠的。很長一段時間裡他唯一的希望便是那雷峰塔的倒掉。後來他從大舅父那裡得到了一本彈詞《白蛇傳》,不出幾天裡面法海繡像的眼睛就叫他用指甲掐得稀爛。
他也有極愛的故事,便是那“老鼠娶親”,從新郎、新娘到賓客、執事,沒有一個不是尖腮細腿,像煞了讀書人,卻穿著紅衣服、綠褲子,實在是可愛。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魯迅傳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55 |
中國近代史 |
$ 299 |
華文文學人物傳記 |
$ 299 |
華文文學人物傳記 |
$ 306 |
中國近代史 |
$ 306 |
傳記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魯迅傳
魯迅這個名字,曾經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語文課本上出現過,讓人熟悉了他的“橫眉冷對千夫指”,學習了他的“俯首甘為孺子牛”;過於熟悉,反而容易視而不見,過於親切,反而喜歡略過不談,對我們來說,他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魯迅先生之偉大,在於一貫地為真理正義而倔強奮鬥,至死不屈,並在於從極其艱險困難的處境中,預見與確信光明的將來。
作者簡介:
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壽,後改名周樹人,字豫才,後改為豫亭,浙江紹興會稽縣人。“魯迅”是他1918年5月發表中國現代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時首次使用的筆名,此後成為他最廣為人知的名字。
TOP
章節試閱
一、紹興:黃金世界和在人間
有誰從小康之家而墜入困頓的麼,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
——魯迅《呐喊•自序》
在我們每個人的生命過程中,總會有許許多多個這樣的時刻:它們與我們相距遙遠,以至於在很長的時間裡我們都對其一無所知;然而,它們卻以對時代氛圍的深刻展露沉澱了下來,最終共同編織成了某種命運交響曲;也許唯有在我們的生命終結之後,後來者的目光才能穿過漫漶的歷史煙雲,洞察出它們之於我們的全部意義。
而對於魯迅,1881年便可以成為這樣的一個時刻,而且關乎源起,儘管對動盪不安的整個中國近...
有誰從小康之家而墜入困頓的麼,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
——魯迅《呐喊•自序》
在我們每個人的生命過程中,總會有許許多多個這樣的時刻:它們與我們相距遙遠,以至於在很長的時間裡我們都對其一無所知;然而,它們卻以對時代氛圍的深刻展露沉澱了下來,最終共同編織成了某種命運交響曲;也許唯有在我們的生命終結之後,後來者的目光才能穿過漫漶的歷史煙雲,洞察出它們之於我們的全部意義。
而對於魯迅,1881年便可以成為這樣的一個時刻,而且關乎源起,儘管對動盪不安的整個中國近...
»看全部
TOP
目錄
引言 …III
一、紹興:黃金世界和在人間 …001
二、南京歲月 …026
三、別求新聲於異邦 …041
四、囚徒 …071
五、鐵屋中的吶喊 …093
六、孤獨者 …130
七、到南方去 …155
八、最後的橫站 …170
延伸閱讀 …189
魯迅先生年譜 …211
一、紹興:黃金世界和在人間 …001
二、南京歲月 …026
三、別求新聲於異邦 …041
四、囚徒 …071
五、鐵屋中的吶喊 …093
六、孤獨者 …130
七、到南方去 …155
八、最後的橫站 …170
延伸閱讀 …189
魯迅先生年譜 …211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劉金平
- 出版社: 麥禾陽光 出版日期:2017-07-26 ISBN/ISSN:9789869496018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06頁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華文文學人物傳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