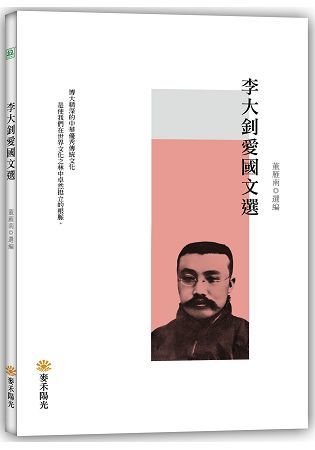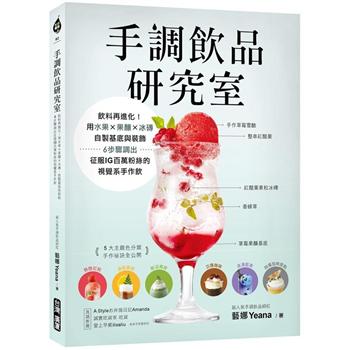法俄革命之比較觀
俄國革命最近之形勢,政權全歸急進社會黨之手,將從來之政治組織、社會組織根本推翻。一時泯棼之象,頗足致覘國者之悲觀。吾邦人士,亦多竊竊焉為之抱杞憂者。余嘗考之,一世紀新文明之創造,新生命之誕生,其機運每肇基於艱難恐怖之中,徵之歷史,往往而是。方其艱難締造之初,流俗驚焉,視此根本之顛覆,乃為非常之禍變,抑知人群演進之途轍,其最大之成功,固皆在最大犧牲、最大痛苦之後。俄國今日之革命,誠與昔者法蘭西革命同為影響於未來世紀文明之絕大變動。在法蘭西當日之象,何嘗不起世人之恐怖、驚駭而為之深抱悲觀。爾後法人之自由幸福,即奠基於此役。豈惟法人,十九世紀全世界之文明,如政治或社會之組織等,罔不胚胎於法蘭西革命血潮之中。二十世紀初葉以後之文明,必將起絕大之變動,其萌芽即茁發於今日俄國革命血潮之中,一如十八世紀末葉之法蘭西亦未可知。今之為俄國革命抱悲觀者,得毋與在法國革命之當日為法國抱悲觀者相類歟。
或者謂法人當日之奔走呼號,所索者“自由”,俄人今日之渙汗絕叫,所索者“麵包”。是法人當日之要求,在精神在理性之解放,俄人今日之要求,在物質在貪欲之滿足。俄人革命之動機視法人為鄙,則俄人革命之結果,必視法人為惡。且在法國當日,有法蘭西愛國的精神,足以維持法蘭西之人心。而今日之俄國無之,故法人雖冒萬險以革命,卒能外禦強敵內安宗國,確立民主之基業,昌大自由之治化,將來俄人能否恢復秩序,重建組織,如當年法人之所為,殊為一大疑問。不知法蘭西之革命是十八世紀末期之革命,是立於國家主義上之革命,是政治的革命而兼含社會的革命之意味者也。俄羅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紀初期之革命,是立於社會主義上之革命,是社會的革命而並著世界的革命之彩色者也。時代之精神不同,革命之性質自異,故迥非可同日而語者。法人當日,固有法蘭西愛國的精神,足以維持其全國之人心;俄人今日,又何嘗無俄羅斯人道的精神,內足以喚起其全國之自覺,外足以適應世界之潮流,倘無是者,則赤旗飄飄舉國一致之革命不起。且其人道主義之精神,入人之深,世無倫比。數十年來,文豪輩出,各以其人道的社會的文學,與其專擅之宗教政治制度相搏戰。迄今西伯利亞荒寒之域,累累者固皆為人道主義犧牲者之墳墓也。此而不謂之俄羅斯人之精神殆不可得。不過法人當日之精神,為愛國的精神,俄人之今日精神,為愛人的精神。前者根於國家主義,後者傾於世界主義;前者恒為戰爭之泉源,後者足為和平之曙光,此其所異者耳。
由文明史觀之,一國文明,有其暢盛之期,即有其衰歇之運。歐洲之國,若法若英,其文明均已臻於熟爛之期,越此而上之進步,已無此實力足以赴之。德之文明,今方如日中天,具支配世界之勢力,言其運命,亦可謂已臻極盛,過此以往,則當入盛極而衰之運矣。俄羅斯雖與之數國者同為位於歐陸之國家,而以與上述之各國相較,則俄國文明之進步,殊為最遲,其遲約有三世紀之久。溯諸歷史,其原因乃在蒙古鐵騎之西侵,俄國受其蹂躪者三百餘載,其漸即長育之文明,遂而中斬於斯時,因復反於蠻僿之境而毫無進步。職是之故,歐洲文藝復興期前後之思想,獨不與俄國以影響,俄國對於歐洲文明之關係遂全成孤立之勢。正惟其孤立也,所以較歐洲各國之文明之進步為遲;亦正惟其文明進步較遲也,所以尚存向上發展之餘力。
由地理之位置言之,俄國位於歐亞接壤之交,故其文明之要素,實兼歐亞之特質而並有之。林士論東西文明之關係,有曰:“……俄羅斯之精神,將表現於東西二文明之間,為二者之媒介而活動。果俄羅斯於同化中國之廣域而能成功,則東洋主義,將有所受賜於一種強健之政治組織,而助之以顯其德性於世界。二力間確實之接觸,尚在未來,此種接觸,必蓄一空前之結果,皆甚明顯也。”林氏之為此言,實在一九○○年頃。雖邇來滄桑變易,中國政治組織之變遷,轉在俄國革命之前,所言未必一一符中,而俄羅斯之精神,實具有調和東西文明之資格,殆不為誣。原來亞洲人富有宗教的天才,歐洲人富有政治的天才。世界一切之宗教,除多路伊德教外,罔不起源於亞洲,故在亞洲實無政治之可言,有之皆基於宗教之精神而為專制主義之神權政治也。若彼歐洲及其支派之美洲,乃為近世國家及政治之淵源,現今施行自由政治之國,莫不宗為式範,流風遐被,且延及於亞洲矣。考俄國國民,有三大理想焉:“神”也,“獨裁君主”也,“民”也,三者於其國民之精神,殆有同等之勢力。所以然者,即由於俄人既受東洋文明之宗教的感化,復受西洋文明之政治的激動,“人道”、“自由”之思想,得以深中乎人心。故其文明,其生活,半為東洋的,半為西洋的,蓋猶未奏調和融會之功也。今俄人因革命之風雲,衝決“神”與“獨裁君主”之勢力範圍,而以人道、自由為基礎,將統制一切之權力,全收於民眾之手。世界中將來能創造一兼東西文明特質,歐亞民族天才之世界的新文明者,蓋舍俄羅斯人莫屬。
歷史者,普遍心理表現之紀錄也。故有權威之歷史,足以震盪億兆人之心,而惟能寫出億兆人之心之歷史,始有震盪億兆人心之權威。蓋人間之生活,莫不於此永遠實在之大機軸中息息相關。一人之未來,與人間全體之未來相照應,一事之朕兆,與世界全域之朕兆有關聯。法蘭西之革命,非獨法蘭西人心變動之表徵,實十九世紀全世界人類普遍心理變動之表徵。俄羅斯之革命,非獨俄羅斯人心變動之顯兆,實二十世紀全世界人類普遍心理變動之顯兆。桐葉落而天下驚秋,聽鵑聲而知氣運,歷史中常有無數驚秋之桐葉、知運之鵑聲喚醒讀者之心。此非歷史家故為驚人之筆遂足以聳世聽聞,為歷史材料之事件本身實足以報此消息也。吾人對於俄羅斯今日之事變,惟有翹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傾耳以迎其建於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羅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適應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時之亂象遂遽為之抱悲觀也。
1918年7月1日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李大釗愛國文選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174 |
歷史 |
$ 193 |
中文書 |
$ 194 |
社會 |
$ 198 |
毛澤東及中國近/當代人物 |
$ 198 |
中國當代人物 |
$ 198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李大釗愛國文選
鵬鳥將圖南,扶搖始張翼;
一翔直衝天,彼何畏荊棘?
相期吾少年,匡時宜努力;
男兒尚雄飛,機失不可得。
—李大釗
作者簡介:
董雁南
李大釗不僅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卓越的社會活動家,而且是學識淵博、勇於開拓的著名學者,在五四運動前後佔有崇高的歷史地位。本書為李大釗愛國文選,充分展現了李大釗的愛國思想。
TOP
章節試閱
法俄革命之比較觀
俄國革命最近之形勢,政權全歸急進社會黨之手,將從來之政治組織、社會組織根本推翻。一時泯棼之象,頗足致覘國者之悲觀。吾邦人士,亦多竊竊焉為之抱杞憂者。余嘗考之,一世紀新文明之創造,新生命之誕生,其機運每肇基於艱難恐怖之中,徵之歷史,往往而是。方其艱難締造之初,流俗驚焉,視此根本之顛覆,乃為非常之禍變,抑知人群演進之途轍,其最大之成功,固皆在最大犧牲、最大痛苦之後。俄國今日之革命,誠與昔者法蘭西革命同為影響於未來世紀文明之絕大變動。在法蘭西當日之象,何嘗不起世人之恐怖、驚駭而為之深...
俄國革命最近之形勢,政權全歸急進社會黨之手,將從來之政治組織、社會組織根本推翻。一時泯棼之象,頗足致覘國者之悲觀。吾邦人士,亦多竊竊焉為之抱杞憂者。余嘗考之,一世紀新文明之創造,新生命之誕生,其機運每肇基於艱難恐怖之中,徵之歷史,往往而是。方其艱難締造之初,流俗驚焉,視此根本之顛覆,乃為非常之禍變,抑知人群演進之途轍,其最大之成功,固皆在最大犧牲、最大痛苦之後。俄國今日之革命,誠與昔者法蘭西革命同為影響於未來世紀文明之絕大變動。在法蘭西當日之象,何嘗不起世人之恐怖、驚駭而為之深...
»看全部
TOP
目錄
法俄革命之比較觀 …001
庶民的勝利 …006
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上) …010
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下) …040
再論問題與主義 …056
論民權之旁落 …065
戰爭與人口問題 …070
政客之趣味 …074
失戀與結婚自由 …077
暗殺與群德 …096
裁都督橫議 …099
隱憂篇 …111
大哀篇 …115
朱舜水之海天鴻爪 …119
東瀛人士關於舜水事蹟之爭訟 …130
彈劾用語之解紛 …135
強國主義 …140
新華門前的血淚 …141
輓孫中山聯 …142
紀念五月四日 …143
更名龜年小啟 …144
乙卯殘臘,由橫濱搭法輪赴春申,在太平洋 …145
南天動亂...
庶民的勝利 …006
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上) …010
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下) …040
再論問題與主義 …056
論民權之旁落 …065
戰爭與人口問題 …070
政客之趣味 …074
失戀與結婚自由 …077
暗殺與群德 …096
裁都督橫議 …099
隱憂篇 …111
大哀篇 …115
朱舜水之海天鴻爪 …119
東瀛人士關於舜水事蹟之爭訟 …130
彈劾用語之解紛 …135
強國主義 …140
新華門前的血淚 …141
輓孫中山聯 …142
紀念五月四日 …143
更名龜年小啟 …144
乙卯殘臘,由橫濱搭法輪赴春申,在太平洋 …145
南天動亂...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董雁南
- 出版社: 麥禾陽光 出版日期:2017-07-19 ISBN/ISSN:9789869496094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142頁
- 類別: 中文書> 社會科學> 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