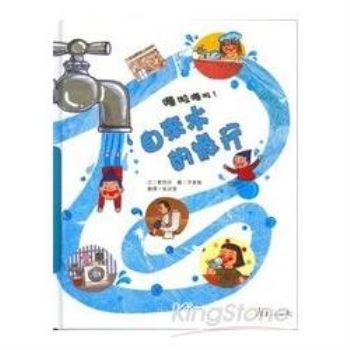不甘寂寞的帝王,
每日放任公公們胡鬧,
東廠加上錦衣衛,
玩不夠再來個西廠!
可公公這麼多,
總有些還是會空虛寂寞覺得冷,
所以怎樣都要鬥爭一下來暖個身。
北大歷史學博士帶你回到明朝現場,
見識情治機關東廠和西廠的厲害之處!
明朝太監何其多,公家單位大家都想吃香喝辣步步高升,
但想成為皇上寵愛的「大太監」,那可真是粥少僧多呀!
都說太監是佞臣,但名留青史的「好太監」也不是沒有,
何況明代還有007的錦衣衛,太監可比我們想的厲害多呢!
他們除了沒有「寶貝」,可是允文又允武,
待在皇上身邊他們有三寸不爛之舌,上了戰場戰力又直逼「無垢兵團」,
活躍於「東廠」時更是威風八面!更別提目中無人、先斬後奏的「西廠」了!
這些特務機關有說不完的八卦,比後宮更加吸引人!
太監、太監,到底是太賤?還是太奸呢?
| FindBook |
有 10 項符合
明朝的那些九千歲2:大太監的生死鬥爭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98 |
二手中文書 |
$ 240 |
明史 |
$ 272 |
明史 |
$ 282 |
中文書 |
$ 282 |
中國歷史 |
$ 288 |
中國歷史 |
$ 288 |
政治/法律/軍事 |
$ 288 |
歷史 |
$ 306 |
社會人文 |
電子書 |
$ 320 |
中國史地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明朝的那些九千歲2:大太監的生死鬥爭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胡丹
中國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三峽大學文學與傳媒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中國明史學會會員,主要研究明、清史及歷史文化傳播。
長期活躍在中國史研究的科研一線,同時致力於歷史文化的普及工作。
所著「明宮揭祕」系列白話歷史作品,在天涯論壇的「煮酒論史」版發表後,立即以其紮實的史學功底、犀利幽默的筆法、豐富的想像力、厚重的歷史感和隨處綻發的新見吸引了大量讀者。
作者亦被多家媒體譽為令人期待的新銳歷史作家。著有《大明王朝家裡事兒》(大旗出版)、《大明後宮有戰事》、《明朝的那些九千歲》(大旗出版)、《明代宦官史料長編》等書。
胡丹
中國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三峽大學文學與傳媒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中國明史學會會員,主要研究明、清史及歷史文化傳播。
長期活躍在中國史研究的科研一線,同時致力於歷史文化的普及工作。
所著「明宮揭祕」系列白話歷史作品,在天涯論壇的「煮酒論史」版發表後,立即以其紮實的史學功底、犀利幽默的筆法、豐富的想像力、厚重的歷史感和隨處綻發的新見吸引了大量讀者。
作者亦被多家媒體譽為令人期待的新銳歷史作家。著有《大明王朝家裡事兒》(大旗出版)、《大明後宮有戰事》、《明朝的那些九千歲》(大旗出版)、《明代宦官史料長編》等書。
目錄
前言
第一卷 那些動亂的日子裡
第一章 莫謂太監不殉國
第二章 公公一聲叱,汝休莫想逃!
第三章 拍馬衝陣的報效內官們
第四章 太監裡出了個大漢奸
第五章 金太監被貶,只因一句真話
第六章 上皇被誣,忠宦殉主
第七章 與弟與弟,還我土地
第八章 「宦權」,如春江水漲
第九章 曹、石驕逐徐有貞
第十章 宦官公子要學曹操
第二卷 一朝天子一朝臣
第一章 大漸託付,牛玉承遺詔
第二章 急入司禮奪權
第三章 「奸黨」未興而速敗
第四章 一個月,牛太監也完蛋啦
第五章 成化三宗弊
第六章 狐妖牽出來個西廠
第七章 西廠開張,燒起幾把火
第八章 革西廠,司禮監再生變故
第八章 西廠回歸
第九章 內閣「團團轉」
第十章 再革西廠,汪直也被人暗算了
第十一章 東廠太監謀入司禮柄政
第十二章 群奸之中擔道義
第三卷 「弘治致治」的光環下
第一章 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
第二章 宦官隊裡出了個「海瑞」!
第三章 忠、奸兩相宜
第四章 今日李廣!明日李廣!
第五章 「批紅」是這樣的
第六章 監閣共受顧命
第四卷 一瑾死,百瑾生
第一章 名起「八虎」
第二章 絕地反擊
第三章 家世、婚姻:劉太監的日常
第四章 朝堂上忽現匿名信
第五章 劉瑾真是千年富豪?
第六章 張永西征
第七章 千刀萬剮,再來一碗粥!
第八章 張永想學「劉馬侯」封爵
第九章 皇帝竟給自己加俸祿
第十章 寧王朱宸濠反了
第十一章 張永成了王陽明的保護傘
第十二章 拿了江彬,朝廷安穩
第一卷 那些動亂的日子裡
第一章 莫謂太監不殉國
第二章 公公一聲叱,汝休莫想逃!
第三章 拍馬衝陣的報效內官們
第四章 太監裡出了個大漢奸
第五章 金太監被貶,只因一句真話
第六章 上皇被誣,忠宦殉主
第七章 與弟與弟,還我土地
第八章 「宦權」,如春江水漲
第九章 曹、石驕逐徐有貞
第十章 宦官公子要學曹操
第二卷 一朝天子一朝臣
第一章 大漸託付,牛玉承遺詔
第二章 急入司禮奪權
第三章 「奸黨」未興而速敗
第四章 一個月,牛太監也完蛋啦
第五章 成化三宗弊
第六章 狐妖牽出來個西廠
第七章 西廠開張,燒起幾把火
第八章 革西廠,司禮監再生變故
第八章 西廠回歸
第九章 內閣「團團轉」
第十章 再革西廠,汪直也被人暗算了
第十一章 東廠太監謀入司禮柄政
第十二章 群奸之中擔道義
第三卷 「弘治致治」的光環下
第一章 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
第二章 宦官隊裡出了個「海瑞」!
第三章 忠、奸兩相宜
第四章 今日李廣!明日李廣!
第五章 「批紅」是這樣的
第六章 監閣共受顧命
第四卷 一瑾死,百瑾生
第一章 名起「八虎」
第二章 絕地反擊
第三章 家世、婚姻:劉太監的日常
第四章 朝堂上忽現匿名信
第五章 劉瑾真是千年富豪?
第六章 張永西征
第七章 千刀萬剮,再來一碗粥!
第八章 張永想學「劉馬侯」封爵
第九章 皇帝竟給自己加俸祿
第十章 寧王朱宸濠反了
第十一章 張永成了王陽明的保護傘
第十二章 拿了江彬,朝廷安穩
序
前言
《明朝的那些九千歲》一共三部,是以「朝代」為序。《明朝的那些九千歲》每一卷寫一朝,讀者會發現,全書故事大致上是銜接的,沒有出現斷裂的情況。這不是因為我筆法高、轉承自然,而是因為朝政的發展有其連續性,而大太監們在推動朝政發展上發揮作用。故我只需轉動歷史的把手,大太監們就一個接一個上場了—他們本為明代歷史上的重要角色。
雖然叫的是《明朝的那些九千歲》,寫的是大太監的故事,但大太監的生成及衰榮,是附生在明代政治機體之上的,如果不對政治史、宦官史的變遷歷程有所交代,則無法完全明白大太監們「力量」的源泉。所以本書在必要的節點上,會用一定的篇幅介紹明代宦官制度的新發展。可以說,《明朝的那些九千歲》是一部以大太監為中心,以太監故事相銜接的通俗明代宦官史。
第一部從開國寫到英宗正統年間,讀者於其中可知,明代之有「大太監」,即所謂「權閹」,並不是中晚期以後才有。早在永樂年間,就「湧現」出不少著名的大太監。大太監太多了,恰恰是最有名的鄭和我沒怎麼寫,因為他的事蹟讀者大多比較瞭解,而我寫的,全是讀者朋友們不熟悉、然確乎可稱大太監的人物。
本書是第二部,副標題是《大太監的生死鬥爭》,從正統十四年(西元一四四九年),土木之變講起,一直寫到正德十六年三月武宗朱厚照駕崩,從湖廣安陸遠道來繼位的世宗朱厚熜還沒到北京,我們這一部的故事就講完了,餘下的,留到下一部講。
過去總說明代是「太監帝國」,宦官「亂政」亂得厲害,可明朝到底有哪些大太監,除了鄭和、王振、劉瑾、魏忠賢,大概再多也數不出幾個吧。
我在每一卷的開頭,都列出了當卷「關鍵人物」,都是在書中占有一定分量的大太監。讀者朋友們可稍微留意,看有多少。全書都循此體例,三部寫下來。我估計,超過一百絕對沒問題。
這些大太監並不都是壞的,比如這一部裡寫到成化、弘治年間的大太監懷恩、覃昌、覃吉等,都是很有「名大臣」之風的好太監,就連素來瞧不起宦官的士大夫們,對他們都讚譽有加。還有一些很有個性的太監,比如「善諫」的何鼎、蔣琮等。對這些太監的書寫,無疑將給「骯髒」的明代宦官史增加兩個側面。
這一本的主題是「大太監的生死鬥爭」,所謂「鬥爭」,是指大太監之間的對抗與鬥爭,比如成化初年牛玉與王綸、正德初年劉瑾與張永等,他們為了權勢發生劇烈衝突。這是發生在明代中樞核心的戰爭。大太監們多是負有輔政之責的司禮太監,他們對於朝政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所以大太監鬥法,不是「一個人在戰鬥」,往往是兩個政治集團間的衝突造成時局動盪,其結果也將影響朝政的發展方向。也就是說,從太監的角度來寫明代政治史,本書應該算是首創吧。
如果讀者朋友讀了通俗的歷史故事意猶未盡,或學有餘力,還可以看看我即將出版的《明代宦官制度:考證與研究》。這是一部學術專著,也是我的博士論文,是國內第一部研究明代宦官制度的專門論著。我寫通俗的明代宦官故事,都是基於我對明代宦官的深入研究,材料多取自我所編寫的《明代宦官史料長編》。
我說這些,是為了告訴大家,您所讀的,是一部信史。
《明朝的那些九千歲》一共三部,是以「朝代」為序。《明朝的那些九千歲》每一卷寫一朝,讀者會發現,全書故事大致上是銜接的,沒有出現斷裂的情況。這不是因為我筆法高、轉承自然,而是因為朝政的發展有其連續性,而大太監們在推動朝政發展上發揮作用。故我只需轉動歷史的把手,大太監們就一個接一個上場了—他們本為明代歷史上的重要角色。
雖然叫的是《明朝的那些九千歲》,寫的是大太監的故事,但大太監的生成及衰榮,是附生在明代政治機體之上的,如果不對政治史、宦官史的變遷歷程有所交代,則無法完全明白大太監們「力量」的源泉。所以本書在必要的節點上,會用一定的篇幅介紹明代宦官制度的新發展。可以說,《明朝的那些九千歲》是一部以大太監為中心,以太監故事相銜接的通俗明代宦官史。
第一部從開國寫到英宗正統年間,讀者於其中可知,明代之有「大太監」,即所謂「權閹」,並不是中晚期以後才有。早在永樂年間,就「湧現」出不少著名的大太監。大太監太多了,恰恰是最有名的鄭和我沒怎麼寫,因為他的事蹟讀者大多比較瞭解,而我寫的,全是讀者朋友們不熟悉、然確乎可稱大太監的人物。
本書是第二部,副標題是《大太監的生死鬥爭》,從正統十四年(西元一四四九年),土木之變講起,一直寫到正德十六年三月武宗朱厚照駕崩,從湖廣安陸遠道來繼位的世宗朱厚熜還沒到北京,我們這一部的故事就講完了,餘下的,留到下一部講。
過去總說明代是「太監帝國」,宦官「亂政」亂得厲害,可明朝到底有哪些大太監,除了鄭和、王振、劉瑾、魏忠賢,大概再多也數不出幾個吧。
我在每一卷的開頭,都列出了當卷「關鍵人物」,都是在書中占有一定分量的大太監。讀者朋友們可稍微留意,看有多少。全書都循此體例,三部寫下來。我估計,超過一百絕對沒問題。
這些大太監並不都是壞的,比如這一部裡寫到成化、弘治年間的大太監懷恩、覃昌、覃吉等,都是很有「名大臣」之風的好太監,就連素來瞧不起宦官的士大夫們,對他們都讚譽有加。還有一些很有個性的太監,比如「善諫」的何鼎、蔣琮等。對這些太監的書寫,無疑將給「骯髒」的明代宦官史增加兩個側面。
這一本的主題是「大太監的生死鬥爭」,所謂「鬥爭」,是指大太監之間的對抗與鬥爭,比如成化初年牛玉與王綸、正德初年劉瑾與張永等,他們為了權勢發生劇烈衝突。這是發生在明代中樞核心的戰爭。大太監們多是負有輔政之責的司禮太監,他們對於朝政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所以大太監鬥法,不是「一個人在戰鬥」,往往是兩個政治集團間的衝突造成時局動盪,其結果也將影響朝政的發展方向。也就是說,從太監的角度來寫明代政治史,本書應該算是首創吧。
如果讀者朋友讀了通俗的歷史故事意猶未盡,或學有餘力,還可以看看我即將出版的《明代宦官制度:考證與研究》。這是一部學術專著,也是我的博士論文,是國內第一部研究明代宦官制度的專門論著。我寫通俗的明代宦官故事,都是基於我對明代宦官的深入研究,材料多取自我所編寫的《明代宦官史料長編》。
我說這些,是為了告訴大家,您所讀的,是一部信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