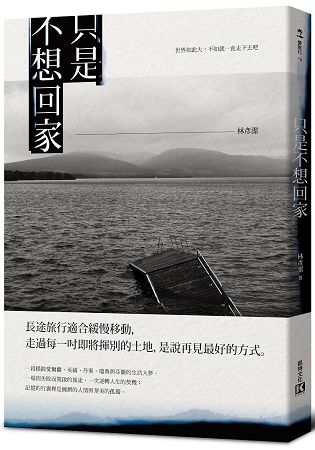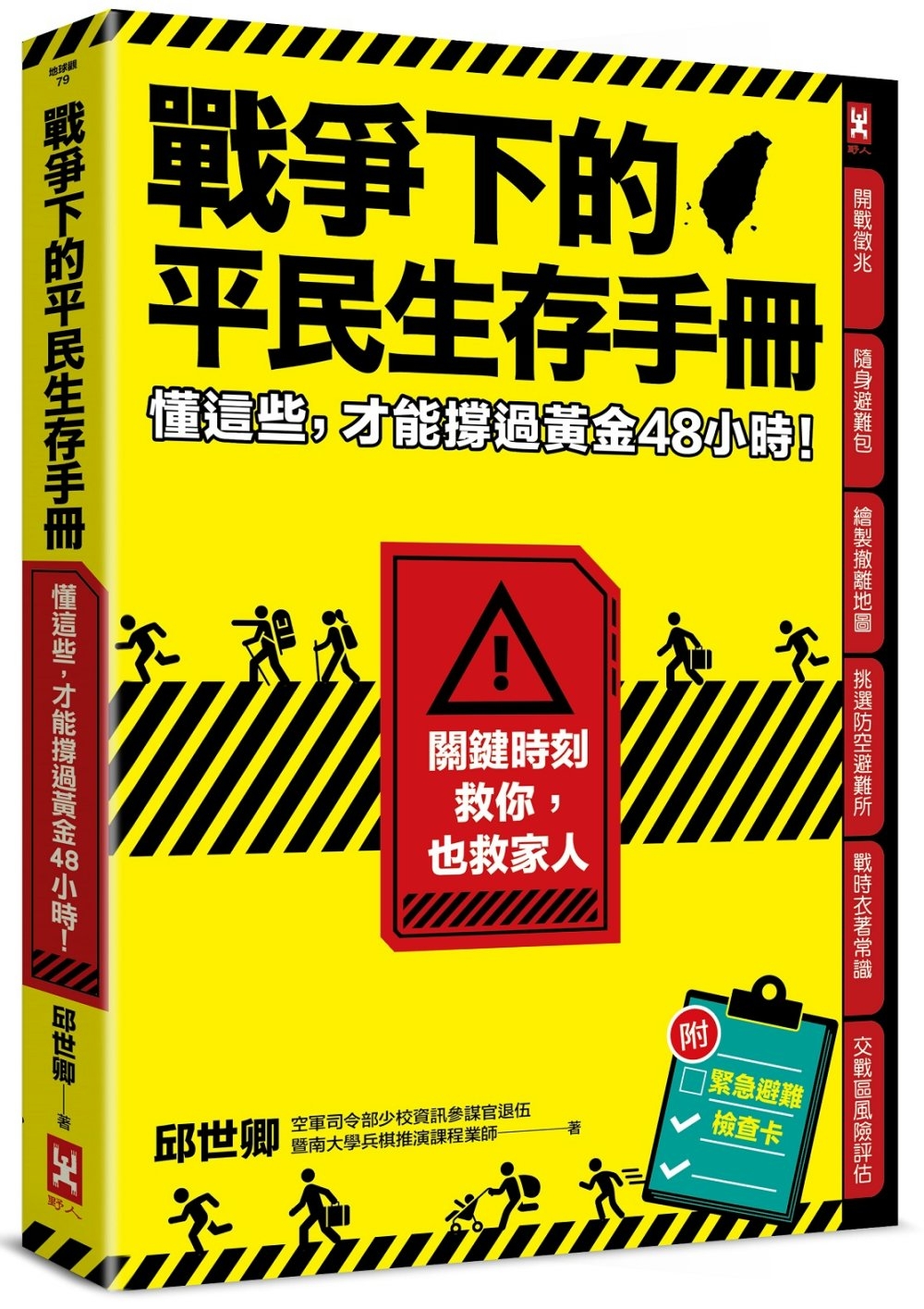【內文試閱1】世界這麼大,接著走就對了
巴士從西向東橫向對半穿越愛爾蘭,再度回到首都都柏林(Dublin),接著轉搭另一輛巴士,往東北方的貝爾法斯特(Belfast)前進,正式進入北愛爾蘭(Northern Ireland)。
從都柏林開車進入北愛爾蘭的國土,僅僅九十分鐘。我與一路上相遇、告別、重逢數次的費德里克,無預警在電話中斷訊,手機訊號從愛爾蘭電信公司瞬間轉換成英國,正式與他和愛爾蘭雙雙道別。微涼的九月初,學校假期結束,費德里克即將返回西班牙工作崗位,我則還在思考該繼續旅行,或是留在愛爾蘭找份工作,安安穩穩的度過一年,一路上不斷思索這個問題,依舊徒勞無功,流浪到最後總會有個答案吧。我看著斷訊的手機螢幕,為自己茫然的下一步給了看似安心的註解。
沿途拖著行李預計步行三十分鐘到前一晚下訂的青年旅館,穿越貝爾法斯特市中心,城市的氛圍比起純樸含蓄的愛爾蘭,多了成熟的韻味,建築物的線條、面貌也帶點現代化的氣息,不像愛爾蘭總保有些孩子喜愛的鮮豔色調。走了將近四十分鐘,看來是迷路了,正好遇見幾位在路邊閒聊的計程車司機,上前尋問青年旅館確切的方向,接下來短短幾十秒的回應,我竟然一句也聽不懂,只能從他熱情的手勢判斷前往的方向。貝爾法斯特市民的口音像是混合了泰語的發音,和英國人鏗鏘有力的英式英語,不禁令我擔心接下來幾天鴨子聽雷的後果,會不會因此多走上好幾公里的冤枉路。
歷經迷路和突如其來的大雨,狼狽不堪,總算抵達青年旅館,拉甘背包客(Lagan Backpackers)是位在一整排紅磚瓦樓房中的其中一戶,外觀如同一般住家沒什麼兩樣,若不是手中的門牌號碼再次提醒,全身濕透的我,大概會被認為是誤闖民宅的遊民。
向櫃臺人員繳付證件,填完基本資料,我拿出一張歐圓大鈔準備付下三晚的住房費用,卻被告知找回的錢將全數依照現在的匯率轉換成英鎊,當下才又提醒我,雙腳踏的國土不僅口音截然不同,曾經血脈相連的孿生姐妹,自一九二一年,愛爾蘭早已由一場獨立戰爭,正式揮別東北方的國土,從此一島兩國。北愛爾蘭與蘇格蘭、英格蘭、威爾斯合併為「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簡稱UK。
拉甘背包客原是兩層樓的住宅,經營者將住家用途轉換成招攬房客的空間。除了一樓角落做為訂房手續的櫃臺,其餘空間就跟一般住家幾無二致,就連床鋪緊密的排列方式,若非閨中密友或熟識的家人,我想很難在第一晚就能接受如此「親密」的對待。一般青年旅館安排六人到八人為一間房,仍會顧及隱私,將床位規劃成上下舖,中央留下公共空間,鮮少像拉甘背包客在雙層床位中央再填入數張單人床,似乎唯有選擇上舖,才可免除半夜轉身和隔壁床的室友四目相對的窘境。
所幸第一晚隔壁床並無人入住,到了第二晚進房時才遇見來自南韓的女室友金智秀。男女混宿的床位通常直接反映在低廉的價錢上,入住一晚十英鎊(約台幣五百元)的床位,還附上傳統英式早餐,在貝爾法斯特屈指可數。直到隔壁床舖出現新室友,被迫近距離接觸下,交談是化解尷尬最自然的互動。
金智秀是一名南韓的社工,隻身來到北愛爾蘭擔任國際志工,協助社區老人照護的工作,利用兩天休假日到處旅行。閒聊之下,我們交換了觀看對方國家電視劇的經驗。改編自日本漫畫的台灣偶像劇《流星花園」,四位花美男仍是泡菜妹永遠的歐巴。台灣回饋韓國就不只是收視率上的表現了。韓式料理成為聚會難以剔除的名單之一;魚貫進入韓國旅行的人數年年攀升;販賣韓國服飾成為低成本創業者的首選。說了那麼多台灣進貢韓國文化的豐功偉業,金智秀在南韓時有所聞,她開玩笑說,希望有生之年來到台灣旅行,嘴裡吃的不是泡菜,聽到的不是滿街的台灣人說著韓文,否則大概會以為南韓悄悄併吞了台灣。原本過於親近的床鋪距離,因為台灣哈韓的話題,化解了一晚的尷尬。
在愛爾蘭的科芙小鎮,知道該地曾是鐵達尼號停靠的中繼站,而貝爾法斯特則是打造鐵達尼號這艘船的所在地,同樣因為過去這場船難事件而聲名大噪。
鐵達尼號於一九一二年沉船,一百年後,貝爾法斯特為了保留過去沉船歷史的記憶,耗時三年在當時打造鐵達尼號的造船廠旁,蓋了一座博物館,名為「鐵達尼號貝爾法斯特」(Titanic Belfast),自二○一二年開放以來,每年有成千上萬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造訪貝爾法斯特,到此探索沉船前飄蕩在船艙裡的嘆息、絕望與無助。
走進鐵達尼號,迎接我的是一台纜車,大約二十分鐘的航程,帶我回到一百年前處女航行駛的途中,一同和二千二百一六名乘客與工作人員隨著船身起伏,航向紐約。從船身底部出發,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工人日以繼夜在昏暗悶熱的環境下工作,纜車緩緩上升,投影的歷史畫面夾雜工人敲打船體的刺耳聲響,身歷其境。抵達船艙,下纜車步行,櫥窗裡結合投影技術,生動呈現貴族與平民在三種船艙等級裡生活的景象。其中讓我駐足最久的展區,是一連串從一九一二年四月十四日晚間十一點四十分,一直到次日四月十五日凌晨二點二十分所發出的無線電訊號,每一通訊號清楚記載著船體的位置、氣候溫度、撞上冰山的距離、船長的命令、乘客逃生狀況,最後船尾消失於海平面的最後一刻,來自北大西洋海面的無線電訊號,最終不再發出任何聲響。
即便我腦中的電影畫面,將鐵達尼號沉船過程透過分鏡拆解,加深了與真實沉船情況更具張力的表現,仍然不敵我耳中迴蕩的每一通求救訊號來得更為真實且沉痛。聲音的想像,幾乎掩蓋掉印象中的電影畫面,關於鐵達尼號的故事,好像又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
不知不覺從愛爾蘭跨越毫無屏障的國界來到北愛爾蘭,心境上也莫名隨之轉換了。世界如此大,不如就一直走下去吧!
【內文試閱2】媽媽的距離
我習慣在移動的途中向宿主發出借宿訊息,一來免除宿主需等待多時的不確定感,也符合我毫無旅行路線的計劃。巴士上昏睡四小時,才剛抵達英格蘭約克(York)火車站,電話就響起了。
「你好,剛剛收到你的來信,我很樂意接待你兩晚。請問你現在人在哪裡?」派翠克(Patrick)語帶親切的對我說。
「非常謝謝你這麼迅速回覆借宿需求,還親自撥電話跟我確認,我剛抵達約克火車站。」接到這通溫暖的電話,長途車程累積的疲累,瞬間消逝。
轉搭火車,五十分鐘後到站,斯卡伯勒(Scarborough)車站門口,我看見派翠克牽著他的愛犬,樂喜(Lexi),四處搜尋我的身影。
從蘇格蘭一路奔波到英格蘭,派翠克看出我眼裡的疲憊,體貼邀請我到一旁面海的酒吧稍作休息。斯卡伯勒鎮上公車班次的間距,若是一不小心錯過了,走進酒吧喝一杯,絕對是消磨等待時間最好的選擇。
我牽著樂喜在酒吧外頭等著,派翠克端出兩杯啤酒。傍晚五點多,面海的景色呈現微微的紅光,海浪猛烈拍打沿岸石牆,低矮的防波堤,海水不斷濺上路面,打在併排的車輛上,警報器嗡嗡作響。每當窗外起風,天空飄起細雨,派翠克就會拉著樂喜往外跑,來到酒吧選同一處座位,看著整晚不平靜的浪。
天黑前的晚霞,像是加了色母,留下一片層層疊疊的暗紅,籠罩著天空。
派翠克退休前是一名小學老師,在里茲(Leeds)教了幾十年的書,退休後從約克西邊的里茲搬到東邊的斯卡伯勒,他和我一樣都喜歡靠海的地方。另一個讓他愛上這座臨海小鎮的原因,是沿著海岸邊的山,永遠可以發現新的路線和高度,從不同角度欣賞沿海風光。
派翠克精準的算好公車抵達的時間,帶我搭上通往上層路面的輕軌電車,僅約三十秒的時間,只為讓我免於扛著身上沉重的行李,攀爬近百層的階梯而苦不堪言。步出纜車,眺望整面山坡上的建築,隱隱透著絢爛的光線,將漆黑的海面,暈成一片多層次的墨,我幾乎看傻了,忘了若是錯過這班公車,就得在綿綿細雨的夜晚,拖著十幾公斤重的行李走在泥濘的山路上,到達派翠克位在另一個山頭的住處。我想步行四十分鐘的山路,對派翠克來說應該是家常便飯,但我可不想在第一晚就領教他口中擁有毫無死角、完美曲線的斯卡伯勒。
紙條一:
早安,我不想一大早就吵醒你,廚房裡有咖啡和茶,我和樂喜在對面的花園裡
曬太陽。
手裡握著咖啡杯保暖,脖子上圍著厚重的圍巾,英國九月的天氣對我來說已有些寒意。派翠克在陽光下忙著園藝工作,一身輕薄短衫,仍是滿身大汗,樂喜一見我就興奮的撲上來,幸好派翠克即時將她攔住,否則清晨藉由一杯熱咖啡沐浴,肯定寒意全消。
進入長達三十年的教職生涯之前,派翠克渴望的是當一名全職園丁。
「退休後唯一讓我期待的事,終於可以浪費大把時間打造自己的花園。」派翠克說:「這些花花綠綠的植物,會因為你的細心照料而越長越好,和人相處就不同了,總是無法預期。」
我聽出了派翠克這句話背後,可能有著令他感到失望的故事,但我沒有追問,只是好奇他為何過著獨居的生活。
「你的家人沒跟你住在一起嗎?」我問。
「我沒有結婚,我有兩個弟弟,其中一個最近搬來約克,不過我們不太常見面。」他說。
我想我不該再問下去了,免得破壞帶點陽光的涼爽早晨。
一杯咖啡之後,樂喜早已搖著尾巴等在花園門口,派翠克每天固定帶她到山裡走走。我換上球鞋,加入他們的清晨健行。
早晨潮汐低,留下整片清爽乾淨的沙灘,像是一幅畫在邊上留白。派翠克停下腳步眺望,這是他最喜歡這座城市的角度,彎下腰解開樂喜的的項圈,任由她四處奔跑玩耍。
三年前,派翠克將媽媽的骨灰就撒在這片山坡上,希望她能永遠看見眼前這片美麗的海景,想念媽媽的時候,他會走到這裡和媽媽說說話。派翠克有過一段悲慘的童年回憶,最大的原因來自於她最愛的母親,露西(Lucy)。
露西從小在英國中部的修道院長大,修女的管教非常嚴格,成年之前飽受精神和肉體上的虐待,造就了猜忌和極度缺乏安全感的扭曲性格。二十歲那年,露西終於離開了她永遠不想回去的「家」。渴望擁有家庭的露西,隔年認識第一任丈夫,兩人很快有了愛的結晶,生下了派翠克。婚後,露西嫉妒、猜疑的性格表露無遺,引發憂鬱症,成天與丈夫惡言相向,也將童年遭遇的不當管教,發洩在派翠克身上。派翠克十歲那年,露西認識了第二任丈夫,卻不願切割與派翠克爸爸的關係,一條枷鎖將這兩任丈夫和露西綁在一起,無情的將年幼的派翠克困在這段不健康的家庭關係裡。三年後,派翠克同母異父的兩個弟弟相繼出生,直到派翠克年滿十八歲,聽從高中老師的建議,搬離家中到外地求學,才結束長達八年殘酷的共生關係。
在我住進派翠克家裡之前,竟有長達十八年的時間,沒有任何一位像我老遠跑來換宿的訪客主動聯繫他,當然主要原因是沒有背包客願意長途跋涉遠離市區,來到這座景點屈指可數的鎮上,成天與大海相望。直到碰見我這位罕見的亞洲客,願意聽他說說話,也許這段深埋心底的秘密,透過傾吐才知道曾經的傷害有多深。我隱約看見派翠克望向遠方的那對雙眼,在訴說過往的同時,摻雜了無奈、憐惜、欣慰的眼神。母親臥病在床的那一年,派翠克終於說服她搬到斯卡伯勒一起生活,在此之前,派翠克仍然害怕面對一直深愛著的母親,而那段日子成為了母子倆此生唯一共同的美好回憶。
「剛搬到斯卡伯勒的時候,我養了一隻狗叫斑尼,他陪著我母親走過那段病痛的日子,我想斑尼的關係要比我和她好得多了。」樂喜從遠處跑回派翠克身邊,他摸摸樂喜的頭說。
「隔年斑尼也走了,我將他的骨灰也撒在這片山坡上,我想媽媽會很開心有斑尼和她作伴,再也不用害怕孤單了。」派翠克悵然的說著。
當派翠克說起這段往事的時候,我刻意將頭撇向面海的那一端,讓海風吹著濕潤的雙眼。我和派翠克相處才兩天,就能打從心底分享鮮少和外人談及的故事,和他相處就像家人一樣自在。
紙條二:
早安,桌上的麥片與早上剛出爐的吐司,請盡情享用,當然還有咖啡、果汁、
紅茶。我帶樂喜到海邊洗澡,等我回來一起外出喝下午茶。
歷經一個多月的旅行,已經好久沒有睡得這麼沉了,睜開眼,再過十分鐘竟然就到中午。等待派翠克和樂喜回家的同時,閒來無事,在家裡四處走走看看,發現壁爐上方擺了三張照片,其中兩張是派翠克已故的雙親,另一張是和派翠克同樣有著圓潤身材的男人,與他有幾分相似。
派翠克和兩個同母異父的弟弟在母親過世前並沒有太多交集,三年前母親病逝於斯卡伯勒,前來探望的只有最小的弟弟,另一個弟弟因為受不了母親長期的精神折磨,成年後就搬離家中,從此不再和家人聯絡,二十多年來毫無音訊。派翠克唯一的家人只剩有著一半血緣關係的弟弟,卻僅止於感恩節和聖誕節的輕聲問候。
從派翠克家中搭乘巴士到市中心只要十五分鐘。派翠克帶我往靠海的一端走去,遠遠就看見屋頂上竄起一座時鐘,小巧的咖啡廳掛在半山腰。時鐘咖啡(The Clock Café)於一九一三年開始營業,紅瓦疊成屋頂,柱子漆上鮮黃色,一格一格的白窗櫺鑲成整面窗,沒有過於華麗的外表,在此佇立一百年,我正好趕上她的百年大壽。時鐘咖啡出了一本小冊子,紀念她過去這一世紀的所見所聞。
咖啡廳門口擺著兩張面海的長凳,前方的石牆平台成了餐桌,我和派翠克望著眼前的海景,嘴裡嚼著裹上香濃奶油的司康(Scone)。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方的這座平台,是當時防禦德國艦隊從海面上轟炸的絕佳地點;到了一九三九年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這座咖啡廳成了海軍航行指揮的地方。時鐘咖啡參與了世界上最重要的兩次戰爭,在戰亂中為斯卡伯勒人民扮演著防衛的角色,若不是坐在身旁的派翠克告訴我這些故事,我大概只在乎平台上那些可口的茶點,而渾然不覺這座平台曾經掩護過多少士兵。我想經營者不想過於渲染這座平台的豐功偉業,只是單純的把長凳擺在平台後方,讓路過喝杯咖啡的遊客,在欣賞美景的同時,不經意的置身在這段歷史中。
派翠克繼續說起他和斯卡伯勒之間更深層的關係。五十五歲時,派翠克的胰臟出了問題,被診斷出只剩下幾個月的生命,只能暫停教職,住進醫院長期治療。他的意志力戰勝了病痛,健康暫時穩定下來。過去斯卡伯勒陪伴派翠克度過好幾個學期結束後的暑假,生病之前,他曾想過退休後搬到這裡養老,現在既然提前退休,總算可以為自己好好過日子了。斯卡伯勒似乎成為了派翠克活下來的動力。
派翠克身旁從來沒有伴侶相伴,獨身六十年,年輕時曾遇見心儀的對象,卻總是在雙方決定更進一步的當下,過於親密的恐懼讓他心生畏懼。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派翠克為此非常憂心無法像常人一樣擁有穩定的伴侶關係,卻又無法敞開心房接納即將萌芽的愛情,讓對方完全走入他的生活。在長期自責、怨恨與愧疚中引發了憂鬱症,他開始接觸心理醫生的治療,原來心底那團躁動的漩渦,來自兒時一段不尋常的共生關係。母親將前後婚姻關係的存在視為理所當然,讓年幼的派翠克扭曲心理上對愛的正常認知,那團漩渦在他成年之後成為每天夜晚的夢魘。在我借宿的那段時間,派翠克不斷提醒我,若是聽見他在夜晚瘋狂喊叫,不要感到驚慌,那只是他常年的驚嚇,而每晚驚醒後,樂喜總是用憐憫的雙眼望著床上驚魂未定的派翠克,才稍稍讓他獲得恐懼後的救贖。
曾經有個朋友問我:「你知道最令人恐懼的事情是什麼嗎?」我當時想了很久回答不出來,「當你不知道恐懼距離你多遠的時候。因為恐懼的距離會隨著你的幻想忽遠忽近,這樣的恐懼才巨大的可怕。」朋友這麼告訴我。
離開斯卡伯勒的最後一晚,享用了派翠克親手料理的農舍派(Cottage Pie),這是他小時候家裡最常出現的食物。以前家裡常常有隔夜菜,一個禮拜總有幾個晚上,媽媽會把馬鈴薯放在前一天的食物上面,再撒上一層便宜的起司,一起放進烤箱裡,出來後就變成一道美味的料理。當然派翠克沒有將隔夜菜招待即將與他道別的訪客,但是藉由這道料理,他想起了媽媽,也讓我嘗到了他想念媽媽的味道。
隔日,我們相擁道別,彼此嘴角都掛著欣慰的笑容。短短三天,我們交換了彼此的人生故事,堅信不久的將來會想念對方。派翠克在火車啓程前帶著樂喜先行離開了月台,我想他是不願意讓感傷的氣氛,隨著火車行駛發出轟隆轟隆的聲響,拉高離別的情緒。看著他的背影在月台轉角消失,心裡真有些不捨。
火車停靠下一站,旅客魚貫走進,我從窗外拍下一位母親看著孩子即將遠離家鄉的神情,突然想起多年前第一次暫別台灣,母親在機場送別時別過頭那一刻的表情。
| FindBook |
有 9 項符合
只是不想回家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60 |
二手中文書 |
$ 160 |
環遊世界 |
電子書 |
$ 224 |
旅遊書 |
$ 253 |
旅行文學 |
$ 272 |
旅遊 |
$ 281 |
中文書 |
$ 288 |
旅行文學 |
$ 288 |
歐洲旅遊 |
$ 288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只是不想回家
世界如此大,不如就一直走下去吧
長途旅行適合緩慢移動,
走過每一吋即將揮別的土地,是說再見最好的方式。
一段橫跨愛爾蘭、英國、丹麥、瑞典與芬蘭的生活大夢,
一場因失敗而開啟的旅途,一次逆轉人生的契機;
記憶的行囊裡是擁擠的人情與華美的孤獨。
旅程開啟於一段不快樂的時期,一個無法達成的夢想卻為作者指引了另一個去向。人生難以預測每一步路,永遠無法知悉命運降臨於己的諸多細節,從愛爾蘭到西北歐各國,沒有預期心理的路途,迎面而來的往往是最鮮明、瑰麗的人世風景,釋放了種族、國籍和語言、文化的無形界線,所有經過眼前的容貌皆是另一個自己。
以異國生活為敘事文本,在人與人的輾轉相遇之中,尋求的是每一種讓自己快樂的方式:快樂地度日、快樂地成敗或快樂地悲喜…世界這麼大,接著走下去就對了,唯有透過旅行,才發現生命將有太多可能。人們不該永遠只過同一種生活、在乎同一件事情、堅持同一種思維,這將是每一段旅行帶給自己最大的提示與隱喻。
作者簡介:
林彥潔
從事廣告製片多年,常常有時間久了應該可以做些別的事的念頭,相信不斷嘗試沒做過的事,最後也不會有什麼損失。熱衷長時間旅行,旅程中有時痛苦也有快樂,唯有不斷經歷這些,才能在參與世界之後,獲得意想不到的結果。
TOP
章節試閱
【內文試閱1】世界這麼大,接著走就對了
巴士從西向東橫向對半穿越愛爾蘭,再度回到首都都柏林(Dublin),接著轉搭另一輛巴士,往東北方的貝爾法斯特(Belfast)前進,正式進入北愛爾蘭(Northern Ireland)。
從都柏林開車進入北愛爾蘭的國土,僅僅九十分鐘。我與一路上相遇、告別、重逢數次的費德里克,無預警在電話中斷訊,手機訊號從愛爾蘭電信公司瞬間轉換成英國,正式與他和愛爾蘭雙雙道別。微涼的九月初,學校假期結束,費德里克即將返回西班牙工作崗位,我則還在思考該繼續旅行,或是留在愛爾蘭找份工作,安安穩穩的度過一年,一...
巴士從西向東橫向對半穿越愛爾蘭,再度回到首都都柏林(Dublin),接著轉搭另一輛巴士,往東北方的貝爾法斯特(Belfast)前進,正式進入北愛爾蘭(Northern Ireland)。
從都柏林開車進入北愛爾蘭的國土,僅僅九十分鐘。我與一路上相遇、告別、重逢數次的費德里克,無預警在電話中斷訊,手機訊號從愛爾蘭電信公司瞬間轉換成英國,正式與他和愛爾蘭雙雙道別。微涼的九月初,學校假期結束,費德里克即將返回西班牙工作崗位,我則還在思考該繼續旅行,或是留在愛爾蘭找份工作,安安穩穩的度過一年,一...
»看全部
TOP
目錄
前言:夢想遣返回台
愛爾蘭
英國奶奶遺忘前的問候
庶民文化看見世界
德國媽媽的晚茶時間
犧牲者
三個男人與十九世紀公寓
皮繩上的魂
學習的理由
每天睜開眼,就想成為一位藝術家
圖書館員的最後一天
英國
世界這麼大,接著走就對了
北愛爾蘭畫家的一句話
麥金塔許教派
媽媽的距離
世界是我的牡蠣
丹麥、瑞典、芬蘭
自行車的異想之路
搭便車的漫長等待
IKEA、肉桂卷,原來還有這些
抬起頭就能看見信仰
生命沒有年齡
後記
愛爾蘭
英國奶奶遺忘前的問候
庶民文化看見世界
德國媽媽的晚茶時間
犧牲者
三個男人與十九世紀公寓
皮繩上的魂
學習的理由
每天睜開眼,就想成為一位藝術家
圖書館員的最後一天
英國
世界這麼大,接著走就對了
北愛爾蘭畫家的一句話
麥金塔許教派
媽媽的距離
世界是我的牡蠣
丹麥、瑞典、芬蘭
自行車的異想之路
搭便車的漫長等待
IKEA、肉桂卷,原來還有這些
抬起頭就能看見信仰
生命沒有年齡
後記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林彥潔
- 出版社: 凱特文化 出版日期:2017-09-29 ISBN/ISSN:9789869504324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192頁 開數:25開
- 類別: 中文書> 旅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