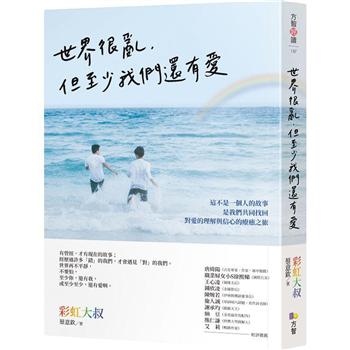第一章
秋來香晚,一殿豔紅。
龍央殿外,跪著一名即將被處死的侍衛,大婚的鸞彩鋪了滿地,紅彤彤的布晃得扎眼,還有十天便是皇帝婚期。
金鑾椅上,虞國皇帝李效坐著,臉色陰沉。
大學士手執摺子,匆匆路過龍央殿,腳下不停,進了殿裡,一躬身。
「臣叩見陛下。」李效沉聲道:「賜座。」
兩名太監搬了椅子來,大學士一撣袖子,就著椅子邊小心翼翼地坐了,抬眼打量皇帝臉色,只一瞥,便即心裡有數。
李效是他看著長大的,自十六歲登基,至今六年,喜怒無常、嗜殺、暴戾、不近女色、無愛好,比虞國以往的任何一位皇帝都難伺候。
這條頭龍,渾身都是逆鱗。
今日,大學士上殿前見一名侍衛跪在殿外,領子裡插了根凌遲的牌,不知是觸了李效的哪根神經,離死不遠了。
大學士對侍衛穿的服飾熟得不能再熟——是鷹奴。
宮內豢鷹,供王公大臣們春狩秋獵時用,是百年前起祖先立的編制。前些年朝上大臣們以空費國庫為由,聯名遞了摺子,想將鷹隊裁掉。皇帝沒批,但將鷹隊從七十人減為二十人,尋常侍衛從四品,侍衛隊長正四品,養鷹人的隊長,被喚作“鷹奴」。
外頭跪的侍衛面容白皙乾淨,觀那模樣不到二十,侍衛冠沿插五根彩翎,便是這一任的鷹奴。
大學士思忖良久,一捋白須:「不知陛下召臣來何事?」
李效冷冷道:「先生要告老?」
龍案上,攤著大學士告老還鄉的摺子。
大學士欣然一笑,緩緩唏噓:「老了,站不動了。」
李效臉色現出難得的溫和:「站不動,坐著也行。」
大學士自嘲地搖了搖頭:「皇上今年大婚,喝完酒,老臣也好放心回家。」
李效婚期在即,心裡頗有點說不出的滋味,正想讓大學士來說說話,稍作排遣,當即轉了話頭,淡淡問:「先生最近都在讀什麼書?」
大學士答:「回陛下,老臣在讀《虞史》。」
李效:「小時候,先生給我揀了不少故事說過。」
大學士若有所思點頭:「每次重讀,多少都有點體悟。」
李效:「有何體悟?」
大學士反問道:「陛下可曾記得百餘年前,統曆年間,我朝第二任帝君,皇成祖長樂帝。」
李效:「記得,明凰殿裡,還掛著長樂帝的畫像,統曆年間匈奴進犯,勾結皇后反叛。統曆十六年秋,朝堂傾覆,戰火頻起。一夜間奸賊謀朝篡位,國之將危。成祖連夜逃離京城,韜光養晦,重奪政權,掃蕩邊陲,振我大虞聲威。」
「成祖挽狂瀾於既倒,是孤此生最敬仰之人。」
大學士看了殿外侍衛一眼,溫和笑道:「皇上都知道了,老臣也沒什麼故事可說了。」
李效道:「不,先生的故事還是很有趣的,況且孤對成祖所知寥寥,只知其英雄氣概,卻不知其點滴小事,倒頗有點興頭。」
大學士欣然道:「那老臣便說說?」
太監端上茶水,大學士抿去浮葉,喝了一口,緩緩道:「成祖生前,身邊有兩個人。」
統曆年間。
虞國太子李慶成身邊只有兩個人,一個是侍衛,另一個還是侍衛。
為何不是太監呢?
皇上認為太監多了不好,閹人心思陰毒,易攛掇著學壞,虞國以武立國,不如陽剛男子陪讀,也可令嫡子學學武人正氣,遂給李慶成派了名侍衛貼身保護。
皇后表示同意,也給李慶成派了侍衛貼身保護。於是太子便有兩名貼身侍衛了。
皇后娘娘派來的侍衛甲:身長八尺七寸,玉樹臨風,儀表堂堂,身穿一襲錦紅飛鷹武袍,頭戴天武垂瓔冠,腳蹬踏虎黑靴,腰繫虞國名劍「雲舒」。
劍出鞘,如龍吟,可斬萬里江水,破雲而上。
侍衛甲名喚「方青余」,面如冠玉,鼻樑高挺,濃眉英目,笑時英俊瀟灑,舉手抬足,頗有武林世家風範。履有春風之聲,龍行鶴步——鶴般倨傲,鶴般謙禮,可見其英姿。
據傳此人乃是虞國第一武功高手,皇后的娘家人,宮內唯有皇上、皇后開口是「青余青余」地叫,連太子也得喊一聲「青哥。」
其餘人都得恭恭敬敬,稱一聲「方大人。」
御前侍衛雖只有四品,卻是未來皇帝的身邊人,誰也不敢得罪了。
皇上派的侍衛乙:身長九尺,膚色黝黑,鼻作鷹鉤,眉若兵鋒,唇如折劍。身穿一襲黑色武袍,袍襟滌得發白,自進宮起就沒換過。此人手腳修長,隱隱比侍衛甲還高了半頭,本是天生的衣裳架子,奈何不苟言笑,一臉陰鷙。
侍衛乙雙手指節分明,指甲修得齊短,手背青筋糾結,彷彿隨時想捏斷人喉骨,站在黑暗裡,便是無聲的夜梟,宮女太監入夜走得緩了,便能察覺他的眼在暗處看著自己,於是屁滾尿流,魂飛魄散。
更令人膽寒的是,他的左臉戴著半張銀製的面具,關於這張面具的由來,宮裡傳說已久,有傳他臉上被仇家斬了一刀,亦有人傳他小時燙了半張臉,總之那半邊面具,配上其陰冷神色,讓人不由得敬而遠之,不敢招惹。
久而久之,宮裡人見了他都繞道走,人緣遠遠不及侍衛甲。
侍衛乙也有個名,喚「張慕成」,後因與太子重了個「成」字,改為「張慕」。但宮裡約好了似的,除了當面碰上,否則都不喚他「張大人」,背地裡俱是「那個人」「那人」地叫。
太子也不喊他「慕哥」,「張哥」什麼的,只混著叫,有時候叫「喂」,有時候叫「啞巴」,大多數時候不主動喊他。
皇后更不想見他,唯有皇上偶爾派人宣,一般皇上見張慕的時候,便是太子挨戒尺、罰板子的時候了。
李慶成在殿裡玩什麼鬧什麼,皇上大部分時間心裡一清二楚,宣張慕不過問幾句話,確認一下。
張慕簡單地點頭、搖頭,「唔」一聲,或者擺手,便決定了太子要挨幾下教訓。
這種侍衛,實在當得太討嫌了,職業素質決定了待遇,太子待見誰不待見誰,一目了然。
此人當值時,身後背著一把三尺九寸長的刀,刀沒有名字,且從不出鞘,便在殿前廊下安靜站著,不說半句話,像截陰險的木頭。
侍衛乙比侍衛甲進宮還早,聽說十七歲就開始跟著太子,那年太子六歲,如今太子十六了,侍衛乙已近而立,在宮內待了整整十年。
自打李慶成懂事以來,便認識這傢夥,記憶裡從未見張慕摘下過面具,甚至連他的聲音也不常聽到。
唯一關於這啞巴的一點點回憶,還是在很多年前,自己被四王爺陰了。
那年四王爺進京,在御花園裡和太子攛掇個事兒,大體是什麼也記不清了,似是大冬天裡讓太子做什麼好玩的,太子便捋了袖子大聲稱好大說好好好:「本宮要玩,這就上湖去。」
太子還未行動,只見張慕伸出一隻手,不由分說就把當朝皇上的弟弟推了個屁股墩,又踹了一腳,四王爺合該犯太歲,朝後直摔進去,嘩啦一聲破了湖冰,墜進太掖池裡。於是大病三天,小命差點交代在京城裡。
事後皇上龍顏大怒,這狗侍衛真是有夠討嫌,逼著張慕給四王爺恭敬磕了三個響頭賠罪,這才揭過。
這還不算,還有更討嫌的。
在書房念書,兩名侍衛便一左一右,立於廊下等,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太子和方青余聊天,張慕便在一旁聽著。
「青哥來給我續段,不想寫了。」李慶成笑道。
方青余微一哂:「續不得,當心太傅罰你。」
李慶成道:「咱們筆跡像,一兩段看不出來。」
方青余口中推讓,卻上前提筆幫李慶成寫了,李慶成懶懶扒在案上,看侍衛幫自個兒作文章,偶爾調侃幾句。
方青余笑了起來,兩道濃眉一擰:「快完了,這可得留你自個兒寫,我念,你寫。」
李慶成朝嘴裡扔了顆葡萄,接過筆,他的字大部分跟著方青余學的,既喚他哥,又學他寫字,方青余人英氣,字也好看,作得一手好文章,文武雙全,中規中矩猶如名家手跡,連帶著太子也學得一手好字,皇上很是欣賞。
至於門外那截木頭,李慶成忍不住瞥了一眼,他?甚至不知道他認不認字。
翌日,皇帝考察功課。
李慶成站著,皇帝坐著,書房牆上掛著兩幅龍飛鳳舞的狂草:盛世天下,錦繡江山。
李慶成平生最愛這幅字,那字揮灑自如、,酣暢淋漓、,磅礴大氣,他不止一次朝父皇討過,皇帝卻從不答應。
李慶成不住打量自己父皇,皇帝老了。
四年前邊疆征戰落下了病根,父皇大部分時間半躺著,蓋條毯子,坐在龍椅上,鬚髮花白,老態龍鍾。
然而老龍威嚴,也是挺嚇人的。
「你自己作的文章?」皇帝聲音不怒自威。
李慶成猶如耗子見了貓,戰戰兢兢答:「是…………是兒臣自己作的。」
「背一次。」龍椅上那人慢條斯理。
李慶成斷斷續續,背了個大概,中間都忘了個光,太傅看不下去,岔道:「殿下近來念書還是挺勤奮的。」
李慶成笑道:「父皇,作文章的人,往往是背不出來的。」
老龍冷冷道:「休要胡攪蠻纏,以武得江山,以文治江山入題,立意尚可將就,然既起了個好頭,何不親力親為寫下去?起承轉合,你便獨力撰了個開頭收尾,中間俱請人代勞?」
李慶成穿幫了,硬著頭皮道:「沒……沒有,都是兒臣自己想的。」
皇帝把文章一扔:「回去重寫,若再讓青余捉刀,罰抄書百次。」
李慶成只得捧著文章,耷拉著腦袋走了。
「射箭練了不曾?」老龍的沉重聲音又道。
李慶成躬著身退了幾步,又抬起頭,說:「練了……昨日沒練,張慕…………看下雨,就沒讓兒臣出去。」
一名太監輕聲在皇帝耳邊說了幾句什麼。
皇帝吩咐道:「回去勤練射箭。」
「是、是。」李慶成如獲大赦,兔子般地跑了。
李慶成走出延和殿外,見數名朝中重臣恭敬等候,與他們打過招呼,往東邊去。心想若非老頭子有事要商量,自己說不得又得挨一頓教訓。
太子走後,太傅告退,一殿靜謐,皇帝方道:「你也回去罷,時時提點著慶兒,不可荒廢了武技。」
張慕從屏風後走出,說:「唔。」
皇上開始咳嗽,張慕似乎改變了主意,單膝跪地杵著,沒有起來。
皇帝知道他還有話想說,片刻後問:「還有事稟報?」
張慕不答話,皇帝擺手道:「孤身子不礙事。」
太監端上茶,張慕得到了答案,面無表情地再躬身,這次表示告退,走了。
東宮,龍央殿。
李慶成路過的時候,從馬車上掀簾子,朝外看了一眼,看到幾輛宮外的車。
有客人?李慶成心想,還是沒見過的,什麼來頭?皇后的娘家人?
太監通傳,李慶成進殿,滿殿清香,皇后一身淡紅繡袍,花團錦簇地坐在榻上,手肘倚著個小茶桌,端詳桌上棋盤。
皇后不是李慶成的親娘,對李慶成卻很好。
李慶成的親娘早死,皇后把太子撫養大,情同親母子,婦人年逾四十,卻保養得極好,絲毫看不出老態。
「兒臣拜見母后。」李慶成先道了安。
皇后道:「見過你父皇了?」
李慶成脫了外麾,交給宮人,笑道:「剛從父皇那兒過來,背書沒背上,挨說了。」
皇后似嗔非嗔看了太子一眼:「背什麼書,青余只說太傅讓你作文章,可不曾說什麼背書來著。」
李慶成嘿嘿笑:「青哥幫寫,沒背出來,露餡兒了,母后在看啥呢?」
皇后慵懶一笑,挽了頭髮:「剛妙音大師進宮裡來,給擺了個局,這不正看著呢。」
李慶成上前坐了,指道:「這局我見黃檻寺裡的和尚們擺過,名叫‘『反客為主’』,母後母后你看……」
李慶成一撩袖,應了白子,皇后輕輕地「咦」了聲。
「一子填了這個眼兒。」
皇后道:「倆子兒呼應著呢。」
李慶成:「你朝這位一鎮,牠倆不就解了?這枚主位上的掃掉……留顆旁的客子兒,也起不了什麼用。」
皇后秀眉微一蹙,袍袖攏了,笑吟吟看著李慶成的眼睛:「皇上今兒都和皇兒說了些什麼?」
李慶成嘴角一抿:「沒有說什麼。」
方青余在一旁笑道:「是屬下害了太子。」
李慶成掏了掏耳朵:「不是青哥的錯,母后,這局解了,你瞧。」
皇后嫣然一笑,心思又回到棋局上來,果不其然,李慶成一招反客為主,便把局解了個清楚。
「午膳咱娘兒倆一處吃罷。」皇后道。
李慶成想了想,說:「啞巴陪著我進宮來,也不知去了哪兒。」
皇后淡淡道:「待會兒喚人攥個食盒送去就是。」
宮人擺了桌,方青余依舊立於一旁伺候,李慶成道:「明兒可就中秋了。」
皇后道:「可不是麼,該做的功課都做了?你父皇宴請朝中的大人們那會兒,記得該說啥說啥。青余也給殿下提點著。」
李慶成笑道:「那是自然,都多少歲的人了。」
皇后調羹在碗裡劃拉,似有點心不在焉,午膳後著方青余把李慶成送回去。
夜。
張慕在廊前站著,太子和方青余在房內廝混,聲音不住傳來。
方青余長得實在英俊,五官精緻卻不失男子英氣,難得的是除去外袍,一身武人肌肉,膚色白皙,身材輪廓分明,腹肌健碩有力,猶如綢緞包著鋼鐵。
李慶成本對房事一知半解,十六年來,皇后也未曾給他指婚,數年前一次方青余喝了酒,李慶成便讓他躺自己床上醒酒,方青余睡得正酣,太子也躺了上去。一宿醉後本無事,太子夜半枕著方青余臂膀,便說起親近話來。
方青余半醉半醒,只不住口地哄著,懷中雛龍又別有一番意味,半大的李慶成問起男女之事,方青余當即半是調唆,半是玩笑地翻身,將太子給壓了。
那幾日恰逢張慕不在,否則李慶成叫聲足夠讓啞巴拔了刀,一刀送方青余上西天。
然而叫歸叫,方青余卻擔了十二萬分的小心,生怕李慶成痛怕了,入入停停,溫言軟語配著淺嘗輒止的手勁,調教一夜後太子竟是有滋有味,欲罷不能,只覺龍陽之興更在方青余所述男女歡情之上,當即對方青余更有種說不出的依戀。
方青余賣了力地討好,連著數日令李慶成嘗遍箇中妙處,白日間依舊鈕釦繫至衣領,談笑如沐春風,夜裡則趴太子榻上成了餓虎。
張慕歸來時亦是如此,太子威逼利誘,勒令啞巴不許把此事捅出去。
張慕只得神情複雜地點了頭,於是開始了聽牆角的侍衛生涯,人生最大悲劇,莫過於此。
一輪滿月高懸,月十四,銀光灑滿殿頂。
小太監吹了燈,方青余拉直衣領出來,朝張慕禮貌一點頭。
張慕也不回禮,便垂手站著。
方青余轉身走了,殿中傳來李慶成聲音:「啞巴,你還在外頭?」
殿門吱呀打開,小太監望了一眼,說:「回殿下,張大人還在外頭。」
李慶成的聲音懶懶的,帶著滿足與愜意:「入秋了冷,今天開始,不用守夜了。」說畢也不管張慕走沒走,裹著被子翻身,低低喘息,睡了。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鷹奴(上)(限)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鷹奴(上)(限)
統歷年間,太子李慶成安坐皇位身側常伴兩名侍衛,放逸風流,八面玲瓏,方青餘;孤僻寡言,訥直守信,張慕。
統曆十六年,朝堂傾覆,政權旁落;張慕帶著李慶成連夜逃離京城。自此,真龍困淺灘,唯有韜光養晦才能奪回皇權。
作者簡介:
非天夜翔
資深人氣網路小說作家。一個熱愛電影和冒險的旅者,一個努力感受世界的作者。
繪者
指尖糖
TOP
章節試閱
第一章
秋來香晚,一殿豔紅。
龍央殿外,跪著一名即將被處死的侍衛,大婚的鸞彩鋪了滿地,紅彤彤的布晃得扎眼,還有十天便是皇帝婚期。
金鑾椅上,虞國皇帝李效坐著,臉色陰沉。
大學士手執摺子,匆匆路過龍央殿,腳下不停,進了殿裡,一躬身。
「臣叩見陛下。」李效沉聲道:「賜座。」
兩名太監搬了椅子來,大學士一撣袖子,就著椅子邊小心翼翼地坐了,抬眼打量皇帝臉色,只一瞥,便即心裡有數。
李效是他看著長大的,自十六歲登基,至今六年,喜怒無常、嗜殺、暴戾、不近女色、無愛好,比虞國以往的任何一位皇帝都難伺候。
這...
秋來香晚,一殿豔紅。
龍央殿外,跪著一名即將被處死的侍衛,大婚的鸞彩鋪了滿地,紅彤彤的布晃得扎眼,還有十天便是皇帝婚期。
金鑾椅上,虞國皇帝李效坐著,臉色陰沉。
大學士手執摺子,匆匆路過龍央殿,腳下不停,進了殿裡,一躬身。
「臣叩見陛下。」李效沉聲道:「賜座。」
兩名太監搬了椅子來,大學士一撣袖子,就著椅子邊小心翼翼地坐了,抬眼打量皇帝臉色,只一瞥,便即心裡有數。
李效是他看著長大的,自十六歲登基,至今六年,喜怒無常、嗜殺、暴戾、不近女色、無愛好,比虞國以往的任何一位皇帝都難伺候。
這...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非天夜翔
- 出版社: 葭霏文創 出版日期:2017-12-29 ISBN/ISSN:9789869524360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04頁 開數:25
- 類別: 中文書> 漫畫/輕小說> B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