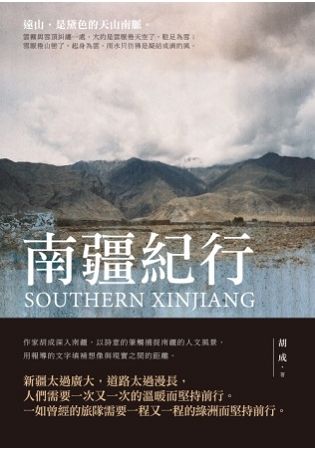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南疆紀行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40 |
二手中文書 |
$ 356 |
中國近代史 |
$ 396 |
中文書 |
$ 396 |
Others |
$ 405 |
社會人文 |
$ 405 |
旅遊 |
$ 405 |
歷史 |
電子書 |
$ 450 |
中國史地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Readmoo 評分:
圖書名稱:南疆紀行
……庫爾勒、若羌、且末、民豐、于田、和田、皮山、葉城、莎車、英吉沙、疏勒、喀什、塔什庫爾干、伽師、巴楚、阿克蘇、溫宿、烏什、拜城、庫車、輪台…… 26個日子,21個縣市,1個認識南疆的機會。
南疆,指新疆北起天山、南至崑崙山脈、以塔里木盆地爲中心的廣大地域。是古代絲綢之路的關鍵紐帶,亦是今日中國的敏感地帶。十三個世居民族生活在這片土地,同時亦有包括內地漢人在內的各省各族百姓陸續於此落地生根。民族與宗教混雜,加以政治情形牽引,使得大眾想像中的南疆始終神祕且充滿禁忌,對於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所知甚少。
本書是作家胡成親歷南疆的紀實之作,除了直擊各地漢人在南疆的生存現狀,亦側寫南疆複雜多元的民族與宗教文化,將這片土地的過往歷史與今日現實,一一呈現在讀者眼前。
南疆是神祕的,是禁忌的。
民族與民族之間,宗教與宗教之間,
橫亙着有如塔里木盆地的隔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