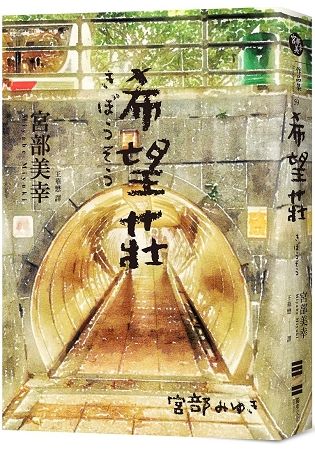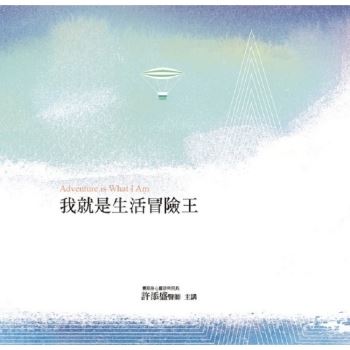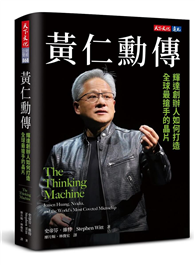圖書名稱:希望莊
【故事簡介】
要經過多少次劫難的洗禮,人生才能不留下絕望?
原本是童書編輯的杉村三郎,因邂逅財團千金,踏上與眾不同的人生道路。然而,看似圓滿的婚姻,以妻子的外遇畫下句點。他孑然一身返回故鄉,彷彿是命運的玩笑,在破解一樁不倫疑案後,找到發揮長才的路──成為私家偵探。
一日,一名男子上門,表示父親住院期間頻頻慨嘆「我殺過人」。他起先不當一回事,在父親離世後,卻愈來愈在意。杉村著手調查往昔的相關人士,竟找到最近一件女性遇害案的關鍵線索⋯⋯老人奇妙的遺言,是臨終的懺悔自白?還是,隱藏著難以啟齒的苦衷?
在生活的大震盪後,杉村又經歷311大地震。無法避免的社會裂縫,為他帶來一件又一件「尋人」任務:早該死去的老婆婆,打扮得雍容華貴出現在別處;女高中生希望能調查母親失蹤的戀人……杉村不禁懷疑,除了揭露真相,「偵探」還有什麼能耐?
【精彩內容摘錄】
「像我這樣的偵探,往後遇到的案子,應該是社會因311地震而改變、沒有改變、非改變不可卻無法改變、不想改變卻被迫改變──這些種種衝突造成的扭曲所形成的案子。」──摘自〈分身〉
▍作者簡介
宮部美幸Miyabe Miyuki
1960年出生於東京,1987年以《ALL讀物》推理小說新人獎得獎作〈鄰人的犯罪〉出道,1989年以《魔術的耳語》獲得日本推理懸疑小說大獎,1999年《理由》獲直木獎確立暢銷推理作家地位,2001年更是以《模仿犯》囊括包含司馬遼太郎獎等六項大獎,締造創作生涯第一高峰。
寫作橫跨推理、時代、奇幻等三大類型,自由穿梭古今,現實與想像交錯卻無違和感,以溫暖的關懷為底蘊、富含對社會的批判與反省、善於說故事的特點,成就雅俗共賞,不分男女老少皆能悅讀的作品,而有「國民作家」的美稱。
2007年,即出道20週年時推出《模仿犯》續作《樂園》。2012年,再度挑戰自我,完成現代長篇巨著《所羅門的偽證》。2013~2014年,「杉村三郎系列」《誰?》、《無名毒》、《聖彼得的送葬隊伍》接連改編日劇,2016年推出系列最新作《希望莊》。近著尚有《荒神》、《悲嘆之門》、《消逝的王國之城》等。
相關著作:《怪談:三島屋奇異百物語之始(經典回歸版)》《悲嘆之門(上)》《本所深川不可思議草紙》《獵捕史奈克(經典回歸紀念版)》《蒲生邸事件(經典回歸紀念版)》《逝去的王國之城》
▍譯者簡介
王華懋
專職譯者,譯有數十本譯作。近期譯作有《今晚,敬所有的酒吧》、《便利店人間》、《無花果與月》、《戰場上的廚師》、《花與愛麗絲殺人事件》、《破門》、《一路》、《海盜女王》等。
譯稿賜教:huamao.w@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