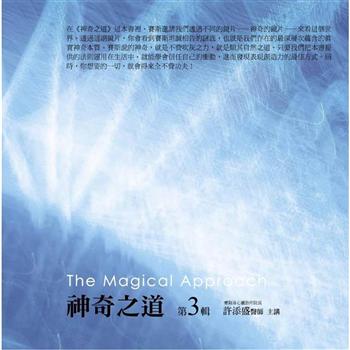圖書名稱:1921穿越福爾摩沙
1920年代的臺灣最繁麗生動的畫像
1921年4月,英國旅行家魯特夫婦橫越太平洋和大西洋,返國途中,他們從南到北穿越臺灣(西方人稱為福爾摩沙)。由於當時英國接納日本移民前往北婆羅洲開墾,魯特得以透過殖民地官員友人的介紹,成為臺灣總督府的貴賓,在總督府官員的隨行下遊覽日本的島嶼殖民地。
此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日本統治臺灣即將屆滿三十年,進入文官總督時期,實施內地延長主義。然而,民族自決風潮已至,臺灣人的議會請願運動方興未艾;戰勝國日本雖取得世界強國的資格,但日本移民卻繼華人之後成為「黃禍」而遭到歐美排斥,且與英國的同盟關係進入尾聲,菸毒輸入中國的問題也備受質疑。在這隱隱不安的戰間期開端,臺灣總督府為魯特呈現的是一幕幕產業與建設突飛猛進、朝氣蓬勃的景象;曾經擔任英屬北婆羅洲殖民地官員的魯特,卻在讚賞進步發達之餘,憑著自身的東方知識和經驗、對於臺灣歷史的廣泛閱讀,以及不受官方行程拘束的觀察力,敏銳察覺到日本殖民統治光鮮亮麗的背後眾多扞格不入、困窘挫敗之處,尤其是日本對臺灣原住民理蕃政策的缺失,他都在書中一一針砭並給予建議。
西方老牌殖民帝國管理者與考察者的目光,來到了東方新興強權苦心經營的模範殖民地,雙方在美麗之島交會,究竟擦出了怎樣的火花?又是怎樣的洞察,得以穿透展示櫥窗,為1920年代的東亞島嶼留下繁麗而生動有趣的畫像?在近一個世紀後重讀這本遊記,縱使物換星移,仍宛如親臨現場般令人回味無窮。
作者簡介 |
歐文.魯特(Edward Owen Rutter, 1889-1944),英國旅行家、文學家,歷史學者、殖民地官員。1889年出生於紐約曼哈頓,1910年開始在英屬北婆羅洲擔任殖民地官員。一戰期間他從軍參戰,先後在法國和巴爾幹前線作戰,諧擬朗費羅(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1807-1882)《海華沙之歌》的詩作《蒂亞達塔之歌》(Song of Tiadatha)是一戰期間戰爭詩的傑作,日後他據此寫成記述戰時遭遇的遊記。1921年,他與妻子一同環遊世界,自北婆羅洲出發,經臺灣、日本、美國、加拿大返回英國,完成跨越太平洋和大西洋的長途旅行,並於1923年出版《1921穿越福爾摩沙:一位英國作家的臺灣旅行》(Through Formosa : An Account of Japan's Island Colony,倫敦T. Fisher Unwin Ltd)。其一生著作豐富,除了遊記和小說創作、歷史事件的研究外,還有對北婆羅洲原住民族的民族誌寫作。他曾經是英國皇家地理學會、皇家人類學會會員,1933年成為金雞出版社(Golden Cockerel Press)的合夥人,在二戰期間任職情報部,負責編寫文宣書籍,介紹英國在戰爭時期的貢獻和努力。
譯者簡介 |
蔡耀緯,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現任職於永樂座。譯有《臺灣邊疆的治理與政治經濟(1600-1800)》(2016,合譯)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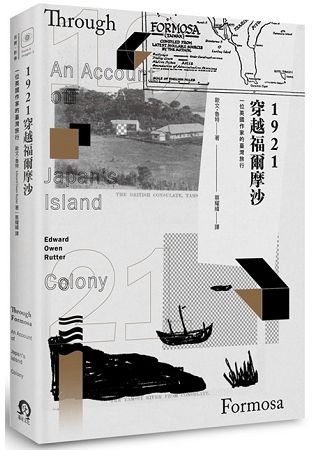

 2018/01/03
2018/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