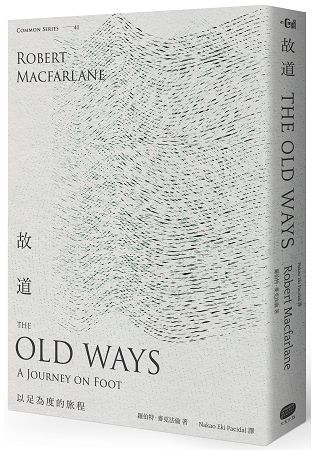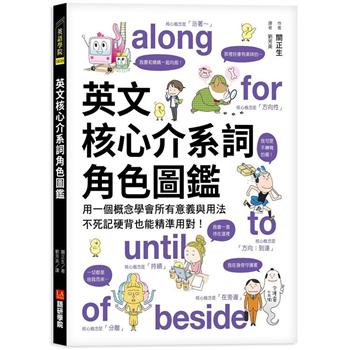圖書名稱:故道
每道轉彎可能都通往天堂
抑或每個角落都可能藏著地獄
故道,舊日之道,是小徑,是路跡,既非霸道的柏油路,也非單調的人行道。
故道由眾人日復一日踩踏出來。作者麥克法倫說:「路徑是大地的習性,是兩廂情願的造物。」大地向人類展示自身習性,那些起伏、彎折、質地,邀請人類行走其上,而人類只踩出一道足以落腳的地方,融入,不對抗。這是人類和大地的默契,一種最親密,也最詩意的關係。
我們在這種路徑上得到靈魂的救贖,那是朝聖之道。作者帶領我們走到西班牙聖雅各伯巡禮路、藏族貢嘎雪山轉山路,跟隨世上無數特立獨行的人踏上信仰之旅,相信某些向外出走的行旅,終將成為返回內心的旅程。有些路向我們揭露柔軟的自己,背後卻深埋死亡危機。作者走過的蘇格蘭泥炭路便告訴我們,要相信石頭,要始終能看到石頭,不要一看到平坦青綠的地面就受到誘惑而離開道路,因為那裡同時也是險惡的沼地。
於是作家托馬斯說,行走時,「每道轉彎可能都通往天堂,抑或每個角落都可能藏著地獄。」
海上也有道路,而且早在羅馬開始構築道路之前的三千年,海上已有密集的交通。若我們將地圖內外反轉,想像一個連結起港口和港口、島嶼和島嶼的行旅體系,想像海洋變成陸地,不再是邊緣,而是貿易和朝聖網絡的核心,聚落圍著大洋發展出共同的文化認同,共享文化、技術、工藝和語言,國界因而動搖崩漬——那是某一段時期的真實歷史。
英格蘭的白堊丘頂萬年古道,不但有起伏的丘陵、溪流、山毛櫸斜坡林、遍地野花的草原,更有石器時代的鬼魂。在以色列屯墾區,巴基斯坦人要追隨祖先漫步於「神聖之地」,得冒著被槍射死的危險。蘇格蘭赫布里底地區的蓋爾語中,有許多詩意地精準的詞彙,用以形容荒原景觀的特徵,其中一個是「Èig」,指的是「荒原河塘岸邊的石英石晶體,能捕捉並反射月光,因此在夏末和秋天時,會引來遷徙中的鮭魚」。
愛默生說:「萬事萬物都致力於書寫自身的歷史。」道徑上,處處是注記,那是人類、鳥獸、風、水流、陽光所留下的符號,而作者麥克法倫,便是這些注記的翻譯家。他以足為眼,閱讀大地、景物,並帶著重重叩問,不停追索人類為何自古便沈迷於行走,指出小徑穿越人心一如穿越地方,也指出步行不只是尋訪風景,向我們訴說:「這尤其是一本關於人和地的書:人透過步行而探索內心,而我們走過的地景,則透過種種微妙的方式形塑了我們。」
每條故道,由是皆指出一條通向遠方、回訪歷史、探戡內心的路徑。行走其上,正是在同時進行三段不同向度的旅程,觀看三種不同的風景。每走一回,都是一趟自我精神世界的尋訪之旅。
作者簡介
羅伯特.麥克法倫Robert Macfarlane
才氣縱橫的劍橋文學院士,專長當代文學,也是英國史上最年輕的布克獎評委會主席。
能寫擅走,至今已走了一萬多公里,也爬過許多險惡的山,自述「我的腳跟到腳趾的量測空間是29.7公分。這是行進的單位,也是思想的單位」。
被視為新一代自然寫作及旅行文學的旗手,以大量出色的文學修辭(尤其是隱喻)極度延展風景意象及深度,層出不窮的感官描述創造出人的內在風景和外在風景不停親密交流的感受。創新的寫作語言帶動大量評論,並啟發了新一波的地方寫作。當代旅遊文學名家William Dalrymple在書評中便點評道:在這些(顯示了旅遊寫作生生不息的活力,以及旅遊文學為每個繼起的新世代重新創造自己的能力)的所有新作家中,有一個人特別展示了文筆出眾的旅行書仍然可以美得如此渾然無瑕。那個作家就是羅伯特.麥克法倫。
創作領域包括文學、旅行與自然,也熟悉地形學及生態學,同時還能主持紀錄片。
書籍凡出版幾乎必得獎,首部作品Mountains of the Mind贏得《衛報》第一書獎、《週日泰晤士報》年度青年作家獎和Somerset Maugham Award。第三部作品The Wild Places同時獲得英國最重要的登山文學獎Boardman Tasker Prize和美國指標性的Banff Mountain Festival大獎,並改編為BBC節目。《故道》一書則 獲Dolman Prize for Travel Writing。
譯者簡介
Nakao Eki Pacidal(那瓜)
太巴塱部落阿美族人。荷蘭萊頓大學歷史學博士研究。譯有《地球寫了四十億年的日記》、《公司男女》、《西班牙人的台灣體驗》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