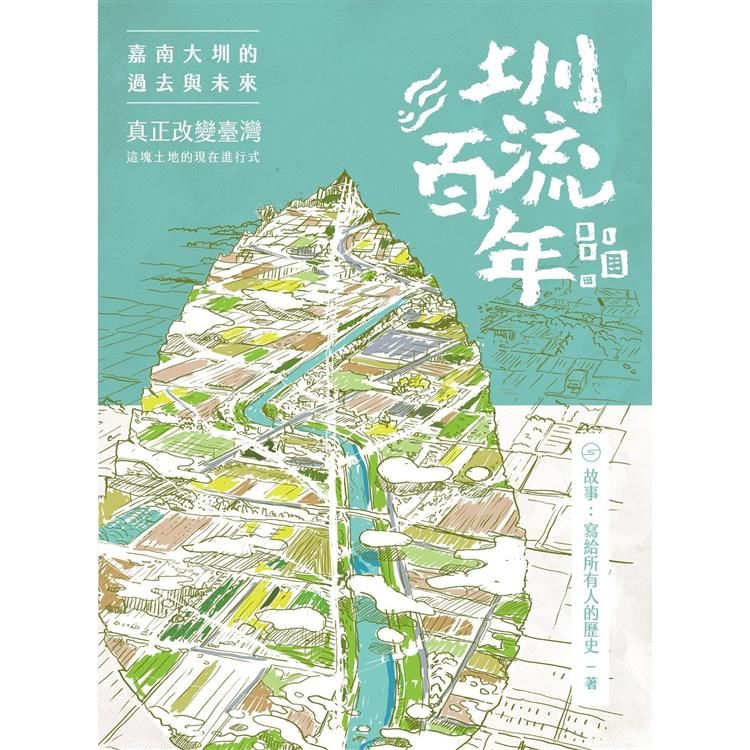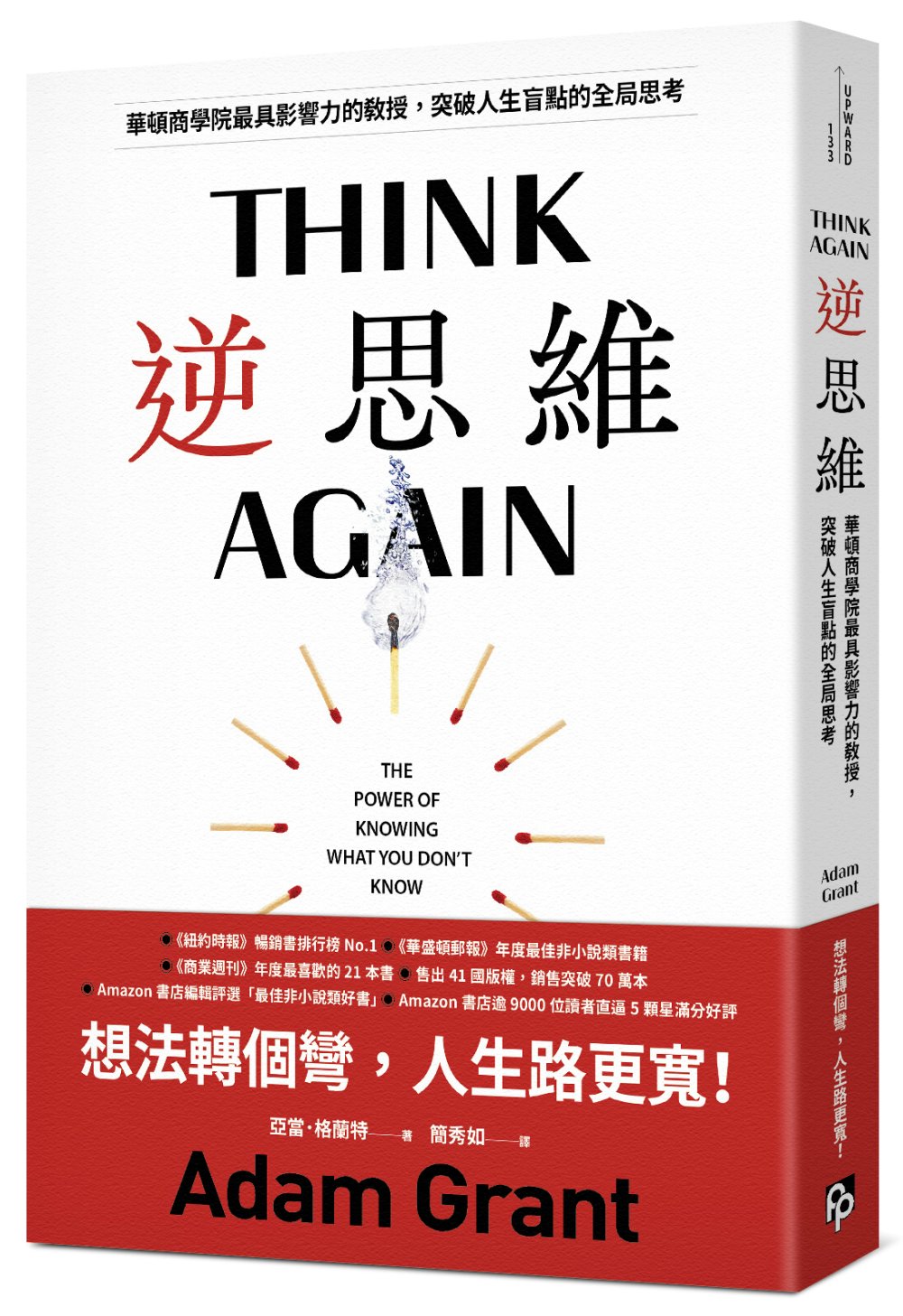其一〈米的日治臺灣史〉
你阿嬤吃的米不是你吃的米
米是亞洲諸國的主食,但是你吃的米跟你父母、阿公阿嬤吃的是同一種米嗎?很可能不是喔!
十七世紀初的文獻《東蕃記》中曾經記載臺灣:「無水田,治畬種禾,山花開則耕,禾熟,拔其穗,粒米比中華稍長,且甘香。」「畬」即是旱田的耕作方式,「禾」則是旱作的稻,也稱陸稻。後來,隨著漢人大舉移居臺灣,順勢移植了原鄉的耕作經驗與水田小區、精耕的經營模式,也引進當時的常用品種,於是原有的旱稻種原隨之被中國稻作主流──糯米與秈米所取代。
日治初期日本對臺灣稻米種類曾進行調查,結果顯示十九世紀末的臺灣總共有四百零三種稻米(水稻三百七十九種、陸稻二十四種)。水稻品種當中,又分成秈稻二百九十種、糯稻八十九種,顯示臺灣已大量種植秈米。
口感乾爽的秈米對當時臺灣人而言是習以為常的滋味,但日本人可吃不習慣。一八七三年,臺灣尚未割讓給日本,年輕的日本軍人樺山資紀祕密來臺進行調查和探勘,他怎樣也想不到,二十多年後,自己竟成了第一任臺灣總督。據說樺山在臺灣調查期間最不能適應的就是米飯,熱飯乾而鬆散,冷飯不黏也不香,讓他食不下嚥。
臺灣秈米有這麼難吃嗎?其實這是雙方飲食文化的差異所致。日本種植的「粳稻」較有黏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食物就是壽司跟飯糰,鬆散的臺灣米完全不是日本人喜歡的口感,當然會覺得難吃了。
臺灣米淹腳目:臺灣成為帝國米倉
明治維新之後,日本逐漸步入現代化,大量人口離開農村進入城市,農業產量無法滿足所需。日本政府雖試圖透過進口米糧來補充,但是隨著人口成長,米價始終居高不下,加上日本米一年只一穫,糧食供應有其風險。反觀臺灣米一年兩穫,生產相對穩定,於是在取得臺灣之後,當然就希望透過殖民地來解決母國的糧食問題。
因此,「農業臺灣,工業日本」就成了殖民統治的發展方針,總督府在臺灣採行米、糖二元發展的策略,積極推動農業改革工作,前述的私營水圳收歸國有、建設現代水利設施,都是在這個目標下推動而成。
一九○四年日俄戰爭爆發,激烈的戰爭讓日本產生嚴重的經濟恐慌,此時臺灣米不僅早成為日本本土重要的糧食來源,也曾支援前線,重要性大為攀升。為了確保輸入日本的臺灣米安全無虞,同年總督府開始實施「移出米檢查規則」,對臺灣輸往日本的稻米執行嚴格的品質檢查。
戰爭結束之後,日本國內的稻米不足問題浮上檯面,為確保母國的糧食供給,總督兒玉源太郎認為應該將臺灣的稻米生產納入日本糧食供需體系。於是總督府開始執行多項農業政策,計畫在臺灣進行稻米增產,並開始嘗試改良品種,努力讓臺灣米更為日本人接受。
家庭主婦意外啟動大圳建設計畫
第一次世界大戰(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爆發,讓遠離戰場的日本工業發了戰爭財,詎料隨之而來的通貨膨脹卻引發了「米騷動事件」,幾乎動搖了日本的國本。
這事件的遠因是日本長期米糧不足,吃不到米、物資貴得離譜一直讓百姓心中憋著一把火。導火線則發生在一戰末的一九一八年,日本眼看俄國發生革命,決定出兵西伯利亞擴大在亞洲大陸上的利益。消息一出,米商紛紛囤積白米,想再發一筆戰爭財,結果卻導致日本國內白米價格暴漲。
米價飆漲讓人直呼活不下去,日本一女工就曾投書報紙,她說自己一家三口人每月收入二十一到二十二圓左右,在付完米錢和房租後,買菜錢就沒了,這怎麼生活呢?
後來,不只是升斗小民活不下去,就連有國家供給的警察與監獄單位也都有類似的難題。
俗話說:「惹熊惹虎,毋通惹到恰查某。」米價的飆漲讓家庭中擔任採買的媽媽們義憤填膺。一九一八年,二百多名買不到白米而忍無可忍的富山縣主婦聚集街頭,群起要求官方降低米價,抗議不果之後,氣憤的主婦們最後竟然衝進米店搶米,甚至與警察爆發了激烈衝突。
這場「家庭主婦的逆襲」很快蔓延全國,名古屋、京都等主要城市都發生搶米暴動。數日後,大阪市民和工人暴動,搶光了二百五十多家米店;隔天在米商最集中的神戶也爆發幾萬名市民暴動,米店損失慘重,有的大商人不只店鋪遭到攻擊,連住宅也被憤怒的市民一把火燒掉。
米騷動總共波及三十八個城市,約一千萬人參與其中,就連首都東京也無法倖免。警察雖加強戒備,在各米店、工廠和富人住宅前加了崗哨,仍無力鎮壓,日本政府只好出動軍隊,花了一個多月才暫時平息。
米騷動後,日本政府意識到事態嚴重,開始整治零售業,也注意到必須確保穩定的糧食來源。於是日本政府斷然採取了殖民地的稻米增產措施,並著手規劃建設作為稻米生命線的水利灌溉設施。
米騷動不僅導致原有的內閣下臺,也讓臺灣至此走向文官總督體制,進一步對臺灣實施同化政策、內臺一體等政治方針。為解決國內缺糧問題,日本對臺灣和朝鮮進行了更積極的稻米增產措施。
比起稻米一年僅能夠有一穫的朝鮮和日本,一年足以兩穫的臺灣,在糧食生產上顯然更具有優勢。而且日本米一年只有十月收割,臺灣則可以在五月至六月、十月至十一月間收割兩次。更進一步來說,臺灣米可以在日本的舊米用盡、新米尚未收成前補充國內所需的產量。
面對來自殖民母國的壓力,臺灣總督府一直不斷尋找可栽培水稻的水田用地,並計畫建設灌溉工程。然而,原本十年計畫的官設埤圳工程,接連受到自然災害的影響,工程一再變更,最需要水的嘉南平原官設埤圳工程遲遲沒有進展。
歷史就是這麼巧妙,在米騷動尚未爆發前的一九一七年,總督府技師八田與一就曾提出「官佃溪埤圳計畫」來改善嘉南平原的農業用水問題,不過當時並未通過預算案。直到米騷動發生之後,政局紛擾不安,日本當局感受到相當大的壓力,在增產糧食的迫切需求下,終於批准上述建造案,嘉南大圳的建造計畫由此啟動!那那些點燃了米騷動的富山縣主婦們大概永遠不會想到,她們的舉動竟意外改變了臺灣吧!
其二〈滾滾不停的圳水,代代傳承的念想〉
從凋零轉向新生:再造大圳
食衣住行育樂,即使在充滿變化與不確定性的二十一世紀,仍有許多需求未曾改變。「民以食為天」,這亙古不變的真理或許能成為再造大圳的關鍵。文化資產保存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讓文化景觀融入日常生活,而不是只去維持失去功能的空殼,對於這一點,大圳早在數十年前就已做到──只是當今的臺灣人並沒有意識到它與生活必需品之間的連結。
王淳熙以自身耕種的經驗出發,給出頗有興味的思考方向:「人的基本生活就是要吃,但是如果你不去理解『吃』這件事跟土地之間的關係,你就只是『吃到食物』而已。」我們對食物的想像往往跟現實脫節,過去「沒吃過豬肉,至少也看過豬走路」的戲語在如今已是完全相反的意義。民生物質不虞匱乏,反而削弱了人們與土地的連結,市面上充斥大量加工品,讓我們用看不見產地、看不見材料原貌的食物餵養下一代。在根本不知道食物從何而來的情形下,我們又要怎麼讓孩子學習知足、去保護腳下這片養育他們的土地?
對於這個問題,陳鴻圖與王淳熙給出了同樣的答案:體驗。
因為沒有實際務農的經驗,多數人無法理解「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的辛勞,也對於農作物生長需要耗費的資源一無所知;未曾親眼目睹烏山頭水庫核心的運作,一般人無法知曉水利人員為臺灣的水資源做出多少奉獻。當人們對大圳與土地的認識只剩下一行行統計數據與文字敘述時,自然很難與之締結情感。
「我們需要的,是讓大家重新『注意到』大圳,以及大圳帶來的改變。」陳鴻圖以過去做研究的實踐精神為例,提議可以讓一般人去接觸農民、水利人員的工作,透過第一手經驗拉近民眾與這些工作的距離。
「我自己的小朋友也是在教科書上面學(跟大圳相關的知識),但是我發現只是這樣跟他們講並沒用,所以自己就安排全家在烏山頭水庫住了三天兩夜。」陳鴻圖說起自己如何帶領孩子認識大圳,以及親自接觸的經驗如何加深他們對整個大圳與水庫的印象,「我們從水庫出發,走了一段水路到東口去看整個灌溉景況,然後提醒他們:『你們看,《KANO》電影就有一段是在這裡拍的。』這樣一路走一路講,他們當然就會更了解嘉南大圳,也更了解八田與一。」
親身體驗的做法不只適用於大圳,而是整個人文教育都可以借鑑的思維。臺灣是有著豐沛自然資源以及多元歷史文化的寶島,身為西太平洋的交通樞紐,特殊的地理位置也吸引世界各國來此留下自己的足跡。這些足跡或許不屬於今日的臺灣人,但卻屬於這片名為「臺灣」的土地。我們依附這片土地而活,卻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慢慢忽略了這個事實;我們目光越放越遠,步伐越跨越大,但忘了注意腳下被踩踏的土壤。
不管是文資處、環保局介入維護,或是入選世界遺產潛力點,這些做法都是為了加深嘉南大圳在臺灣人民心中的印象。然而王淳熙認為與其一味向外尋求國際的認可,臺灣更需要從內部著手打下厚實的情感基礎。
「嘉南大圳的價值大多存在於臺灣人與臺灣歷史中,這或許不適合放到世界的層級去比較。客觀來講,嘉南大圳雖然大,但卻不是最大的。當時是『亞洲第三』,現在已經不是了,一直緊抓著這個不放反而會模糊我們看待大圳的焦點。」
「農村、或者是受到水圳灌溉的區域可以多舉辦一些活動,讓小孩子有機會去培養對這些水圳的感情。」陳鴻圖又以美濃獅子頭水圳舉辦的戲水活動為例,開放水圳給一般民眾玩水不只是活用水圳本體,更讓當地居民自然而然「關心」起這條與他們生活密切連結的水圳─畢竟,沒有人會希望自己的孩子泡在有汙染疑慮的河水中。其他如彰化八堡圳「跑水祭」、桃園大圳「騎單車遊大圳」等活動也都是嘉南大圳很好的學習對象,讓水利設施融入大家的日常生活,提升非農民對大圳的情感。
期許下一個百年
水,是一切的根本。沒有水的滋養,作物無法生長,資源不足就會限制人類社會的進步。即使我們平時接觸不到嘉南大圳與其他水利建設,卻仍會間接接受到水圳的滋養。
「同樣是北緯二十三.五度,非洲那邊可是撒哈拉沙漠啊!」陳鴻圖的一句笑語,點出嘉南大圳對臺灣的最大貢獻。因為嘉南大圳百年來的灌溉,才讓臺灣有現在的繁榮基礎;百年後的今天,我們應該回過頭想想如何照顧嘉南大圳了。
再造大圳的重點在於「造」字,既然臺灣已經沒辦法回到百年前的農業社會,生生不息的大圳自然需要被賦予新的意義與核心價值。嘉南大圳百年來經過硝煙砲火的洗禮、撐過產業變遷的衝擊,其存在的意義本就隨著社會進步不斷被重新檢視。時代在變,人也在變,誰也說不清楚下一個百年會是什麼樣子。「從某個角度來說,臺灣人沒有辦法等待太長的時間。但是這些事情幾乎是需要以『世代』為單位的時間來轉變。」講到臺灣人急躁的天性,王淳熙十分語重心長。
再造大圳所要挑戰的是社會結構上的革新,因此更需要建立一套能長久維繫人與土地、與水源之間連結的「觀念」。唯有觀念正確,我們才能看清自己的處境與目標,再視需求去整合各領域的資源,制訂相應的策略。
嘉南大圳百年來養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臺灣人,但一百年過去了,時代已然不同,現代面對的挑戰遠比過去更加嚴苛。八田與一所設計的大圳如同一輛老爺車,雖然跑起來吃力卻不會拋錨,如今的水利會也面對著比水利組合更大的挑戰,一方面得用新科技與現代工法給老爺車汰換零件,另一方面則要扛起農業轉型、組織轉型的艱鉅任務。
但無論如何,我們都要謹記嘉南大圳是為農業而生的設施,如果沒有了農地、沒有了農民,大圳也將失去生存的意義。
「大圳的美,是來自於大圳賦予土地、賦予農業生命力的景觀。因為有水圳,所以有農田;因為有農田,所以有水圳。如果今天農田不存在了,水圳就會變成水溝。」王淳熙帶著深情道出大圳與土地之間的共生關係。
倘若沒有了平原上的萬頃良田,沒有了良田上種植的臺灣米糧,沒有了奔流不息的嘉南大圳,嘉南平原會是什麼模樣?
| FindBook |
有 10 項符合
圳流百年:嘉南大圳的過去與未來──真正改變臺灣這塊土地的現在進行式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圳流百年:嘉南大圳的過去與未來──真正改變臺灣這塊土地的現在進行式
★嶄新的角度:採「大歷史」的格局,將大圳視為生命體進行整體闡述,並將焦點放在與大圳互動的人們,捨棄過往只關注大圳工法或八田與一生平的寫法。
★精美的插圖:將諸多敘述文字轉譯成圖像表達,把無數繁雜數據改造成易懂畫面,增加閱讀的愉悅感。
★全面的梳理:寫八田與一,也寫建設工程的人員與使用大圳的農民;記大圳的具體建設,也記大圳的無形影響;論百年前國際情勢的連結,也論百年後該如何面對挑戰、重獲新生。
★臺南市市長黃偉哲、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局長施國隆、臺南市政府文化局局長葉澤山、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陳文松、「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共同創辦人蕭宇辰專文推薦
★東華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陳鴻圖、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蔣竹山聯袂推薦
「烏山頭水庫暨嘉南大圳」自1930年竣工以來,蘊育了豐碩的嘉南平原,對臺灣農業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在大圳灌溉範圍內,因不同地區的土壤環境與距離渠道遠近,形成多樣灌溉模式、農業地景及與大圳的互動方式。
為什麼要認識嘉南大圳?是因為它曾是亞洲第三長的灌溉水渠嗎?還是它運作了上百年,放眼世界也是極為罕見?抑或是它改變了整個嘉南平原的景觀、克服了降雨不均的隱患,逆轉了天與地的限制?
是的,但也不僅只是這樣。
本書採用全新的嘗試,不再過度著墨於嘉南大圳的實體建設過程與細節,而是從「大歷史」的角度,詮釋這等大型水利設施的建造必要性和轉機,以及其與東亞局勢、帝國布局的對應關係;從「那時人」的感受,側寫大圳帶來的正面助益與負面糾葛,延伸到官方、民間對於水源的管理與分配;更從「當代人」的視野,檢視走過百年滄桑卻仍運作如常的嘉南大圳所帶動的環境變化、產業變遷,反思大圳該如何迎接下一個百年。
一條大圳映照出了這塊土地上統治者與生活者的諸多面貌,乃至於人類與環境如何共生的多元故事,多麼有趣。在嘉南大圳開工百年、使用落成九十年之際閱讀本書,你將更能感受到臺灣這塊土地不斷改變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延伸思考一】嘉南大圳的七大謎團:
一、烏山頭水庫預計可用五十年,為何一用百年未損?
二、日本家庭主婦引起的全國暴動竟然催生嘉南大圳?
三、縱貫線以西的土地原本鹽分很高只能挖魚塭,為何今日遍布水田?
四、在地理上,濁水溪、曾文溪由東向西各自奔流,但水流竟然相通?
五、「咬人」大圳?嘉南大圳促進農業發展,為何會成為咬人的大圳?
六、「水利會」負面消息不斷,為何卻能從日治時代到今日依舊存在?
七、開鑿大圳破壞聚落風水,土裡因而冒血,居民因而猝死,真的嗎?
/////【延伸思考二】嘉南大圳的三大影響:
一、有了嘉南大圳,從此降雨不均的問題不再困擾農民!
二、嘉南大圳對於嘉南平原的地質,產生根本性的扭轉!
三、隨嘉南大圳而來的農業變化對臺灣的發展至關重大!
作者簡介:
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StoryStudio)
由一群喜歡故事的人於2014年成立,致力於知識傳播、公眾教育與文化體驗,結合創意與數位技術,讓歷史與文化走進每個人的生活,和閱聽者一起「從生活發現歷史,從臺灣看見世界,從過去想像未來」。
提倡有根的世界主義(rooted cosmopolitanism),既能在地又能超越在地;立足臺灣,同時關懷跨越國際的文化與政經議題。期能召喚關心文化、喜愛學習新知,並對世界充滿好奇的你,一起在數位時代打造新的知識共和國。
官網https://storystudio.tw/
臉書https://www.facebook.com/gushi.tw/
▌作者其他著作
《故事臺灣史:10個翻轉臺灣的關鍵時刻》、《故事臺灣史:22個改變臺灣的關鍵人物》,親子天下,2019.9
章節試閱
其一〈米的日治臺灣史〉
你阿嬤吃的米不是你吃的米
米是亞洲諸國的主食,但是你吃的米跟你父母、阿公阿嬤吃的是同一種米嗎?很可能不是喔!
十七世紀初的文獻《東蕃記》中曾經記載臺灣:「無水田,治畬種禾,山花開則耕,禾熟,拔其穗,粒米比中華稍長,且甘香。」「畬」即是旱田的耕作方式,「禾」則是旱作的稻,也稱陸稻。後來,隨著漢人大舉移居臺灣,順勢移植了原鄉的耕作經驗與水田小區、精耕的經營模式,也引進當時的常用品種,於是原有的旱稻種原隨之被中國稻作主流──糯米與秈米所取代。
日治初期日本對臺灣稻米種類曾進行調...
你阿嬤吃的米不是你吃的米
米是亞洲諸國的主食,但是你吃的米跟你父母、阿公阿嬤吃的是同一種米嗎?很可能不是喔!
十七世紀初的文獻《東蕃記》中曾經記載臺灣:「無水田,治畬種禾,山花開則耕,禾熟,拔其穗,粒米比中華稍長,且甘香。」「畬」即是旱田的耕作方式,「禾」則是旱作的稻,也稱陸稻。後來,隨著漢人大舉移居臺灣,順勢移植了原鄉的耕作經驗與水田小區、精耕的經營模式,也引進當時的常用品種,於是原有的旱稻種原隨之被中國稻作主流──糯米與秈米所取代。
日治初期日本對臺灣稻米種類曾進行調...
顯示全部內容
推薦序
因水而起──陳文松(成功大學歷史系教授)
嘉南大圳,也就是烏山頭水庫以及整個涵蓋雲嘉南地區灌溉系統的給水路網,從1920年動工興建到1930年正式完工,前前後後花了整整十年,終告完成;2020年,也就是迎接嘉南大圳動工興建的一百年。從百年前與迄今一百年之間,這一片廣大土地與無數人民,期間經歷了從日治到戰後不同政權的統治,究竟產生何種重大的改變?而日後又將面臨何種挑戰?本書正是要引領我們去思考這些問題。
本書所稱「圳流百年」可能已是大家從小聽到大的故事,包括嘉南大圳的總工程師兼設計者八田與一,包括三年輪作制等...
嘉南大圳,也就是烏山頭水庫以及整個涵蓋雲嘉南地區灌溉系統的給水路網,從1920年動工興建到1930年正式完工,前前後後花了整整十年,終告完成;2020年,也就是迎接嘉南大圳動工興建的一百年。從百年前與迄今一百年之間,這一片廣大土地與無數人民,期間經歷了從日治到戰後不同政權的統治,究竟產生何種重大的改變?而日後又將面臨何種挑戰?本書正是要引領我們去思考這些問題。
本書所稱「圳流百年」可能已是大家從小聽到大的故事,包括嘉南大圳的總工程師兼設計者八田與一,包括三年輪作制等...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推薦序──臺南市市長黃偉哲、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局長施國隆、臺南市政府文化局局長葉澤山、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陳文松、「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共同創辦人蕭宇辰
第一章、嘉南大圳的年度行事曆
>>>闡述水圳一年四季的工作情形。
第二章、大圳誕生之前的故事
第一節嘉南平原的形成與天然限制
第二節日治初期的水利政策
第三節米的日治臺灣史
>>>除了介紹大圳原生地景、地貌之外,還有促成大圳興建的契機──絕對出人意料。
第三章、建設大圳:從藍圖修改到工安事件
第一節要選哪一款大圳?
第二節一九二〇,大圳...
第一章、嘉南大圳的年度行事曆
>>>闡述水圳一年四季的工作情形。
第二章、大圳誕生之前的故事
第一節嘉南平原的形成與天然限制
第二節日治初期的水利政策
第三節米的日治臺灣史
>>>除了介紹大圳原生地景、地貌之外,還有促成大圳興建的契機──絕對出人意料。
第三章、建設大圳:從藍圖修改到工安事件
第一節要選哪一款大圳?
第二節一九二〇,大圳...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