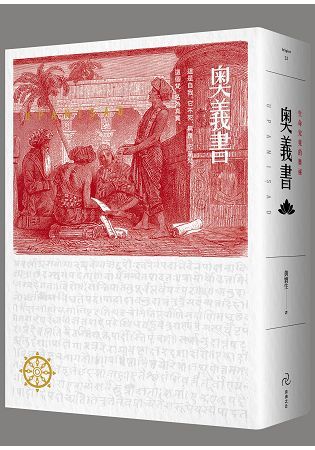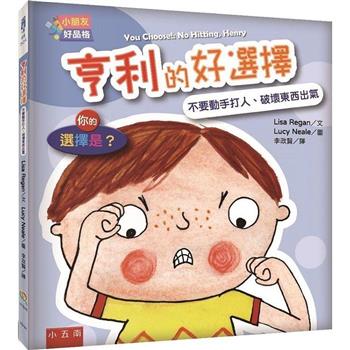在世界上,沒有比研讀『奧義書』更令人受益和振奮的了。
它是我生之慰藉,也將是我死之慰藉。
──哲學家叔本華
它是我生之慰藉,也將是我死之慰藉。
──哲學家叔本華
「這是自我。它不死,無畏,它是梵。
這個梵,名為真實。」
《奧義書》與《吠陀經》及《薄伽梵歌》同被譽為是印度三大聖典。而《奧義書》標誌了印度從崇尚天神的「祭祀之路」,轉向了探討生命究竟奧祕的「知識之路」,在印度思想史上占有極為重要地位,對印度宗教和哲學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奧義書》的核心內容是探討世界的究竟之因和人的本質。其中的兩個基本概念是「梵」(Brahman)和「真實自我」(atman,真我、靈魂)。《奧義書》由吠陀發展而來,在吠陀頌詩中,確認眾天神主宰一切;而在奧義書中,確認了梵是世界的本源。
印度上古時代也稱吠陀時代(約自西元前二千前始),並形成種姓社會制度,分成四種種姓:第一種姓婆羅門是祭司階級,掌管宗教;第二種姓剎帝利是武士階級,掌管王權;第三種姓吠舍是平民階級,主要從事農、牧、手工和商業;第四種姓首陀羅是低級種姓,主要充當僕役。從四種種姓排列次序就可以看出,婆羅門祭司在社會中居於首要地位。《吠陀經》主要是頌神、祈禱等詩文集,表明了印度吠陀時代是崇拜神祇的時代,熱衷祭祀。
在印度上古初民的心目中,人間一切事業的成功都依靠天神的庇佑,而婆羅門主導祭祀活動,並在祭祀活動中接受布施和酬金,是最大的實際受益者。祭祀本身成了最高目的。包括天神在內的一切力量都源自祭祀。而婆羅門執掌祭祀,也被提高到等同天神的地位。婆羅門的祭祀理論在吠陀晚期達到鼎盛。
一千多年之後(約自西元前八百年始)到了吠陀晚期,開始出現各種《奧義書》。《奧義書》並不是一部經典,而是當時哲學文獻的總稱,它超越吠陀經典,突破祭祀主義樊籬,可以說是在婆羅門教內部發生的一場思想革命。婆羅門一向壟斷知識,崇拜神祇,推行祭祀主義,已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思想領域中的革故鼎新勢在必行。《奧義書》又被稱為「吠檀多」,即「吠陀的終結」,展現了對於祭祀和人生的另一種思路。
《奧義書》來自於那些摒棄世俗祭祀、也摒棄世俗生活方式的聖人隱者,他們遠離了城鎮和鄉村隱居在森林裡,並祕密傳授關於生命的真義。這些作者強調內在的或精神的祭祀,以區別於外在的或形式的祭祀。《奧義書》名稱的原義即是「坐在某人身旁」,蘊含「祕傳」之意,表示了「奧義」或「奧祕」,因此《奧義書》也成為研究神祕主義(密契主義,Mysticism)的著作。
現存於世的《奧義書》多達二百多種,有些成書甚至晚至十六世紀。現代研究學者公認與吠陀時代末期思想密切相關的《奧義書》只有十三種,即本書所翻譯出的「十三奧義書」,包括散文體及詩體,產生年代約在西元前七、八世紀至西元初期。
「這是我內心的自我,小於米粒,小於麥粒,小於芥子,小於黍粒,小於黍籽。
這是我內心的自我,大於地,大於空,大於天,大於這些世界。
包含一切行動,一切願望,一切香,一切味,涵蓋這一切,不言語,不旁騖。」
在《奧義書》中,「梵」作為世界本源,而「自我」一詞常常用作「梵」的同義詞,也就是說,梵是宇宙的自我、本源或本質。而「自我」一詞既指稱宇宙自我,也指稱人的個體自我,即人的本質或靈魂。梵是宇宙的本源,自然也是人的個體自我的本源。正如《歌者奧義書》中所說:「這是我內心的自我。它是梵。」
在《奧義書》的創世說中,世界最初的唯一存在是自我,由自我創造出世界萬物。這個「自我」也就是梵。《大森林奧義書》中指出:「正像蜘蛛沿著蛛絲向上移動,正像火花從火中向上飛濺,確實,一切氣息,一切世界,一切天神,一切眾生,都從這自我中出現。」按照《奧義書》的種種描述,梵創造一切,存在於一切中,又超越一切。
與梵和自我的關係相關聯,《奧義書》中也探討宇宙和人的關係。在探討這種關係時,《奧義書》中的常用語是「關於天神」和「關於自我」。「關於天神」指關於宇宙,「關於自我」指關於人體。宇宙和人都是梵的展現,也就是以梵為本源。在《奧義書》的描述中,宇宙中的自然現象與人體的各種生理和精神功能具有對應關係。《大森林奧義書》將宇宙中的水、火、風、太陽、方位、月亮、閃電、雷和空間,分別與人的精液、語言、氣息、眼睛、耳朵、思想、精力、聲音和心相對應,並且確認宇宙中的「原人」和人體中的「原人」都是「這自我」,換言之,「這是甘露,這是梵,這是一切」。
《奧義書》將「梵」和「自我」視為最高知識。知道了梵和自我,也就知道一切。認識到「梵我合一」,也就獲得解脫。《歌者奧義書》中說:「這是自我。它不死,無畏,它是梵。這個梵,名為真實。」然而,在日常生活中,「真實」常被「不真實」掩蓋:「正像埋藏的金庫,人們不知道它的地點,一次次踩在上面走過,而毫不察覺。同樣,一切眾生天天走過這個梵界,而毫不察覺,因為他們受到不真實蒙蔽。」因此,《奧義書》自始至終以揭示這個「真實」為己任。《奧義書》確認梵為最高真實,以認知「梵我合一」為人生最高目的。
圍繞梵和自我的中心論題,《奧義書》還涉及其他許多論題,提出不少新觀念。其中包括「業」和「轉生」的觀念。而《奧義書》追求的人生最高目的是認知梵,達到「梵我合一」。人死後,自我進入梵界,擺脫生死輪迴,不再返回,自然是達到「梵我合一」之境。
在《奧義書》之後產生的印度古代哲學中,「吠檀多哲學」是《奧義書》的直接繼承者。而「數論」和「瑜伽」也能在《奧義書》中找到淵源或雛形。在《奧義書》中,數論和瑜伽是作為認知梵的手段或方法。
十九世紀初,法國學者迪佩隆(A. Duperron)依據波斯文譯本,將奧義書翻譯成拉丁文,題名為Oupnekhat,其中含有五十種奧義書。當時,德國哲學家叔本華讀到這個譯本,給予奧義書極高的評價:「在整個世界,沒有比研讀奧義書更令人受益和振奮的了。它是我生之慰藉,也將是我死之慰藉。」他也在《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一版序言中推崇奧義書,說道:「我揣測梵文典籍影響的深刻將不亞於十五世紀希臘文藝的復興,所以我說讀者如已接受了遠古印度智慧的洗禮,並已消化了這種智慧,那麽,他也就有了最最好的準備來聽我要對他講述的東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