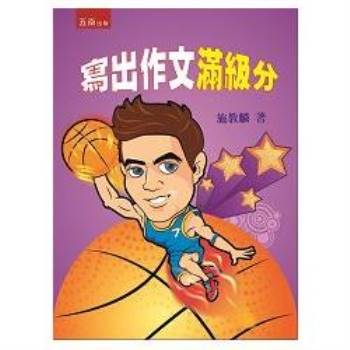如果有一種愛,需要許以千年的誓約,這份愛,可以抵得住所有的打擊與背叛嗎?
都說父親是最初的戀人,被剝奪父愛之後,女兒可以如何堅強卻又偽裝地存活下來?四位各有一方天地的傑出女性,在其美好的外表下,卻因著歷經白色恐怖的童年歲月,而讓她們的感情路顛顛撲撲:知名的編劇幼年遇刺,驚惶不安的家居日常是她的生活寫照,離婚後再遇一個美好的對象卻遲遲不敢面對自己的真心;活潑的藝術家看著父親在自己面前被警總一臉是血地拖走,自此別離十一載,總說自己被偷走了十一年的青春,轉而與年輕男子交往;自美返台的大提琴家原該展開舞台生涯的,卻因為父親的緋聞從此告別舞台,藏身在音樂教室裡教琴,苦戀著有了丈夫的女人;唯一在幸福婚姻關係中的,也曾是跌跌撞撞,心裡永遠住著小警總的大學老師。父親缺席的童年讓這些女性不得不自立自強,但這樣的人生到底產生了甚麼副作用?白色恐怖的扭曲時代對一個世代的某些女性又造成什麼影響?
作者不想以苦難紀實的方式去記錄一段歷史,而是選擇以愛情故事述說原生家庭對人一生的影響,特別是在一個高度政治扭曲的社會底下,狀似美好的外在,卻有著傷痕處處,不為人知的內在,只有在最細微處,才得以察覺。原來,受苦難的不會只有受難者的家庭,其實是整個社會,都是受難體,許多我們以為很遙遠的,毫無干係的,卻也深受影響,人生驟變...
本書特色
作者的父親當年親歷白色恐怖,身為白恐第二代,一出生父親就待在牢裡,母親獨力照顧她和姊姊。一晚母女三人外出返家,發現門鎖被撬開,但被搜了個天翻地覆的家裡卻甚麼也沒丟,臨睡前掀開棉被,赫然發現一把菜刀正躺在那裡,無聲地威嚇著小女孩,這暗示了她逃過的是另一種命運,也同時讓她了解到,家,原來是這樣的不安全。在白色恐怖的那個年代,她甚至因為父親是政治犯而被叫到司令台接受師長同學恥笑,這不是小說,這是真實人生。
這樣的人生,如果不夠堅強,許多時候是會想要把自己藏起來的,而這本書名《向著光飛去》, 正是她與許多人內心真正的渴望。
作者簡介:
施又熙
實踐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原名施珮君,2012年改名。1969年生於高雄市白色恐怖家庭,一生與知名父母有著難以擺脫的糾結,矛盾的情緒每每在作品中不斷呈現。從小展露寫作天分,高中時兩度獲校內大獎,卻因背景與自我認同的矛盾衝突,18歲即成文字逃兵,直至36歲才為自我的療癒而重新提筆,目前定居於新北汐止。
專擅刻畫人性,無盡黑暗處仍可得見溫暖陽光。走出憂鬱風暴後,近年加入社福團體宣導精神醫學與心理衛生,文字更添理性與療癒之風。
2013年首度嘗試舞台劇劇本,啼音初試即獲獎,作品並於2014年台北嘉義兩地公演。
目前除專職寫作,亦教授書寫療癒課程、精神障礙者家屬教育團體,並以文學與精神醫學等相關議題於各大專院校演講。著有長篇小說《月蝕》、《五芒星的誘惑》,散文集《風與南十字星的對話》、《勇敢》、《媽咪,我們會這樣幸福多久?》,傳記文學《台灣查某人的純情曲—陳麗珠回憶錄》,劇本《多桑的百合花》。
其他作品散見《網氏電子報—邊境真相》專欄,及以下網站:
痞客邦:http://teresashih.pixnet.net/blog
臉書粉絲專頁:書寫。療癒。施又熙
章節試閱
謹將此書獻給
在那個幽微時代下不被看見的孩子們
受難長輩們
我的母親 陳麗珠女士
我的寶貝 王芃
以及
一直給我支持打氣的大哥 陳立宏先生
這是一個與時代緊緊繾綣的故事,
命運如是,
愛,
亦然。
序曲
「那一年,就在我最需要你的時候,你就這樣離開了,你知道後來那十多年我是怎麼熬過來的嗎?你知道你被抓走之後,我跟媽媽弟弟過著怎樣的日子嗎?你知道我在學校是怎樣的被欺負嗎?你還記得那時候我只有十四歲嗎?十四歲!這些年來你有問過我們那段日子是怎麼過的嗎?」新芳嘶吼著,對著她的父親聲淚俱下。
兩鬢早已花白的杜文只能眼睜睜看著女兒的淚水,喉頭堵著,兩手垂在身旁,雙拳緊握仍忍不住抖著,不知道如何回應這樣的指責。
「說話啊!」新芳憤怒地瞪著父親,而父親仍是一逕地沈默。她不是沒有看到父親的反應,她看到他緊握發抖的雙手,但這麼多年來他總是如此沈默,離開火燒島回家已經十年了,火燒島像個禁忌的話題,他從來不問他不在時,她與媽媽、弟弟如何度過,但新芳明明就知道火燒島不是禁忌,她明明就看過、聽過他與難友在一起時會講起那段歲月,可就偏偏不問她,也不在家中提及。
柳絮靠在一旁的柱子上靜靜地凝視著,心口緊緊的。
「你只會這樣。」新芳眼裡的憤怒漸漸冰冷,再看沈默的父親一眼,近似絕望地轉身甩門而去。
望著被女兒甩上發出巨響的大門,『我不是不想問,』杜文心裡低喃著,轉身走過楞在一旁的,年華早已老去的妻子秀美,回到自己的書房,輕輕地闔上門。蹲坐在書房的角落地板上,這小小的一方斗室,彷彿終生抹煞不去的看守所押房,是他心靈最深的痛,卻也是最習慣的地方,『我是不敢問啊!』從不在外面顯露的悲傷,隨著一行淚水滴落在木造的地板上,濺出煙花般的印記,也像槍決時從卡賓槍管裡噴出的火花。
「好!這場OK了!」導演陳信真拍了一下手,「下一場準備!」對著剛從布景側面繞過來的女演員說道,「新芳去補個妝,下面是第六場,妳回到家,看到媽媽…」
扮演杜文的周慕夏抹去淚水,稍稍轉換情緒後從地上站起,轉頭搜尋著習慣站在陰影處的柳絮,扮演妻子的女子走過來跟他說話。
柳絮在周慕夏尋著她的身影前便沈默地退到攝影棚外,不自覺地屏著氣走經化妝區,彩妝師阿毛抬頭看見她,「柳絮,妳要走了嗎?」
柳絮聽見這聲音才驚醒般地吐出那口氣,露出陽光笑臉點點頭,「對啊,我要回家準備圍爐的火鍋,新年快樂喔。」
「嗯嗯,新年發大財啊!」阿毛樂觀地回應著。
「好喔,我們都很需要。」柳絮笑著說道,沿途跟相遇的劇組工作人員互道新年快樂,走出電視台寒慄襲來,忍不住打了冷顫,卻沒有立刻穿上手中的大衣,只是深深地呼吸著這樣冷冽的空氣,臉上的笑容慢慢卸下。
在這除夕的傍晚,台北是一貫的清冷,也好,對於柳絮來說,人少點的地方總是讓她自在一些。彷彿像是冷夠了,全身開始發抖才穿上大衣往自己停車的地方走去。
這風,真的很冷,柳絮手上拎著手套與一條圍巾,厚厚軟軟的,摸著是種溫度,暖暖的,心裡卻總是不踏實,像她的人生、她的一切,也像她的愛情,她慢慢地圍上圍巾並且戴起手套,如果周慕夏知道又該叨念了。
走在人行道上,心裡頭卻一直縈繞著剛才的拍攝現場,那些都是她寫的場景與對白,再熟悉不過的內容在眼前演出,即便只是角色扮演,也揪著她的心,擰著她的呼吸,過去一直逃避的人生場景,這幾年她反撲似地開始訴說從小到大她所理解的世界,那個與社會大多數人疏離的世界。
寒風中走了一小段路,放在大衣口袋裡的雙手感覺到手機的震動,看了一眼來電顯示接起電話,「喂?」
「是我。」電話那頭不是剛才杜文的老聲,而是周慕夏低沈的嗓音,他人高馬大,可講話總是一派的低聲優雅,除了演戲的劇情需要之外,彷彿沒聽過他揚起嗓門講話,就算在學校教課也是如此。
「我知道。」
「妳走了嗎?那場戲一結束就沒看到妳。」
「嗯。」柳絮走到自己的車子旁停下來講電話,看著路上稀疏來往的車輛。
「妳還好嗎?」周慕夏其實已經習慣柳絮不時這樣沈默或簡短的回應,相較於其他仰慕他明星光環的女性來說,通電話的這位女子是非常獨特的存在。他與柳絮交往已經四年多了,柳絮始終有著心態上若即若離的狀態,有時候溫暖而熱情,有時候推開他人只活在自己的世界裡。初始以為是她難以親近,後來發現並非如此,而是她總被一些過往的傷痛困擾,特別是這次的劇本雖然得獎並且深受公司與導演的喜愛,但他也知道柳絮前年一整年,在這個劇本的創作過程中是如何地被自己的記憶與傷痛折磨著。
「沒事啊。」柳絮回應著,眼睛望著對面街道上一對中年人牽著手,另一手提著超市的提袋裝滿蔬菜地從超市走出來,她不是刻意冷淡,只是不想讓人為她擔心,不管那個人是誰,不管是不是她愛的人或是愛她的人。
「我應該午夜前可以結束這邊的工作,晚點去找妳?」周慕夏繼續問著。
柳絮把玩著手上的車鑰匙,「今晚可能不方便,你知道千榕跟文心她們要來圍爐,起碼會到半夜或天亮後才離開,而且你也累了,拍了一整天的戲,你應該多休息的。」
周慕夏沈默了數秒,掂估著她的心情,知道她這幾年來的除夕都會有幾位與她生命經驗相仿的女性友人到她家裡圍爐守歲,這對她們來說是重要的相聚,或許不見得會談及那段苦難歲月,但相聚即是一種相知與支持。往年都是由著她與姊妹們相處,但今年不同,因著這戲,他對柳絮總有些不放心,覺得特別在這樣舉家團圓的日子裡應該陪伴在她身旁。
「我知道,不過我真的很想見妳,明天中午前我去找妳。」
「好。」
「千榕她們回去後妳要睡覺,先別忙著整理,明天我去了再跟妳一起收拾。」
柳絮知道這是他表達關心的方法也就由著他,「好。」
「車子停得遠嗎?要穿暖,圍巾手套不要只拿著卻不用。」經過了四年多的相處,他幾乎可以精準判斷出柳絮的許多反應與習慣,當他在她身旁時,總不忘為柳絮親手整理這些照顧的細節,而此刻也就只能囉唆叮囑而已。
「我已經走到車子旁邊了,也圍著圍巾跟手套了,你不用擔心,我穿得很暖。」
「好。」周慕夏轉頭對招呼他準備下場戲換裝的劇組人員揮揮手,「妳真的還好嗎?」
「我沒事,」柳絮聽見手機那頭有人在呼喚他的聲音,「別擔心我,你快去,大家在等你了吧?」
「是啊,在催我去換裝了,妳趕快上車吧,開車小心,明天見。」
「嗯,明天見。」
周慕夏掛斷電話,還是放心不下,柳絮源自於她己身的成長經驗經常是報喜不報憂的,他們的關係雖然狀似穩定,但只要他暗示想結婚的念頭,就會立刻感受到柳絮的退卻。再過兩年就要五十歲的他儘管成熟穩定,對自己不管身為演員還是大學副教授甚至是戲劇治療師的角色都充滿信心,但柳絮這樣的情緒變化仍然讓他在某些時刻會有許多的想像,到底要怎麼做才能更好,讓彼此更穩定,或者說到底該如何做才能真正地進到柳絮的心裡,讓她願意放心把自己交給他?什麼時機才適合求婚?交往四年,這些念頭經常盤旋在他的腦海裡,他知道柳絮需要時間,因為她的生命經驗,所有美好的事物對她可能都是一種威脅—對於自我存在的質疑。
而另一頭的柳絮進到車子裡,鑰匙剛剛插進龍頭鎖,手機便傳來周慕夏的LINE訊息:『是新的一年要開始了,我會一直陪著妳,牽著手。』
眼淚就這麼突然地落下,一滴一滴的,變成一串一串,圍巾盛不住的都落到了大衣前襟上,這是柳絮最放鬆也最害怕的情況,無預警地止不住淚水,像是許多的委屈終於可以大哭,然而更讓她害怕的是自己要如何才能擺脫傷痛記憶的困擾?還有那些錯過時機再也無法處理的失落,要如何結束?最讓她心驚的莫過於不斷自問,自己真的可以擁有愛情嗎?她已經試過一次了,不是嗎?這次真的可以一生相守嗎?
謹將此書獻給
在那個幽微時代下不被看見的孩子們
受難長輩們
我的母親 陳麗珠女士
我的寶貝 王芃
以及
一直給我支持打氣的大哥 陳立宏先生
這是一個與時代緊緊繾綣的故事,
命運如是,
愛,
亦然。
序曲
「那一年,就在我最需要你的時候,你就這樣離開了,你知道後來那十多年我是怎麼熬過來的嗎?你知道你被抓走之後,我跟媽媽弟弟過著怎樣的日子嗎?你知道我在學校是怎樣的被欺負嗎?你還記得那時候我只有十四歲嗎?十四歲!這些年來你有問過我們那段日子是怎麼過的嗎?」新芳嘶吼著,對著她的父親聲淚俱下。
兩鬢早已花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