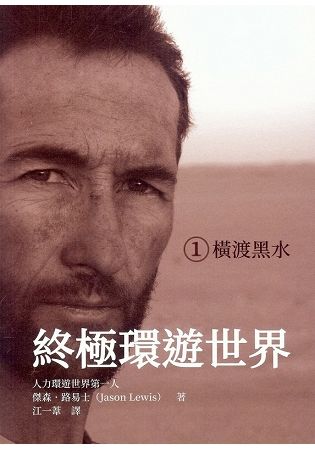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終極環遊世界1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90 |
二手中文書 |
$ 255 |
世界遊記 |
$ 264 |
中文書 |
$ 264 |
主題旅遊 |
$ 270 |
環遊世界 |
$ 270 |
世界旅遊 |
$ 270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Readmoo 評分:
圖書名稱:終極環遊世界1
他在澳洲昆士蘭海岸遭受鱷魚攻擊,在太平洋中血液中毒,在印尼和中國得瘧疾,在喜瑪拉雅山上急性高山症發作。他在科羅拉多州 發生車禍,斷了兩條腿,幾乎致死,在蘇丹和埃及邊界被視為特務而遭監禁。
本書是⟪終極環遊世界⟫四部曲的首部曲,訴說了歷史上最寂寞、最嚴苛卻也最振奮人心、最無厘頭的旅行故事。僅以人身之力來環遊世界,被⟪泰晤士週日報⟫譽為「最後一位第一個環遊世界的偉大人物」。
他的挑戰不只來自肉體。科學家預測二〇三〇年時地球人口將來到八十三億,簡直是個「完美風暴」。冒險家傑森.路易士在旅途中接觸成千上萬學童,呼籲我們應該加強聯繫,擔負共同的責任,留給未來世代一個可棲的星球。
作者簡介
傑森.路易士(Jason Lewis)
英國冒險家,一九六七年生於約克郡,倫敦大學畢業。為人力環遊世界第一人(二〇〇七年),也是歐陸至北美人力橫渡大西洋第一人(一九九五年與Steve Smith共同完成)、直排滑輪橫越北美第一人(一九九六年)和腳踏船橫渡太平洋第一人(二〇〇〇年)。二〇〇七年《泰晤士報》(The London Times)、《運動雜誌》(Sport Magazine)和荒原路華(Land Rover)汽車年度運動員。英國倫敦大學、皇家地理學會和冒險家俱樂部研究員,著有《終極環遊世界》四部曲。個人網站www.jasonexplorer.com/
譯者簡介
江一葦
自小夢想環遊世界,走過半個地球,無法出門的時候,就在書中和雲端上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