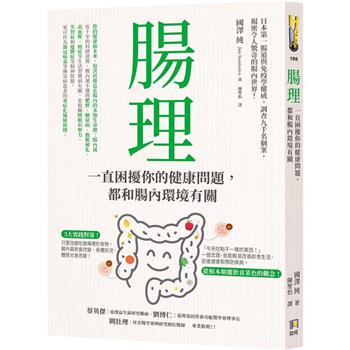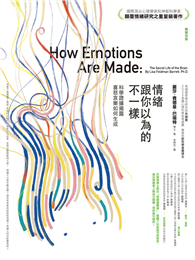對張哲夫來說,建築師的自「我」表態,並不是建築的唯一。
四十年來的建築經歷,代表著使用者與設計者的思想交流。本書精選了張哲夫
的廿一個建築作品,針對建築從無到有的過程,從環境本身、建築需求,一直
探討到細部設計及使用者行為,如何統整這些鉅細靡遺的各種理想,實踐出適
合台灣本土的建築作品。
藉著此次張哲夫回顧建築歷程的同時,也邀請夏鑄九、徐明松、吳光庭、邱文
傑、褚瑞基、陳邁、呂欽文、簡學義等幾位優秀的建築界人士,一同講述彼此
在建築生涯中經歷過的種種,期能做為建築後進的參考,並在未來對台灣的
建築環境帶來改變。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建築無我:張哲夫/超越型式的追逐的圖書 |
 |
建築無我: 張哲夫/ 超越型式的追逐 作者:張哲夫 出版社:田園城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7-11-30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建築無我:張哲夫/超越型式的追逐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張哲夫
張哲夫建築師事務所主持人,紐約普萊特學院建築碩士,畢業於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第八屆中華民國傑出建築師。
張哲夫為台灣知名建築師,自1970年在美國紐約學成至1978年返台執業,近四十年餘經驗,完成建築不下百棟。作品涵蓋範圍廣泛,包含企業總部、廠辦大樓、銀行、學教建築、美術館、集合住宅及社區、國際酒店、古蹟修建、宗教建築、車站建築等。
針對每一案件,均以大處著眼、小處著手為原則,一面關心都市尺度之空間品質,同時也落實於每一設計及施工細節之探究,以謙遜的態度關懷人文與自然環境,創造出對環境友善又能滿足使用者需求的作品,提昇文化氣質,增進生活品質為目標。
於2015以「台北捷運信義線大安森林公園站」獲得 FIABCI 全球卓越建設獎首獎、2017年以「東和鋼鐵新桃園廠行政中心空橋」獲得英國線上建築設計平台網站WorldBuild365評選為全球最佳的五座橋梁設計等獎項。
編者簡介
高名孝
築閱行銷企劃有限公司企劃總監。淡江大學建築系出身,曾任Dialogue建築雜誌特約主編,經歷包含建築專業、書籍出版、國際展覽、房地產等領域,並長期參與關於建築、都市方面的書籍出版及活動事宜。參與的相關著作有《享讀。林木間》、《計劃城事》、《空間的記憶與轉化》等。
張哲夫
張哲夫建築師事務所主持人,紐約普萊特學院建築碩士,畢業於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第八屆中華民國傑出建築師。
張哲夫為台灣知名建築師,自1970年在美國紐約學成至1978年返台執業,近四十年餘經驗,完成建築不下百棟。作品涵蓋範圍廣泛,包含企業總部、廠辦大樓、銀行、學教建築、美術館、集合住宅及社區、國際酒店、古蹟修建、宗教建築、車站建築等。
針對每一案件,均以大處著眼、小處著手為原則,一面關心都市尺度之空間品質,同時也落實於每一設計及施工細節之探究,以謙遜的態度關懷人文與自然環境,創造出對環境友善又能滿足使用者需求的作品,提昇文化氣質,增進生活品質為目標。
於2015以「台北捷運信義線大安森林公園站」獲得 FIABCI 全球卓越建設獎首獎、2017年以「東和鋼鐵新桃園廠行政中心空橋」獲得英國線上建築設計平台網站WorldBuild365評選為全球最佳的五座橋梁設計等獎項。
編者簡介
高名孝
築閱行銷企劃有限公司企劃總監。淡江大學建築系出身,曾任Dialogue建築雜誌特約主編,經歷包含建築專業、書籍出版、國際展覽、房地產等領域,並長期參與關於建築、都市方面的書籍出版及活動事宜。參與的相關著作有《享讀。林木間》、《計劃城事》、《空間的記憶與轉化》等。
目錄
004 寫在《建築無我》前面的話|夏鑄九
012 張哲夫──建築做為一種社會責任|徐明松
022 台灣建築環境的變遷與建築師的責任|張哲夫 vs. 夏鑄九
034 張哲夫的建築歷程
068 住宅與生活
070 住宅建築的變遷與未來|張哲夫 vs. 吳光庭
078 天母石濤園
086 薇閣大廈
092 台大新象
100 澄湖園
108 高雄都會公園住宅
114 楊梅別墅
120 商業建築
122 商業建築與城市發展的可能性|張哲夫 vs. 邱文傑 vs. 褚瑞基
132 中國信託敦北大樓
138 王象世貿大樓
142 揚昇高爾夫俱樂部
150 雍和台北園區一、二期
168 妮傲絲翠總部大樓
174 公共性建築
176 公家建築的嚴峻挑戰|張哲夫 vs. 陳邁 vs. 呂欽文
192 二高清水服務區
202 國立台灣美術館
212 台北捷運信義線大安森林公園站
228 高雄捷運紅線中央公園站
234 平溪天燈觀光分駐所
240 非典型建築
242 從非典型建築探究建築本質|張哲夫 vs. 簡學義
254 東和鋼鐵新桃園廠行政中心
266 芥菜種會福利園區合建案
278 永聯物流共和國台北園區
290 永聯物流共和國台中園區
304 濟南教會增建案
314 張哲夫建築師回台執業四十年有感
333 感恩之旅與特別感謝
334 收錄個案作品年表
012 張哲夫──建築做為一種社會責任|徐明松
022 台灣建築環境的變遷與建築師的責任|張哲夫 vs. 夏鑄九
034 張哲夫的建築歷程
068 住宅與生活
070 住宅建築的變遷與未來|張哲夫 vs. 吳光庭
078 天母石濤園
086 薇閣大廈
092 台大新象
100 澄湖園
108 高雄都會公園住宅
114 楊梅別墅
120 商業建築
122 商業建築與城市發展的可能性|張哲夫 vs. 邱文傑 vs. 褚瑞基
132 中國信託敦北大樓
138 王象世貿大樓
142 揚昇高爾夫俱樂部
150 雍和台北園區一、二期
168 妮傲絲翠總部大樓
174 公共性建築
176 公家建築的嚴峻挑戰|張哲夫 vs. 陳邁 vs. 呂欽文
192 二高清水服務區
202 國立台灣美術館
212 台北捷運信義線大安森林公園站
228 高雄捷運紅線中央公園站
234 平溪天燈觀光分駐所
240 非典型建築
242 從非典型建築探究建築本質|張哲夫 vs. 簡學義
254 東和鋼鐵新桃園廠行政中心
266 芥菜種會福利園區合建案
278 永聯物流共和國台北園區
290 永聯物流共和國台中園區
304 濟南教會增建案
314 張哲夫建築師回台執業四十年有感
333 感恩之旅與特別感謝
334 收錄個案作品年表
序
導讀專文
寫在《建築無我》前面的話
夏鑄九
張哲夫建築師返台執業四十年有意編輯一本不僅僅像一般常規建築師個人作品集那樣的紀念出版物,我願意就更大的全球視角看待台灣建築師的專業實踐,在前面寫幾句話。首先,試由都市變遷過程審視建築,先談都市現實的問題,再論專業實踐的角色與作用,其間夾雜一點經驗個案。
在殖民城市歷史條件所形構的二元空間結構上,戰後的台灣城市,主要的都市形式為快速經濟發展過程與國家的政策所塑造。由北美洲引入的,形式化、簡單化、沒有生命力、業已先決定了的、也未獲像新加坡或香港那樣真正受到國家重視的“現代都市計劃”(modern urban planning),這個制度(institution),同樣也是台灣版本的“現代建築”(modern architecture),在美利堅盛世與強權所維持的世界和平與政治秩序下(Pax Americana)的東亞移植(transplantation)。
相較於台灣的社會關係的作用,這對同胎兄弟,它們都一樣是難以實實在在起作用的制度性空間。於是,台灣主要的都市形式可以說是:1.在國家政策縱容土地資本的投機城市(speculators cities),2.在制度執行邊緣與縫隙中冒生的、有活力的中小資本慾望再現的非正式城市(informal cities),以及,3.相對晚一步,1989年之後,市民城市(citizens cities)浮現的力量;它們是塑造台灣城市與鄉村容貌(appearance)的有特色力量。這是在充滿衝突的都市過程中所營造的、混亂無序卻生機勃勃的、充滿似非而是、似是而非現象的悖論性空間與社會(paradoxical space and society)的變遷過程。於是,慢慢變得宜居而舒服的台灣城市與市民文化也開出空間的花朵,展現出一種幾乎與現代建築與現代規劃所強調的、西方美學上的紀念性(monumentality)沒有太直接的關係,卻又有些特殊的社會意涵的象徵空間魅力。
做為歷史對照,一般而言,資本主義的城市,中心化、一元化,預先決定了的權力裝置,美學支配,一如巴黎的林蔭大道正是布爾喬亞的階級美學再現,伴隨都市危機與軍事控制,衝突的社會關係,再加上土地資本對房地產市場考量,及在其身後更根本的力量,資本主義城市的創造性破壞,為進一步的積累鋪路。這是巴黎故事看不見的主線。
至於台北故事,台北空間形式的結局,也是都市設計的執行,為何成效不理想?執行,預審,局長定位作用與委員素質的展現是檢討成效的關鍵。張哲夫負責的內湖妮傲絲翠總部大樓,審查過程擔心日後違建,要求將戶外空間加蓋為室內空間。依照如此邏輯,如同擔心陽台加蓋,就不准設計陽台一般,不是削足適履嗎?這難道就是國家機器的權力,拘泥的政府,瑣碎行政文化,面對台灣非正式城市的違建文化之後,無能力治理的遺留表現嗎?
台灣的公共建築物是國家機器,僵化拘泥的國家的象徵表現,也是一種象徵的公共空間,因此,“公共”,是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的互動,是最值得關注的焦點地方。台北市文化局主導的公共藝術節,如2005年老市區的大同新世界,江洋輝的“我們同一國大使館”改造蘭州派出所,曾經營造出有意思的設計與出色的展現,可惜都市發展局與市長對於公共空間的意義表現均不甚了了,最後,被拆除了事。前述西方美學上的紀念性的對立面可以說是市民社會的豐盛多元,尊重與包容既有,市民參與,看到社會關係,這些關乎公共空間的捍衛與爭取、可及、發聲,也是市民城市的意義表現。張哲夫的捷運大安森林公園站,倒是難得的突破性個案,期望日後在大安森林公園的部分,不會影響捷運運輸人流的地方,容納一些文化表演活動。
前述這個都市變遷的歷史過程,可以說是廿一世紀台灣面對全球資訊化巨變趨勢下必須因應的現實。
在巨變過程中,我們得見一個僵硬拘泥的國家(rigid state),在民主化過程中“選舉萬歲”(election first)催生的民萃政治(populist politics)力量,使得“這個國家”之治理,有時軟弱,有時冷酷,更時時刻刻是充滿算計的政治決策,一方面限制了技術官僚能力與本來就不足的氣度,困限於瑣事的危機,沒有大格局,然而,另一方面卻又必須面對殘酷的全球競爭現實。在這個現實裡,一方面既是不能治理的處境,政府是什麼計劃(projects)都不能做,不能實現,不能引領社會對明日城市的文化想像,另一方面又像是在瓦解城市的前夜,竟然預示了社會關係與社會衝突,城市生活與價值認同再現的衝突失序,城市分裂了。台灣的城市是全球資訊化下的分裂城市(divided cities),由國族認同、階級、族群、性別與性傾向、世代與年齡、區域與社區…之間的重重分裂。區域分裂,因國土領域裡國家制度上的無能加速了全球經濟下區域的兩極分化。
六都之外,豈非國土,它們難道是被制度遺忘的邊陲嗎?以及,都市更新、老屋更新等政策,由“容積獎勵”催逼出中小地主對土地利得的貪婪,人人都變身為投機的發展商,市民胃口養大之後都更反而成為難以執行的僵局。於是都市計劃與建築直接現形為貨幣,我們像是回到未來,預見了明天的城市裡台北市中心的晉紳化(gentrification)。剛浮現的台灣市民社會竟然朝向一個私有財產權絕對化的社會,排除了其他的形式的所有權人空間使用的權利,全球信息化城市裡一個極端的新自由主義價值所貫穿的私營城市(private city)降臨了。1980年代末才開始浮現的市民城市,現在分裂了。前述的社會排除與都市衝突竟然像是分裂城市的空間戰爭(war of space)。未來的台北市的希望空間,只有徹底轉向為公共城市(public city),經由社區營造的都市更新,由市民做為主體主導的,自主、參與的都市更新,都市更新才有改造城市的新動能,台北城市也才有明天。
面對分裂的台灣城市的都市現實與都市過程,今天台灣的城市生活中包含的各式各樣的社會關係,尤其是通過面對面的遭遇的產生的社會衝突,經歷了差異和衝突的摩擦會使人們親身體悟到他們自身生活的現實氛圍,這種衝突的經歷逐漸成熟起來,正是台灣社會的公共空間與公共經驗的成長過程。然而國家的權力與現代性的理性以及壓迫性慾望,卻一再干預市民社會的生活,以至於試圖插手民間社會的宗教,滅香封爐。似乎國家不自覺地還以為它可以做到像前述的巴黎故事與奧斯曼男爵(Baron Haussmann)之所為,以為國土的前瞻、城市的規劃、建築的設計仍然要成為一個有序清晰的整體。這種現代性的成見必須破除。城市是由各部分组成的社會秩序,無須強求一致的、可控制的整體形式。就像台灣城市的規劃與分區管制,這是從來就沒有被貫徹執行過的國家理性的紙上企圖,集中管制,功能有效,視覺秩序,遮蓋了新自由主義私營城市的社會不正義,透露出法西斯的徵兆。過於要求強渡關山,此去路難,是非到底難以求安。現實的都市生活剛好相反,混亂無序就是台灣城市的特色與活力的表現。混亂無序其實優於僵死、被國家的技術官僚先決定了規劃,限制了實在起作用的、真實的社會探索,這是台灣城市的公共空間的社會探索,不是國家權力的伸張。
在這種都市現實與都市過程之中,作為市民社會中堅團體的建築師社群,過去被投機城市的土地發展商的價值所支配,失去專業角色的自主性與反省視野,專業團體成為利益團體,不能區分出建築師自主的專業角色。
在制度上,保守的視野與利己的價值又排除了地景建築師與都市規劃師的專業角色,未能整合在自由職業的專業者的制度法令領域之內,加強了社會分工下專業技能的片段化趨勢。
在技術上,專業技能不能與時俱進,譬如說,對永續城市(sustainable city)與綠建築的價值與專業技能無感;以及,在新知識與技術的挑戰下“叫建築太沈重”,資訊城市(information city)搭乘網絡的流動,“建築就是媒體”(architecture as media),建築研究者受限於早已過時了的西歐資產階級形式主義美學的眼界,還以為網絡社會與資訊城市僅僅是表面數位化圖繪形式的美學操作,這也是台灣的建築學院不夠長進的狹隘結局。
最關鍵的還是政府的政策。全球信息化資本主義下都會區域的浮現,西班牙的畢爾包(Bilbao),1997年用法蘭克‧蓋瑞(Frank Gehry)設計的古根翰美術館做為支點,挑起畢爾包都市轉化的歷史策略,首開城市行銷(city marketing)之濫觴。畢爾包效應(Bilbao effect)對擔心世界看不見的台灣豈能倖免?雖然全球化下越界的國際級建築師的經驗與能力值得借取,評選建築師的制度也不宜排外,然而國際競圖氾濫,在偶像建築師明星光環之下,排除了地方建築師的權利,在既有公部門體制之下,營造過程中問題層出不窮,引起建築師的抗議。不知自己是誰的台灣的國家,坐實了南方朔所說的“第三世界的建築物主義”的推手,造就了第三世界無能建構自身主體性的美學笑話。這時我們值得進一步反思與追溯西方文藝復興之後建築論述(architectural discourse)建構的形式主義幽靈的根源。文藝復興的建築師將古典建築變成一個自主而絕對的建築“物”,或者說,建築客體,建築對象(architectural object)。過去,成為被建築師挪用的元素,給予當前所需的意識形態支持,建築對象成為客體,隨手擺弄拼湊(bricolage)。對中世紀與之前的歷史而言,這是在重新建構一個新的傳統與歷史,發明歷史的行動,被稱為是對歷史的遮蔽(the eclipse of history),遮蔽歷史的開端。用黑格爾的說法,這是客體性(objectivity)與主體性(subjectivity)間的分離,師與匠之間的一種革命性的斷裂。到了十八世紀,為啟蒙主義思想鼓勵的西方資產階級美學論述終於成形。西歐哲學家將建築分類為美術(fine arts)的一支,以審美價值區分建築與營造,強調美的營造(建築物,building)才是建築(Architecture)。林肯大教堂與腳踏車棚兩者之間的美學對比就是最有名的例子。歐美社會經歷五百年時間逐步加速的過程,現代性(modernity)步伐仍難掩魯莽,然而,現代性其實就是斷裂(break),是資本追求利潤的慾望造成的創造性破壞的空間再現,這也就是“成為現代”(to be modern)。至於就發展中國家的殖民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經驗而言,制度的移植(transplantation)使得在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上,機器與制度的關係上,都忽略了人。加上專業者也遺忘了人,又欠缺反思,不能接地氣,異化的空間就是必然的結局。去除了人的存在之後的建築其實就是形式主義文化的再生產。空間的全球商品化,偶像建築師就是壟斷性品牌,為新自由主義的支配性意識形態所支持,為發展中國家的缺乏自信的政府心態所肯定,這是在全球化年代建築論述的權力與價值觀赤裸裸地展現在發展中國家的終極表徵。而台灣的建築學院、建築論述、以及建築師本身又豈能置身事外?不過,在國際競圖爭議之外,長期制約台灣建築成長的還是政治力量的不當干預,真正嚴重而未被揭露的事實莫過於選擇建築師的制度背後流露出政府被龐大工程利益侵蝕之後的腐敗,這已經不是媒體上的醜聞,而是國家機器中潛藏的貪瀆,由歷史角度來看,卻經常是伴奏政權終局的輓歌。
大多數的建築師與建築學院,無能辨認建築歷史舞台已經改變,也未能覺察到1968年之後反省性的社會建築(social architecture)已經昇華為具普遍意義的典範轉移,那麼,又如何期待能突破封閉的建築學習過程,摸索明天的出路,掌握社會變遷的隙縫(enclaves of social changes)?面對前述這些現實的空間問題,除了再現一點自以為小確幸的美學玩意兒之外,建築師與建築設計本身,如何能逆境生長,回到歷史的中心,真正做些什麼“歷史性的計劃”(historical project)呢?至於建築批評,一如文學批評、藝術批評、以及週末增刊的媒體上產生的評論文字都是這樣,被認為是一種操作性批評(operative criticism)。他們貌似中立,卻在偷渡既有的美學價值與偏見。他們更是既定的現代建築論述的美學觀點的再生產,致力於、意象(image)、形式(form)的品味移植,空間商品化,流行追趕。對照於建築批評,建築史的寫作則是面對脈絡,社會與制度的脈絡,分析問題,建築史寫作是解秘的計劃(a project of demythification),而不是建構鄉愁,強化文化對體制的再生產。
與建築師專業社群相較,深度反省的能力與展望明天的能力是有關係的,而這部分特別應該是學院的責任。我們的專業養成是一種綜合性的能力,這是一種人文學科提供的精神狀態,關照能力,反身性能力,有能力看到自身,知道自己是誰?
知道自身的限制,也因此,空間的營造提供了一種機會,一種鏡象效果,一種過溪水而能頓悟的能力,讓我們看到自身,也就是“異托邦”(heterotopias)的營造吧?一種象徵空間的力量。
於是最後,我引用賀龍‧巴赫德(Roland Barthes)早就提醒過我們的話,對建築設計積極的潛力多做一點說明:在建築的雙向運動,“求便與夢幻”的緊張關係中,象徵表現的魅力與作用是空間實踐的要害所在。相較於科學的論述,設計是一種陳述的行動,一種象徵的實踐。設計,則在於展示主體的位置與能量,甚至,是在主體不足(不是不在)的同時,又專注於語言的現實本身,認識到語言是由意涵、效果、迴響、轉折、返回、程度等組成的巨大光暈。基於對論述實踐主體的期待,巴赫德的情色城市的建構便重新界定了有自覺的建築師的實踐主體性,這時,建築師的稱呼已不再是社會分工上的角色,或是語言上的被動奴僕。
有自覺的設計師有能力發揮建築再現與表徵的力量,故弄玄虛,玩弄符號,而不是消除符號。
設計師將符號置於一種語言機器之中,而機器的制動器和安全閥都已經拔除了。這是在語言內部所建立的各式各樣的真正的同形異質體(heteronymy),也就是符號學實踐的可能性,一種對權力論述與理性論述的顛覆之道,一種令人愉悅、有快感的、偏離作用(excursion),展現一種像孩童般的,慾望中的來來去去遊戲,一種無權力的論述實踐。這樣,在美學層次上,台灣的建築設計師與建築體驗的使用者,或許可以與2017年年度神片,或者說,公認大爛片,《台北物語》的導演、演員、以及觀眾們所造就的嘉年華式的狂歡就可以溝通與對話。《台北物語》竟然一再公演,由小廳轉大廳,導演黃英雄對媒體說:“我的電影是講人性又超人性的,目的是為了嘲弄台北生活的荒誕與拜金”。可是,觀眾回報以一種必須共同同時在電影院特定空間裡觀賞的嘉年華。大陸浙江來的影評人黃豆豆說的好:“一群人因為共同的目的齊聚在一起,盡情善意地吐槽、放肆地歡笑…它在某個特定的時間完成了超越,翻轉了電影人和觀眾之間的關係,他甚至還帶來了一種觀影的優越感,也因此,它帶來的歡樂是另類的,是發自內心的。”
一直到本書最後送印之際,張哲夫決定用《建築無我》為書名, 我才驚覺到他返台執業四十年最想說的話竟然是“無我”。而無我建築,正是西方現代建築師角色在文藝復興之際浮現的對立性價值(opposition)的再現空間與對極之地(antipode)。自我的表現做為現代性再現的創造性破壞慾望的內在動力,是前文提到的西方現代建築師客體性與主體性間的對立,也是建築師與營造工匠之間的歷史性斷裂。這是現代建築師的歷史誕生,也是建築師的自我在現代專業論述的滋長與創新慾望的撩撥下的引爆點。
然而,面對當前廿一世紀全球信息化的現實,跨界的溝通能力已經反過來成為專業養成的必須素養,以及,經由地方充分參與發揮地方智慧,更是必須的新專業技能的一部分。工業社會形構的現代建築與規劃的專業論述卻不時顯示出其專業傲慢、技術僵硬、欠缺靈活與彈性,缺少文化與人特質的關注。專業論述只有更開放才能提供專業服務。建築無我(selfless architecture),是對現實的深刻反省後追求的境界,卻正是沒有建築師的建築(architecture without architect)。建築的出路,只有在社會與政治的新條件之下,重新回到人本身,重建主體與客體的統一。
建築設計要回到無我。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
這是《金剛經》的教誨。
寫在《建築無我》前面的話
夏鑄九
張哲夫建築師返台執業四十年有意編輯一本不僅僅像一般常規建築師個人作品集那樣的紀念出版物,我願意就更大的全球視角看待台灣建築師的專業實踐,在前面寫幾句話。首先,試由都市變遷過程審視建築,先談都市現實的問題,再論專業實踐的角色與作用,其間夾雜一點經驗個案。
在殖民城市歷史條件所形構的二元空間結構上,戰後的台灣城市,主要的都市形式為快速經濟發展過程與國家的政策所塑造。由北美洲引入的,形式化、簡單化、沒有生命力、業已先決定了的、也未獲像新加坡或香港那樣真正受到國家重視的“現代都市計劃”(modern urban planning),這個制度(institution),同樣也是台灣版本的“現代建築”(modern architecture),在美利堅盛世與強權所維持的世界和平與政治秩序下(Pax Americana)的東亞移植(transplantation)。
相較於台灣的社會關係的作用,這對同胎兄弟,它們都一樣是難以實實在在起作用的制度性空間。於是,台灣主要的都市形式可以說是:1.在國家政策縱容土地資本的投機城市(speculators cities),2.在制度執行邊緣與縫隙中冒生的、有活力的中小資本慾望再現的非正式城市(informal cities),以及,3.相對晚一步,1989年之後,市民城市(citizens cities)浮現的力量;它們是塑造台灣城市與鄉村容貌(appearance)的有特色力量。這是在充滿衝突的都市過程中所營造的、混亂無序卻生機勃勃的、充滿似非而是、似是而非現象的悖論性空間與社會(paradoxical space and society)的變遷過程。於是,慢慢變得宜居而舒服的台灣城市與市民文化也開出空間的花朵,展現出一種幾乎與現代建築與現代規劃所強調的、西方美學上的紀念性(monumentality)沒有太直接的關係,卻又有些特殊的社會意涵的象徵空間魅力。
做為歷史對照,一般而言,資本主義的城市,中心化、一元化,預先決定了的權力裝置,美學支配,一如巴黎的林蔭大道正是布爾喬亞的階級美學再現,伴隨都市危機與軍事控制,衝突的社會關係,再加上土地資本對房地產市場考量,及在其身後更根本的力量,資本主義城市的創造性破壞,為進一步的積累鋪路。這是巴黎故事看不見的主線。
至於台北故事,台北空間形式的結局,也是都市設計的執行,為何成效不理想?執行,預審,局長定位作用與委員素質的展現是檢討成效的關鍵。張哲夫負責的內湖妮傲絲翠總部大樓,審查過程擔心日後違建,要求將戶外空間加蓋為室內空間。依照如此邏輯,如同擔心陽台加蓋,就不准設計陽台一般,不是削足適履嗎?這難道就是國家機器的權力,拘泥的政府,瑣碎行政文化,面對台灣非正式城市的違建文化之後,無能力治理的遺留表現嗎?
台灣的公共建築物是國家機器,僵化拘泥的國家的象徵表現,也是一種象徵的公共空間,因此,“公共”,是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的互動,是最值得關注的焦點地方。台北市文化局主導的公共藝術節,如2005年老市區的大同新世界,江洋輝的“我們同一國大使館”改造蘭州派出所,曾經營造出有意思的設計與出色的展現,可惜都市發展局與市長對於公共空間的意義表現均不甚了了,最後,被拆除了事。前述西方美學上的紀念性的對立面可以說是市民社會的豐盛多元,尊重與包容既有,市民參與,看到社會關係,這些關乎公共空間的捍衛與爭取、可及、發聲,也是市民城市的意義表現。張哲夫的捷運大安森林公園站,倒是難得的突破性個案,期望日後在大安森林公園的部分,不會影響捷運運輸人流的地方,容納一些文化表演活動。
前述這個都市變遷的歷史過程,可以說是廿一世紀台灣面對全球資訊化巨變趨勢下必須因應的現實。
在巨變過程中,我們得見一個僵硬拘泥的國家(rigid state),在民主化過程中“選舉萬歲”(election first)催生的民萃政治(populist politics)力量,使得“這個國家”之治理,有時軟弱,有時冷酷,更時時刻刻是充滿算計的政治決策,一方面限制了技術官僚能力與本來就不足的氣度,困限於瑣事的危機,沒有大格局,然而,另一方面卻又必須面對殘酷的全球競爭現實。在這個現實裡,一方面既是不能治理的處境,政府是什麼計劃(projects)都不能做,不能實現,不能引領社會對明日城市的文化想像,另一方面又像是在瓦解城市的前夜,竟然預示了社會關係與社會衝突,城市生活與價值認同再現的衝突失序,城市分裂了。台灣的城市是全球資訊化下的分裂城市(divided cities),由國族認同、階級、族群、性別與性傾向、世代與年齡、區域與社區…之間的重重分裂。區域分裂,因國土領域裡國家制度上的無能加速了全球經濟下區域的兩極分化。
六都之外,豈非國土,它們難道是被制度遺忘的邊陲嗎?以及,都市更新、老屋更新等政策,由“容積獎勵”催逼出中小地主對土地利得的貪婪,人人都變身為投機的發展商,市民胃口養大之後都更反而成為難以執行的僵局。於是都市計劃與建築直接現形為貨幣,我們像是回到未來,預見了明天的城市裡台北市中心的晉紳化(gentrification)。剛浮現的台灣市民社會竟然朝向一個私有財產權絕對化的社會,排除了其他的形式的所有權人空間使用的權利,全球信息化城市裡一個極端的新自由主義價值所貫穿的私營城市(private city)降臨了。1980年代末才開始浮現的市民城市,現在分裂了。前述的社會排除與都市衝突竟然像是分裂城市的空間戰爭(war of space)。未來的台北市的希望空間,只有徹底轉向為公共城市(public city),經由社區營造的都市更新,由市民做為主體主導的,自主、參與的都市更新,都市更新才有改造城市的新動能,台北城市也才有明天。
面對分裂的台灣城市的都市現實與都市過程,今天台灣的城市生活中包含的各式各樣的社會關係,尤其是通過面對面的遭遇的產生的社會衝突,經歷了差異和衝突的摩擦會使人們親身體悟到他們自身生活的現實氛圍,這種衝突的經歷逐漸成熟起來,正是台灣社會的公共空間與公共經驗的成長過程。然而國家的權力與現代性的理性以及壓迫性慾望,卻一再干預市民社會的生活,以至於試圖插手民間社會的宗教,滅香封爐。似乎國家不自覺地還以為它可以做到像前述的巴黎故事與奧斯曼男爵(Baron Haussmann)之所為,以為國土的前瞻、城市的規劃、建築的設計仍然要成為一個有序清晰的整體。這種現代性的成見必須破除。城市是由各部分组成的社會秩序,無須強求一致的、可控制的整體形式。就像台灣城市的規劃與分區管制,這是從來就沒有被貫徹執行過的國家理性的紙上企圖,集中管制,功能有效,視覺秩序,遮蓋了新自由主義私營城市的社會不正義,透露出法西斯的徵兆。過於要求強渡關山,此去路難,是非到底難以求安。現實的都市生活剛好相反,混亂無序就是台灣城市的特色與活力的表現。混亂無序其實優於僵死、被國家的技術官僚先決定了規劃,限制了實在起作用的、真實的社會探索,這是台灣城市的公共空間的社會探索,不是國家權力的伸張。
在這種都市現實與都市過程之中,作為市民社會中堅團體的建築師社群,過去被投機城市的土地發展商的價值所支配,失去專業角色的自主性與反省視野,專業團體成為利益團體,不能區分出建築師自主的專業角色。
在制度上,保守的視野與利己的價值又排除了地景建築師與都市規劃師的專業角色,未能整合在自由職業的專業者的制度法令領域之內,加強了社會分工下專業技能的片段化趨勢。
在技術上,專業技能不能與時俱進,譬如說,對永續城市(sustainable city)與綠建築的價值與專業技能無感;以及,在新知識與技術的挑戰下“叫建築太沈重”,資訊城市(information city)搭乘網絡的流動,“建築就是媒體”(architecture as media),建築研究者受限於早已過時了的西歐資產階級形式主義美學的眼界,還以為網絡社會與資訊城市僅僅是表面數位化圖繪形式的美學操作,這也是台灣的建築學院不夠長進的狹隘結局。
最關鍵的還是政府的政策。全球信息化資本主義下都會區域的浮現,西班牙的畢爾包(Bilbao),1997年用法蘭克‧蓋瑞(Frank Gehry)設計的古根翰美術館做為支點,挑起畢爾包都市轉化的歷史策略,首開城市行銷(city marketing)之濫觴。畢爾包效應(Bilbao effect)對擔心世界看不見的台灣豈能倖免?雖然全球化下越界的國際級建築師的經驗與能力值得借取,評選建築師的制度也不宜排外,然而國際競圖氾濫,在偶像建築師明星光環之下,排除了地方建築師的權利,在既有公部門體制之下,營造過程中問題層出不窮,引起建築師的抗議。不知自己是誰的台灣的國家,坐實了南方朔所說的“第三世界的建築物主義”的推手,造就了第三世界無能建構自身主體性的美學笑話。這時我們值得進一步反思與追溯西方文藝復興之後建築論述(architectural discourse)建構的形式主義幽靈的根源。文藝復興的建築師將古典建築變成一個自主而絕對的建築“物”,或者說,建築客體,建築對象(architectural object)。過去,成為被建築師挪用的元素,給予當前所需的意識形態支持,建築對象成為客體,隨手擺弄拼湊(bricolage)。對中世紀與之前的歷史而言,這是在重新建構一個新的傳統與歷史,發明歷史的行動,被稱為是對歷史的遮蔽(the eclipse of history),遮蔽歷史的開端。用黑格爾的說法,這是客體性(objectivity)與主體性(subjectivity)間的分離,師與匠之間的一種革命性的斷裂。到了十八世紀,為啟蒙主義思想鼓勵的西方資產階級美學論述終於成形。西歐哲學家將建築分類為美術(fine arts)的一支,以審美價值區分建築與營造,強調美的營造(建築物,building)才是建築(Architecture)。林肯大教堂與腳踏車棚兩者之間的美學對比就是最有名的例子。歐美社會經歷五百年時間逐步加速的過程,現代性(modernity)步伐仍難掩魯莽,然而,現代性其實就是斷裂(break),是資本追求利潤的慾望造成的創造性破壞的空間再現,這也就是“成為現代”(to be modern)。至於就發展中國家的殖民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經驗而言,制度的移植(transplantation)使得在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上,機器與制度的關係上,都忽略了人。加上專業者也遺忘了人,又欠缺反思,不能接地氣,異化的空間就是必然的結局。去除了人的存在之後的建築其實就是形式主義文化的再生產。空間的全球商品化,偶像建築師就是壟斷性品牌,為新自由主義的支配性意識形態所支持,為發展中國家的缺乏自信的政府心態所肯定,這是在全球化年代建築論述的權力與價值觀赤裸裸地展現在發展中國家的終極表徵。而台灣的建築學院、建築論述、以及建築師本身又豈能置身事外?不過,在國際競圖爭議之外,長期制約台灣建築成長的還是政治力量的不當干預,真正嚴重而未被揭露的事實莫過於選擇建築師的制度背後流露出政府被龐大工程利益侵蝕之後的腐敗,這已經不是媒體上的醜聞,而是國家機器中潛藏的貪瀆,由歷史角度來看,卻經常是伴奏政權終局的輓歌。
大多數的建築師與建築學院,無能辨認建築歷史舞台已經改變,也未能覺察到1968年之後反省性的社會建築(social architecture)已經昇華為具普遍意義的典範轉移,那麼,又如何期待能突破封閉的建築學習過程,摸索明天的出路,掌握社會變遷的隙縫(enclaves of social changes)?面對前述這些現實的空間問題,除了再現一點自以為小確幸的美學玩意兒之外,建築師與建築設計本身,如何能逆境生長,回到歷史的中心,真正做些什麼“歷史性的計劃”(historical project)呢?至於建築批評,一如文學批評、藝術批評、以及週末增刊的媒體上產生的評論文字都是這樣,被認為是一種操作性批評(operative criticism)。他們貌似中立,卻在偷渡既有的美學價值與偏見。他們更是既定的現代建築論述的美學觀點的再生產,致力於、意象(image)、形式(form)的品味移植,空間商品化,流行追趕。對照於建築批評,建築史的寫作則是面對脈絡,社會與制度的脈絡,分析問題,建築史寫作是解秘的計劃(a project of demythification),而不是建構鄉愁,強化文化對體制的再生產。
與建築師專業社群相較,深度反省的能力與展望明天的能力是有關係的,而這部分特別應該是學院的責任。我們的專業養成是一種綜合性的能力,這是一種人文學科提供的精神狀態,關照能力,反身性能力,有能力看到自身,知道自己是誰?
知道自身的限制,也因此,空間的營造提供了一種機會,一種鏡象效果,一種過溪水而能頓悟的能力,讓我們看到自身,也就是“異托邦”(heterotopias)的營造吧?一種象徵空間的力量。
於是最後,我引用賀龍‧巴赫德(Roland Barthes)早就提醒過我們的話,對建築設計積極的潛力多做一點說明:在建築的雙向運動,“求便與夢幻”的緊張關係中,象徵表現的魅力與作用是空間實踐的要害所在。相較於科學的論述,設計是一種陳述的行動,一種象徵的實踐。設計,則在於展示主體的位置與能量,甚至,是在主體不足(不是不在)的同時,又專注於語言的現實本身,認識到語言是由意涵、效果、迴響、轉折、返回、程度等組成的巨大光暈。基於對論述實踐主體的期待,巴赫德的情色城市的建構便重新界定了有自覺的建築師的實踐主體性,這時,建築師的稱呼已不再是社會分工上的角色,或是語言上的被動奴僕。
有自覺的設計師有能力發揮建築再現與表徵的力量,故弄玄虛,玩弄符號,而不是消除符號。
設計師將符號置於一種語言機器之中,而機器的制動器和安全閥都已經拔除了。這是在語言內部所建立的各式各樣的真正的同形異質體(heteronymy),也就是符號學實踐的可能性,一種對權力論述與理性論述的顛覆之道,一種令人愉悅、有快感的、偏離作用(excursion),展現一種像孩童般的,慾望中的來來去去遊戲,一種無權力的論述實踐。這樣,在美學層次上,台灣的建築設計師與建築體驗的使用者,或許可以與2017年年度神片,或者說,公認大爛片,《台北物語》的導演、演員、以及觀眾們所造就的嘉年華式的狂歡就可以溝通與對話。《台北物語》竟然一再公演,由小廳轉大廳,導演黃英雄對媒體說:“我的電影是講人性又超人性的,目的是為了嘲弄台北生活的荒誕與拜金”。可是,觀眾回報以一種必須共同同時在電影院特定空間裡觀賞的嘉年華。大陸浙江來的影評人黃豆豆說的好:“一群人因為共同的目的齊聚在一起,盡情善意地吐槽、放肆地歡笑…它在某個特定的時間完成了超越,翻轉了電影人和觀眾之間的關係,他甚至還帶來了一種觀影的優越感,也因此,它帶來的歡樂是另類的,是發自內心的。”
一直到本書最後送印之際,張哲夫決定用《建築無我》為書名, 我才驚覺到他返台執業四十年最想說的話竟然是“無我”。而無我建築,正是西方現代建築師角色在文藝復興之際浮現的對立性價值(opposition)的再現空間與對極之地(antipode)。自我的表現做為現代性再現的創造性破壞慾望的內在動力,是前文提到的西方現代建築師客體性與主體性間的對立,也是建築師與營造工匠之間的歷史性斷裂。這是現代建築師的歷史誕生,也是建築師的自我在現代專業論述的滋長與創新慾望的撩撥下的引爆點。
然而,面對當前廿一世紀全球信息化的現實,跨界的溝通能力已經反過來成為專業養成的必須素養,以及,經由地方充分參與發揮地方智慧,更是必須的新專業技能的一部分。工業社會形構的現代建築與規劃的專業論述卻不時顯示出其專業傲慢、技術僵硬、欠缺靈活與彈性,缺少文化與人特質的關注。專業論述只有更開放才能提供專業服務。建築無我(selfless architecture),是對現實的深刻反省後追求的境界,卻正是沒有建築師的建築(architecture without architect)。建築的出路,只有在社會與政治的新條件之下,重新回到人本身,重建主體與客體的統一。
建築設計要回到無我。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
這是《金剛經》的教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