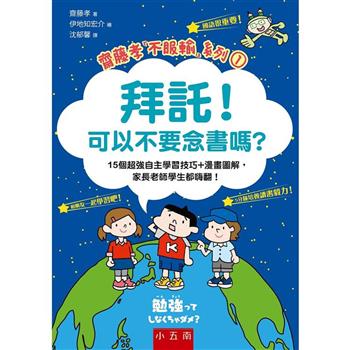詩歌的聲音指的是語音、語調、辭章結構和語法所生成的音樂效果,透過聲音可以感知詩人的生命氣息。詩人的情緒內蘊著傳統與西方文化資源的魅力,也聯動著時代環境與現實生活的變遷,只是透過聲音形式得以彰顯。本書總覽二十世紀八○年代以來漢語新詩的聲音美學轉向,兼顧詩人楊牧、陳黎、張棗、陳東東、藍藍的個性化創作,又在附錄中結合主題、意象與聲音的關係,試圖呈現詩人為何以聲音抒情、又如何抒情。
本書特色
♪ 以詩人楊牧、陳黎、張棗、陳東東、藍藍為個案研究對象,透過剖析詩的聲音(語音、語調、辭章結構和語法所產生的音樂效果),感知詩人的情感蘊藉和生命氣息。
♪ 以嶄新的角度剖析詩作,建構了一套關於聲音的理論性論述,開闊了現代詩研究的視野。
♪ 現代詩研究者必備專著
名人推薦
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東亞語言文化系奚密教授
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楊揚教授
復旦大學中文系郜元寶教授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張松建教授
=====★ 聯合推薦 ★======
現代詩的研究者寥寥,缺乏典範可循。而聲音問題,又是百年爭論不休的重要詩學議題。翟月琴能圍繞音隨義轉、聲依情動,結合宏闊的時代境遇、具體的詩人個性,深入文本細部逐行逐詞解讀,可見對現代漢詩理論與實踐狀況的整體把握。她不拘理論格套、不借抽象概念而追尋心的體驗與美的感受,故而論述由淺及深、由隱而顯,以此呼應古典詩歌批評,是值得推薦的青年詩歌批評者。──復旦大學中文系郜元寶教授
本書以楊牧、陳黎、張棗、陳東東、藍藍的現代詩為個案研究的對象,研討現代漢詩的抒情聲音這個重大學術課題。作者對海峽兩岸的文學史脈絡比較熟悉,廣泛參考學術界的研究成果,體現出嚴謹扎實的學風。此書之文本分析,精緻綿密,兼采合適的理論論述,深入剖析了這批詩人的生命史和藝術歷程,也涉及中西詩學的若干重要面向。翟月琴博士是中國大陸學術界的青年才俊,此書之出版,必將裨益於現代漢詩的批評研究。──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張松建教授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獨弦琴:詩人的抒情聲音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電子書 |
$ 189 |
華文現代詩 |
$ 202 |
中文書 |
$ 238 |
現代詩 |
$ 240 |
華文詩集 |
$ 243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獨弦琴:詩人的抒情聲音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翟月琴
上海戲劇學院戲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現當代詩歌和戲劇。華東師範大學文學博士、上海戲劇學院博士後研究員,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UC Davis)東亞語言文化系訪問學者。曾出版隨筆合集《間隙的空靈》,專著《一九八○年代以來漢語新詩的聲音研究》,於臺灣的《清華學報》、香港的《東方文化》和大陸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當代作家評論》《揚子江評論》《戲劇藝術》《華文文學》等重要期刊發表文章四十餘篇。
翟月琴
上海戲劇學院戲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現當代詩歌和戲劇。華東師範大學文學博士、上海戲劇學院博士後研究員,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UC Davis)東亞語言文化系訪問學者。曾出版隨筆合集《間隙的空靈》,專著《一九八○年代以來漢語新詩的聲音研究》,於臺灣的《清華學報》、香港的《東方文化》和大陸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當代作家評論》《揚子江評論》《戲劇藝術》《華文文學》等重要期刊發表文章四十餘篇。
目錄
【序一】新詩與聲音/楊揚
【序二】/奚密
【推薦語】復旦大學中文系郜元寶教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張松建教授
導言:二十世紀八○年代以來漢語新詩創作的聲音轉向
楊牧:靜佇、永在與浮升
陳黎:「奇妙的獨聲合唱」
張棗:疾馳的哀鳴
陳東東:輪迴與上升
藍藍:震顫的低音
附錄一 反觀「太陽」意象中同聲相求的句式
附錄二 從城市詩看破碎無序的辭章
跋
【序二】/奚密
【推薦語】復旦大學中文系郜元寶教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張松建教授
導言:二十世紀八○年代以來漢語新詩創作的聲音轉向
楊牧:靜佇、永在與浮升
陳黎:「奇妙的獨聲合唱」
張棗:疾馳的哀鳴
陳東東:輪迴與上升
藍藍:震顫的低音
附錄一 反觀「太陽」意象中同聲相求的句式
附錄二 從城市詩看破碎無序的辭章
跋
序
序一
新詩與聲音
楊揚
中國古典詩講究聲韻平仄,在詩學理論上,清楚明白,讓人記得住,用得上。而現代新詩在理論上破除了傳統聲韻格律的限制,主張話怎麼說,詩就怎麼做,從白話詩到自由詩,從現代格律詩到三十年代的現代詩和戰時大學校園詩歌,有關聲音與現代新詩問題的一波又一波的探討,似乎始終沒有一個理想的解決方案。那麼,什麼是現代新詩中的「聲音」呢?
聲音問題在現代新詩發展過程中,沒有產生像古典詩歌聲韻格律這樣明確的規範,但也不是沒有自己的探索。它是隨著新詩審美形態的不斷變化而形成自己的關注焦點。胡適的白話詩歌理論,突現的是五四時期那種沖絕一切、放手一搏的自由解放精神。傳統意義上的「聲音」,也就是聲韻格律,在那時是被視作束縛手腳的鐐銬。隨之而起的「聲音」主流,是郭沫若筆下的狂飆體自由詩的情感節奏;和周作人等宣導的委婉含蓄、意蘊悠遠的「小詩」。至於聞一多、徐志摩等海歸派的現代格律,強調新詩中的國粹精華,體現了現代新詩的傳統回歸。之後,滬上現代詩的崛起,再一次新潮湧動,以強烈的都市氣息,唱響詩壇。抗日的戰火,帶給詩歌的,是東西南北、混雜而有力的共鳴,像街頭朗誦詩、西北的信天遊、西南聯大的校園詩歌等,都洋溢著強烈而旺盛的生命力。詩歌中的聲音不再是線性的單數,而是民族多元文化的匯通。新中國成立,新詩的天空盤旋著勝利者的讚美旋律,新民謠和賽詩會此起彼伏,排山倒海的群眾性詩歌運動構成了詩壇奇觀。七十年代散布於四處的星星點點的地下詩人們,以有別於群眾性吟誦的方式,重啟詩歌之路。但個人的憂鬱而含混的傾述,與時代憂患意識的聯結,讓很多人在詩的朦朧中想像著廣場、紀念碑。此後,漢語新詩的聲音探討別開生面地與搖滾時聚時離,藉助音樂的力量前行。
一般而言,朦朧詩之前的新詩聲音軌跡,在詩學理論中有比較清晰的描述,而此後就顯得比較含混和個人化。這一方面是詩歌本身有很多改變;另一方面也是市場經濟結束了詩的抒情時代。但詩與詩學理論並沒有就此終結,詩歌還在,詩歌與聲音的關係等理論問題還在。作為一個關注當下詩歌以及詩學理論的研究者,翟月琴對新詩以及詩學問題有自己的思考。她的思考最重要的兩個支柱,一是參與詩歌活動所獲得的感性經驗;二是系統化的學術訓練。從研究生時期到今天,她始終積極參與詩歌活動,傾聽詩人們的意見和建議,使她對當代詩歌的探索軌跡有一種自己的理解。在她以往發表的諸多有關新詩創作的評論中,浮現於她閱讀視野的詩歌作品以及重要詩人的訪談,呈現著研究者鮮明的個人體驗和理論傾向。她似乎有意識地要將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後的漢語新詩的探索軌跡,繼續延長出來,將她熟悉和喜愛的詩人作品推薦給大家。如她對楊牧、陳黎、張棗、陳東東、藍藍作品的評介,非常觸目地將這些詩人的詩作安放在詩歌發展長廊中,希望引發研究者的關注、研究。與此同時,翟月琴試圖從詩歌發展的脈絡來思考新詩發展的核心問題,也就是聲音在現代新詩中的價值與作用。尤其是藉助當下詩人詩作對「聲音」的不同理解和表現,展示「聲音」在新詩中的豐富性和重要價值。
翟月琴的這些新詩研究和評論,受到國內同行的好評,一些重要的文學評論刊物和研討活動,也常有她文章和活動蹤影,這些都是她長期努力取得的成績。現在她的詩歌評論彙編出版,無論如何,這都是一件好事。我願意推薦給大家,是為序。
序二
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是近年來海內外學術界的一個熱門話題,對此傳統的梳理自有其意義,提出的若干見地也很有價值。但是在此同時,某些前提卻誇大了中國和西方之間的差異,彷彿抒情是中國文學的核心,卻並非西方文學所長。其實,西方文學又何嘗不擁有悠久輝煌的抒情傳統呢?古希臘詩人如莎弗(Sappho)是公認的世界文學經典,即便是希臘史詩,也不能簡單的以敘事詩來定義它。讓我們以西方最古老的史詩—荷馬的《伊利亞德》(The Iliad)—為例,別忘了詩的第一行就明講,它詠歌的主題既不是特洛伊戰爭,也非神人之紛擾,而是希臘聯軍第一勇士阿吉裡斯因痛失摯友「一怒而動天下」(the wrath of Achilles)。整首詩寫情—友情、親情、愛情、同袍之情—催人淚下。
回溯西方文學的源頭,「抒情詩」(lyric)一詞來自希臘文的七弦琴(lyre)。希臘神話裡,奧費爾斯(Orpheus)是最偉大的詩人、歌者(現代考證認為確有其人)。他手握七弦琴,歌聲讓鳥獸草木都為之動容,甚至感動了閻羅王,讓他從陰間將亡妻帶回人世(雖然最後他忍不住回頭而永遠失去了她)。
反觀中國傳統亦如是。《詩經》是遠古的歌謠,《楚辭》是楚地的歌詞,古詩宋詞元曲都有配樂。詩與歌合一本是古代普世的現象,直到今天我們仍說「詩歌」。甚至放眼現代詩百年史,雖然詩與歌正式分家了,但是兩者的結合並未停止,且屢見佳作。從五四時期胡適的《希望》(歌名改為《蘭花草》)、徐志摩的《偶然》、劉半農的《叫我如何不想他》,到當代余光中的《鄉愁四韻》、鄭愁予的《錯誤》、木心的《從前慢》等等,都透過旋律而相得益彰,膾炙人口。
然而,總體來說,現代詩也隱含了一個悖論,代表了一個挑戰:在脫離了音樂之後,詩如何透過聲音來抒情?換言之,詩如何結合文字和它所承載的聲音——而不是外加的旋律——來表達意義,強化藝術效果?翟月琴教授的新書針對這個問題提出獨到深刻的見解。她對「聲音」的定義既簡單扼要,又通透完備:
這裡的聲音,指的是語音表達(音韻、聲調)、辭章結構(停頓、分行)、語法特點(構詞、句式)、語調生成(語氣、姿態)等形式的合體。
聲音在詩裡的作用是多元、多層次的。它跟文字之間的有機互動,既無所不在又隱而不顯。透過作者敏銳的觀察和細膩的分析,我們對五位重要的現代詩人有了新的理解。更重要的是,此書建構了一套關於聲音的理論性論述,開闊了現代詩研究的角度。在閱讀翟月琴的「聲音詩學」的同時,我們聽到了她清晰明朗,獨一無二的聲音。
奚密
新詩與聲音
楊揚
中國古典詩講究聲韻平仄,在詩學理論上,清楚明白,讓人記得住,用得上。而現代新詩在理論上破除了傳統聲韻格律的限制,主張話怎麼說,詩就怎麼做,從白話詩到自由詩,從現代格律詩到三十年代的現代詩和戰時大學校園詩歌,有關聲音與現代新詩問題的一波又一波的探討,似乎始終沒有一個理想的解決方案。那麼,什麼是現代新詩中的「聲音」呢?
聲音問題在現代新詩發展過程中,沒有產生像古典詩歌聲韻格律這樣明確的規範,但也不是沒有自己的探索。它是隨著新詩審美形態的不斷變化而形成自己的關注焦點。胡適的白話詩歌理論,突現的是五四時期那種沖絕一切、放手一搏的自由解放精神。傳統意義上的「聲音」,也就是聲韻格律,在那時是被視作束縛手腳的鐐銬。隨之而起的「聲音」主流,是郭沫若筆下的狂飆體自由詩的情感節奏;和周作人等宣導的委婉含蓄、意蘊悠遠的「小詩」。至於聞一多、徐志摩等海歸派的現代格律,強調新詩中的國粹精華,體現了現代新詩的傳統回歸。之後,滬上現代詩的崛起,再一次新潮湧動,以強烈的都市氣息,唱響詩壇。抗日的戰火,帶給詩歌的,是東西南北、混雜而有力的共鳴,像街頭朗誦詩、西北的信天遊、西南聯大的校園詩歌等,都洋溢著強烈而旺盛的生命力。詩歌中的聲音不再是線性的單數,而是民族多元文化的匯通。新中國成立,新詩的天空盤旋著勝利者的讚美旋律,新民謠和賽詩會此起彼伏,排山倒海的群眾性詩歌運動構成了詩壇奇觀。七十年代散布於四處的星星點點的地下詩人們,以有別於群眾性吟誦的方式,重啟詩歌之路。但個人的憂鬱而含混的傾述,與時代憂患意識的聯結,讓很多人在詩的朦朧中想像著廣場、紀念碑。此後,漢語新詩的聲音探討別開生面地與搖滾時聚時離,藉助音樂的力量前行。
一般而言,朦朧詩之前的新詩聲音軌跡,在詩學理論中有比較清晰的描述,而此後就顯得比較含混和個人化。這一方面是詩歌本身有很多改變;另一方面也是市場經濟結束了詩的抒情時代。但詩與詩學理論並沒有就此終結,詩歌還在,詩歌與聲音的關係等理論問題還在。作為一個關注當下詩歌以及詩學理論的研究者,翟月琴對新詩以及詩學問題有自己的思考。她的思考最重要的兩個支柱,一是參與詩歌活動所獲得的感性經驗;二是系統化的學術訓練。從研究生時期到今天,她始終積極參與詩歌活動,傾聽詩人們的意見和建議,使她對當代詩歌的探索軌跡有一種自己的理解。在她以往發表的諸多有關新詩創作的評論中,浮現於她閱讀視野的詩歌作品以及重要詩人的訪談,呈現著研究者鮮明的個人體驗和理論傾向。她似乎有意識地要將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後的漢語新詩的探索軌跡,繼續延長出來,將她熟悉和喜愛的詩人作品推薦給大家。如她對楊牧、陳黎、張棗、陳東東、藍藍作品的評介,非常觸目地將這些詩人的詩作安放在詩歌發展長廊中,希望引發研究者的關注、研究。與此同時,翟月琴試圖從詩歌發展的脈絡來思考新詩發展的核心問題,也就是聲音在現代新詩中的價值與作用。尤其是藉助當下詩人詩作對「聲音」的不同理解和表現,展示「聲音」在新詩中的豐富性和重要價值。
翟月琴的這些新詩研究和評論,受到國內同行的好評,一些重要的文學評論刊物和研討活動,也常有她文章和活動蹤影,這些都是她長期努力取得的成績。現在她的詩歌評論彙編出版,無論如何,這都是一件好事。我願意推薦給大家,是為序。
2018年元月於滬上
序二
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是近年來海內外學術界的一個熱門話題,對此傳統的梳理自有其意義,提出的若干見地也很有價值。但是在此同時,某些前提卻誇大了中國和西方之間的差異,彷彿抒情是中國文學的核心,卻並非西方文學所長。其實,西方文學又何嘗不擁有悠久輝煌的抒情傳統呢?古希臘詩人如莎弗(Sappho)是公認的世界文學經典,即便是希臘史詩,也不能簡單的以敘事詩來定義它。讓我們以西方最古老的史詩—荷馬的《伊利亞德》(The Iliad)—為例,別忘了詩的第一行就明講,它詠歌的主題既不是特洛伊戰爭,也非神人之紛擾,而是希臘聯軍第一勇士阿吉裡斯因痛失摯友「一怒而動天下」(the wrath of Achilles)。整首詩寫情—友情、親情、愛情、同袍之情—催人淚下。
回溯西方文學的源頭,「抒情詩」(lyric)一詞來自希臘文的七弦琴(lyre)。希臘神話裡,奧費爾斯(Orpheus)是最偉大的詩人、歌者(現代考證認為確有其人)。他手握七弦琴,歌聲讓鳥獸草木都為之動容,甚至感動了閻羅王,讓他從陰間將亡妻帶回人世(雖然最後他忍不住回頭而永遠失去了她)。
反觀中國傳統亦如是。《詩經》是遠古的歌謠,《楚辭》是楚地的歌詞,古詩宋詞元曲都有配樂。詩與歌合一本是古代普世的現象,直到今天我們仍說「詩歌」。甚至放眼現代詩百年史,雖然詩與歌正式分家了,但是兩者的結合並未停止,且屢見佳作。從五四時期胡適的《希望》(歌名改為《蘭花草》)、徐志摩的《偶然》、劉半農的《叫我如何不想他》,到當代余光中的《鄉愁四韻》、鄭愁予的《錯誤》、木心的《從前慢》等等,都透過旋律而相得益彰,膾炙人口。
然而,總體來說,現代詩也隱含了一個悖論,代表了一個挑戰:在脫離了音樂之後,詩如何透過聲音來抒情?換言之,詩如何結合文字和它所承載的聲音——而不是外加的旋律——來表達意義,強化藝術效果?翟月琴教授的新書針對這個問題提出獨到深刻的見解。她對「聲音」的定義既簡單扼要,又通透完備:
這裡的聲音,指的是語音表達(音韻、聲調)、辭章結構(停頓、分行)、語法特點(構詞、句式)、語調生成(語氣、姿態)等形式的合體。
聲音在詩裡的作用是多元、多層次的。它跟文字之間的有機互動,既無所不在又隱而不顯。透過作者敏銳的觀察和細膩的分析,我們對五位重要的現代詩人有了新的理解。更重要的是,此書建構了一套關於聲音的理論性論述,開闊了現代詩研究的角度。在閱讀翟月琴的「聲音詩學」的同時,我們聽到了她清晰明朗,獨一無二的聲音。
奚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