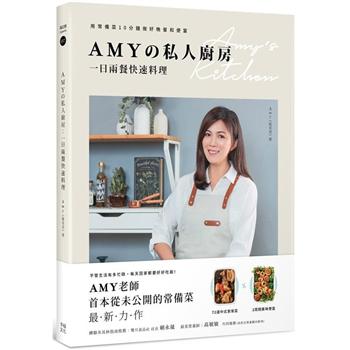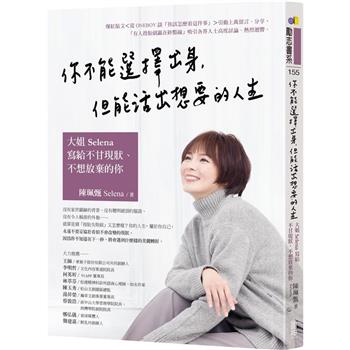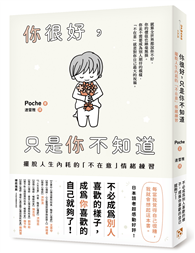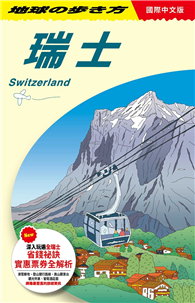我年輕時,就是一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並且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但也時常對社會主義各國此起彼伏的政治內亂感到大惑不解,還覺得各國官方的宣傳有不少弄虛作假的成分;認為「自由平等的聯合體」不應該有這些弊端,長此以往,國際共運很可能會有大麻煩。後來,在博覽群書過程中,我偶然讀到蘇共黨員、黨內民主派代表人物羅伊.麥德維傑夫在國外發表的有理有據的一批著作,這才茅塞頓開:原來,在社會主義時代,史達林式一黨專政的政治體制,居然是反馬克思主義的。這種理論讓我耳目一新,完全顛覆了我對於長官意志和專家教授的盲目迷信。甚至認識到,「官越大越正確」、「領袖最正確」、「老百姓最無理」這種傳統「真理」,就像太陽繞著地球轉這種傳統信念一樣荒誕不經。此後,在學習馬克思主義時,我堅決不再吃「權威」們嚼過的饃,而是獨立自主地去鑽研馬克思恩格斯原著;並且採用馬克思的座右銘“懷疑一切”這種辯證法利器,去觀察和思考國際共運的歷史和現狀。
就在我越來越關注國際共運時,史達林式一黨專政——其本質是領袖專政——這種視民意如草芥的政治體制終於自食惡果了:共產主義世界出現了雪崩式的垮塌,原有三十多個社會主義國家竟然近百分之九十都垮臺了。有道是,亡羊補牢,猶未為晚。更奇葩的是,剩餘的寥寥幾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執政者,無一例外,仍然自我感覺良好,仍然拒絕修補「羊圈」,仍然死死抱緊史達林專制獨裁體制的大臭腳堅決不放,拒不改過自新、還政於民。不久,我有了一種使命感:一党專政即領袖專政這種所謂的「正統」體制,並不是正宗的,而是歪宗的;如不撥亂反正,這種顯失公平、厝火積薪的舊體制,遲早會把下餘幾個社會主義國家也推進萬劫不復的深淵;我有信心,有能力,依據馬克思恩格斯的教誨,依據國際共運的歷史經驗和教訓,獨創出一套關於國際共運歷史、現狀和前景的集大成的理論。
經過十年準備,十年苦熬,我終於在2011年底,完成了長篇現實政治小說《紅黑夢》和本書的寫作。個中艱辛,不堪回首。然而,磨難遠未結束。在中國大陸,出版自由只是停留在憲法條文上,僅是說說而已;凡是獨立思考的作品,皆被官方認定是「反動」的,即便你在依據馬克思主義擺事實講道理也照樣「反動」;出版之難,難於上青天。無奈之下,我只得到「萬惡」的資本主義自由中去碰運氣。生命不息,奮鬥不止。在多次遭受白眼,碰得頭破血流之後,終於,2015年5月,《紅黑夢》初版在臺北問世。2016年8月,《紅黑夢》修訂版在臺北問世;目前,在臺北國家圖書館和香港中央圖書館均可讀到此書。臺灣網路上也有介紹。歡迎讀者諸君閱讀賜教。那部小說與本書,體裁不同,主題完全一致。我的書主要是寫給中國大陸幾千萬能理性思考的中青年黨員和億萬平民的,但何時能返回故鄉出版發行,尚不知;但我堅信這一天不會太遠。好在,我寫書之初就為作品下了三四十年不許過時的「死命令」,即使晚十年二十年「回家」,其威力照樣不減。
我是入黨三十多年的不圖名利、只講良心的老共產黨員,我認為中國大陸的政治體制已經老掉牙了,必須改弦易轍。沒有政治體制現代化做堅實基礎,經濟現代化就缺乏強有力的保障;即便能夠在某個時期突飛猛進,最終也難免是為人作嫁。基礎不牢,地動山搖。教訓太多了,明擺在那裡,不必贅述。
為了避免紅色中國去蹈蘇聯東歐等一大堆白忙活紅色政權的覆轍,我不僅創立了民權社會主義一整套理論,還未經教育主管部門批准,擅自創辦了民權社會主義自修大學,計畫招收數千萬青年才俊,共同幹一番震古鑠今的偉業。在招生公告中,我曾寫道:「每位優秀學生大體上按照我在書中確定的戰略和策略,採用自己認為最恰當的具體方式,為我們的民權千年偉業努力工作。」近日,我偶然想到:在奮鬥過程中,必定會有優秀學生因想不出“恰當的具體方式”而發愁。為了幫這部分同學戰友排憂解難,我在上面這段話之後再作如下補充:「如果您確實想不出恰當方式的話,那麼,我建議您向生活圈子中的有志才俊聊聊民權社會主義原理。如果經您的拼搏,有十名以上的英才苗子購買了本書,成了我們志同道合的戰友,那麼,我承認您就是本校最優秀的學生。並且,您有權成為這個學友群的群主。還有,在自願集資前提下,當學友們舉辦馬克思恩格斯原著研討會、新年聚餐、假日旅遊等聯誼活動時,您還是實至名歸的代理召集人。」
我不是科班出身,是個野寫家兒。對此,我並不自卑,甚至還有少許慶倖哩。假如我真是科班出身,那反而糟了;那一堆一堆奴性十足、酸氣熏天的政治學教授就會害慘我,把我的靈氣打殺淨盡,把我誘騙成毒化成和他們一樣可悲的牆頭草。我的知識和力量來自社會大學,來自特立獨行的觀察和深思。在運拙時乖的幾十年中,我將中國大陸八大行業即工、農、兵、學、商、政、党、知識份子全部幹完;我深知柴米油鹽平民的可憐,也知仰人鼻息順民的可悲,更知有名無實公民的可笑。我敢於不看“上面兒”的臉色,智小謀大地為民請命,就像莽撞的牛闖入了客廳,也許會掃了文人雅士的興,驚了昏睡公民的夢。細細想來,這,對於紅色中國長遠利益來說,未必是壞事。
我自認為是魯迅和柏楊的學生。我師柏楊先生的墓誌銘「不為君王唱讚歌,只為蒼生說人話」是我立身處世的座右銘。我原本是謙和、怯懦、孤僻的弱者,但我基於「重刮魯迅風,再造國民性」的初衷,在寫作本書時,羊質虎皮地刻意模仿了柏楊先生狂放、狂妄、離經叛道的文風。這種筆法是獨闢蹊徑還是不知天高地厚,我無權去評判。相信讀者朋友能夠明鑒。
我當然不敢自詡已經掌握了什麼真理,我的理論僅是毛坯或引玉之磚而已。如果能夠引起中國政論界,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道路前提下,對於“中國向何處去「這一巨大政治問題進行體制內的百花齊放式的理性探討和激辯,以便多數決定,擇善而從,興利除弊,繼往開來,我這一套四本書的目的也就達到了。如果有鴻儒將我駁得體無完膚,我將很樂意放棄我的全部觀點,並虛心向他學習;畢竟,我們不是敵人,都是為了使紅色中國長治久安。如果有專橫跋扈的惡霸,蠻不講理,硬說鑽研馬克思恩格斯原著就是犯上作亂,硬說誰僥倖執政誰就無限正確並且絕不允許制約,硬說黨員和公民只能有盲目聽話的「神聖權利」,硬要用「怎麼?你敢不服?!」這類黑社會流氓話來大言相駭,甚至硬要給我扣上死有餘辜的現行反革命大帽子把我「拉出去」,那麼我就要奉送給大人先生們關於舍生存義的兩句先烈格言——我自橫刀向天笑,留取丹心照汗青。
我是個上不了大雅之堂的鄉野粗人,沒有什麼文化,玩不轉陽春白雪,只會說一些下里巴人的大白話。以上拉拉雜雜地扯了不少,將就著算是序吧。書中錯誤之處在所難免,懇請各方有識之士不吝斧正。
最後,向出版社的長官和編輯致以最誠摯的謝意!
笑天2018年2月3日訂正本書時於曼哈頓作坊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中國向何處去 第 1 冊(簡體字版) : 民權社會主義原理平民版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458 |
中文書 |
$ 458 |
政治 |
$ 468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中國向何處去 第 1 冊(簡體字版) : 民權社會主義原理平民版
作者用宏觀的角度,以馬克思主義為本,為中國政治體制的未來走向提出全新的見解。
本書內容闡述社會主義的真諦,並分析中國實行社會主義的歷程及現狀。作者詳述國際共運的起源與發展,並考據了西方國家的憲政制度、中國近代史、三民主義、台灣及國際政治現狀等等,旁徵博引,資料豐富,文筆淺白,既可作為學術研究的參考資料,也適合普羅大眾增長常識。
作者簡介:
笑天
大陸共產黨員,基層官員。研究馬克思主義及國際共運二十餘年。
作者序
我年輕時,就是一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並且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但也時常對社會主義各國此起彼伏的政治內亂感到大惑不解,還覺得各國官方的宣傳有不少弄虛作假的成分;認為「自由平等的聯合體」不應該有這些弊端,長此以往,國際共運很可能會有大麻煩。後來,在博覽群書過程中,我偶然讀到蘇共黨員、黨內民主派代表人物羅伊.麥德維傑夫在國外發表的有理有據的一批著作,這才茅塞頓開:原來,在社會主義時代,史達林式一黨專政的政治體制,居然是反馬克思主義的。這種理論讓我耳目一新,完全顛覆了我對於長官意志和專家教授的盲目迷信。甚...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上編回顧
第一章天呀!馬恩設想的新社會居然是民權至上的
第一節無產階級專政與社會主義是截然不同的兩個階段
第二節社會主義經濟的建立應尊重廣大群眾的意願
第三節社會主義社會是沒有階級的自由平等的聯合體
第四節黨在革命和專政階段的強力領導及其後的淡出和消亡
第五節人民與領袖是主僕關係,必須防範領袖
第六節民主共和、自由自治、寬容宗教
第七節因歷史局限而過時及反對教條的理論
第八節本章小結:民權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
第二章列寧主義的力量與弱點
第一節力量之一:鐵板一塊的布爾什維克黨
第二節力量之...
第一章天呀!馬恩設想的新社會居然是民權至上的
第一節無產階級專政與社會主義是截然不同的兩個階段
第二節社會主義經濟的建立應尊重廣大群眾的意願
第三節社會主義社會是沒有階級的自由平等的聯合體
第四節黨在革命和專政階段的強力領導及其後的淡出和消亡
第五節人民與領袖是主僕關係,必須防範領袖
第六節民主共和、自由自治、寬容宗教
第七節因歷史局限而過時及反對教條的理論
第八節本章小結:民權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
第二章列寧主義的力量與弱點
第一節力量之一:鐵板一塊的布爾什維克黨
第二節力量之...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