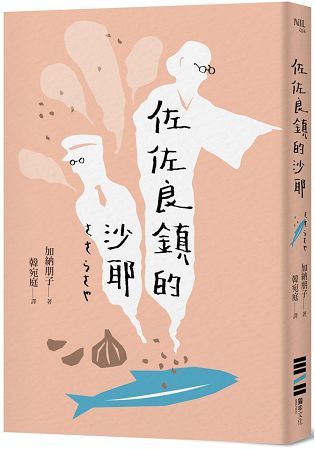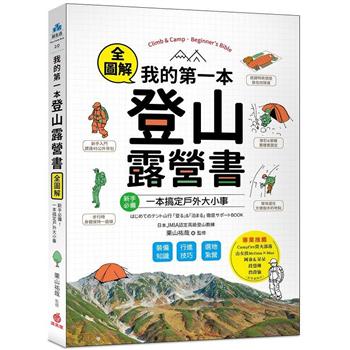「妳要幫我在鰹魚上多加點大蒜喔!」
丈夫留下這句遺言就過世了──再見面時,
呃、他成了可以附身在別人身上的幽靈偵探。
丈夫留下這句遺言就過世了──再見面時,
呃、他成了可以附身在別人身上的幽靈偵探。
悲劇轉成喜劇 平凡寫出不凡
從「親人之死」中溫柔淬出對「生」的憐惜
浪漫唯美的推理魔術師──加納朋子
獨一無二 笑中帶淚的家庭懸疑故事
沙耶最最喜歡的丈夫優太郎死了,
她帶著寶寶小裕從搶奪監護權的親戚那兒連夜逃走,
心好痛,努力在東京建立的小家庭也隨著丈夫的死而破碎,
未料命運將她引到了完全料想不到的歸宿……
死後若再一次見到所愛的人,
你會準備什麼樣的遺言呢?
故事|
第一次死別時來不及出口,
第二次一定要大聲說出最棒的遺言,
那就是……
人煙稀少的老溫泉小鎮,冒出了個陌生茫然的年輕女孩,
她推著大大的嬰兒車,像艘沒了指北針的船地在鎮上盪來晃去。
鎮民七嘴八舌起來──原來,她是東京來的沙耶,
死了丈夫又從搶小孩監護權的親戚那兒逃來此處,
身世很可憐,嘴角卻不思議地掛著柔柔笑意。
一些「看得見」的鎮民更發現,她的身後,
居然跟著一名跨大步、神色坦蕩的青年幽靈!
幽靈正是沙耶露出笑容的祕密,他是丈夫優太郎,
目前暫留人間,偶爾附身在活人身上來見妻兒。
如今,新手媽媽沙耶帶著小嬰兒小裕,
與新手幽靈丈夫在佐佐良鎮展開新生活。
但,這座小鎮怎麼這麼多怪事呢?
入住的屋子被侵占、鄰居婆婆偷拆信件、
路上更撞見自稱間諜,並被餐廳店員綁架的時髦老奶奶、
還有一間會在夜半哭泣、後院藏著骨頭的鬧鬼旅館!
怪事解決不完,嬰兒還像隻任性的小動物,
「我不要等!現在就要!」地嚎啕大哭。
好險,日子拚命過,沙耶連抱起嬰孩都嫌瘦弱的手臂長出肌肉,
心也堅強起來,唯一無法克服的、只有對丈夫的濃濃思念。
她總抱著兒子想:優太郎啊,真的真的很想你,希望你現在就來見我呀。
但,幽靈爸爸卻唱起反調,愈來愈少現身……
他去哪了?還是,他不在了呢?
|關於沙耶&優太郎的推理:佐佐良鎮的六件怪事
失蹤的間諜老婆婆:〈少了指北針的船〉
沙耶第一次從東京來到佐佐良鎮,人生地不熟,
兒子肚子餓得哭起來時,連哺乳都不知在哪比較恰當。
好不容易遇到一位伸出援手的時髦老奶奶。
感謝之餘,她和奶奶隨意地閒聊起來,
老奶奶說起自己是個間諜、又說被家庭餐廳員工監視,
沙耶沒當真,沒想到老奶奶卻在不久後離奇失蹤……
鬧鬼的溫泉旅館:〈笹之宿〉
家裡熱水器還沒裝好,天氣冷得不得了,
沙耶不得已,只能帶著兒子到外頭旅館投宿一晚。
洗溫泉時,一直聽到不似人類的古怪聲響,
房間門口,還莫名其妙地多了一雙不屬於自己的拖鞋……
奇怪的空箱:〈空箱子〉
年輕的沙耶交到三位上了年紀的新朋友──
好奇心旺盛的奶奶、時髦的奶奶、與愛吃溫泉饅頭的奶奶,
三位奶奶沒事就來串門子,逗逗嬰兒小裕,順便鬥鬥嘴。
就算三人唇槍舌戰,還是保持著恐怖平衡般的和平關係,
然而一個溫暖和煦的日子,她們竟因一個空箱大打出手,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被綁架的孩子:〈鑽石男孩〉
沙耶不善言辭,帶小裕到公園晒太陽時,
總無法招架其他好奇媽媽的連珠炮問題,
直到一位帥氣女性像英雄般解救了她!
「我不是誰的妻子,也不是誰的媽媽,我是繪里香!」
如此介紹後,和沙耶一樣獨自養育孩子的繪里香便成了她的好友。
繪里香總神采飛揚,無比帥氣,兩人有講不完的話題。
某天,沙耶在路上瞥見了神色慌張的繪里香,
她似乎收到一封綁架孩童的綁架威脅信……
看得見鬼的女子:〈等待的女人〉
沙耶家的不遠處,住著一名奇妙的鄰居。
那是上了年紀的女子,她總披頭散髮、穿著隨性,
不顧世人窺伺眼光地坐在門戶大開的庭院,癡癡望著遠方。
像在等著一個不會歸來的人。
來自老家的禮物:〈佐佐良鎮的沙耶〉
優太郎的家人不斷寄來各式各樣的禮物:
可愛的小熊寶寶、昂貴的鐘、美麗的檯燈;
還寄了信來,強求沙耶把小裕送回優太郎的家。
但沙耶將禮物全退了回去,她什麼都不要,
她只想努力保護被遠方親戚虎視眈眈著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