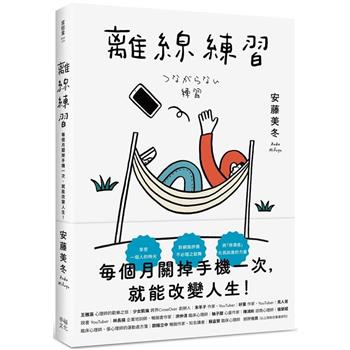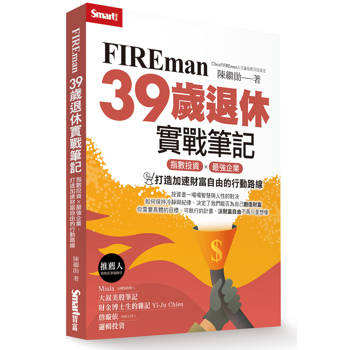柏克萊新生活
在八月底的周日上午,從庫柏蒂諾開車前往柏克萊,本來應該是個值得慶祝的時刻。布蘭達卻莫名地有種像要參加葬禮的難受感。米爾頓帶了辛蒂,開著紅色BMW跑車在前面,布蘭達、庫柏和安妮塔則在休旅車裡緊跟著。那天早上,米爾頓小心翼翼地將布蘭達整齊地放在大門口的行李箱放進已塞滿東西的休旅車後車廂。
米爾頓在前一天就清理好他紅色BMW裡面的東西,並到史蒂文斯溪大道的洗車廠,要求「全套服務」。米爾頓就像矽谷其他大多數優秀的工程師一樣,在過去五年裡,已經跟他的車建立緊密關係。前幾天,他同意為了布蘭達而放棄自己心愛的BMW,照顧孩子時,休旅車顯然比較實用。他覺得彷彿在跟一個人,而不是車說再見。
米彌爾頓和女兒辛蒂在BMW車裡親切地聊著天,隨著各種話題,辛蒂跟她爸爸提起她在暑期幼兒園認識的新朋友-瑪麗蓮。
「爸爸,你認識瑪麗蓮嗎?」
「親愛的,我不認識瑪麗蓮。」
「為什麼不認識,她是一個很好的女孩啊!」
「我相信她是一個很好的女孩,我只是說我不認識她。」
「那麼,你那天應該見見她。她會讓你印象深刻的。」
「我很高興聽到關於瑪麗蓮的事 。告訴我,妳是怎麼認識妳的新朋友瑪麗蓮的。」
米爾頓自己輕聲地笑了起來,因為他回想起前一天晚上,描述他洗車時使用的短語「印象深刻的」。
這時,在深綠色休旅車裡,安妮塔僵硬地坐在前座,布蘭達很緊張地握著方向盤。庫柏緊緊地被繫在幼兒座位,一路上非常聽話。布蘭達覺得這不是讓她媽媽說出真實感受的時間,所以大部份時候都是沉默地開車,但偶爾會解說沿途的地標性建築。
「那裡的奧克蘭看起來很不錯,不是嗎?媽媽,和孩子們從傑克倫敦廣場搭火車到西雅圖應該很有趣才對!」
「難道妳不記得我告訴過你,我和妳爸在幾年前,你們都還在印度時搭過嗎?」
「哦!我忘記了!那一定很棒 。」
「媽,妳看海灣大橋,多麼美麗呀!幸好我們現在不需要開到舊金山。」
路途中,大部份的時間安妮塔都保持沉默,只對布蘭達提出的話題作簡短的回答。安妮塔沒隱瞞她滿腹的擔心,也很不高興錯過了星期天早晨的瑜伽課;一週中,她最喜歡蒂帕老師的瑜伽課。但最重要的,她擔心一大堆其他事情:
布蘭達的婚姻會不會破碎?她優秀的孫子們會不會因布蘭達不在身邊而「被犧牲」?布蘭妲一整個學期一個人獨自住在柏克萊會不會不安全?
安妮塔一向是既有條理又有紀律的母親。現在的她顯然有失常態,布蘭達家明顯的不確定變化讓她感到不安。
在八月的美麗星期天,開車從庫柏蒂諾出發到柏克萊是很輕鬆的。非下班的時間只要50分鐘的車程,因此布蘭達和米爾頓都認為,布蘭達可以時常來回通勤。米爾頓的BMW繼續開向大學大道,朝向雄偉的柏克萊校園和遠處的綠色山丘駛去。
開過校園南邊的夏塔克街(Shattuck Avenue)時,辛蒂指著前方校園西邊的一列尤佳利樹,問她爸爸那裡是媽媽的學校嗎?
「我想是吧!親愛的。」
「我可以常來看她嗎?」
「當然可以。」
行前,布蘭達告訴了米爾頓宿舍的方向和宿舍號碼,米爾頓有點猶豫地開進校園北邊盡頭的已婚宿舍。這兒有長長的車道,通往多戶家庭的住處,他想一定是這裡了,因為布蘭達就緊緊地跟在他後面。
從米爾頓和安妮塔的觀點來看,布蘭達一定瘋了,才會離開家來住這裡。已婚學生宿舍跟富裕的庫柏蒂諾和整個矽谷地區相比,是較髒亂的。在他們的心目中,布蘭達好像要改住修道院,過苦修的生活。這一區的公寓帶有草坪,幾乎所有的前院周圍都散落著便宜、色彩鮮豔的塑膠玩具,有溜滑梯、水池和三輪車等等。在這裡,「已婚學生」很明顯的是指「已婚且有小孩的人。」
不像在南印度的家門口有共用庭院,這些豐富多彩的玩具只是靜靜的存在著, 沒有孩子遊玩的身影。即使在這特定的住宅區,生養孩子在這所頂尖公立大學學生心目中也不是優先項目;布蘭達第一次來到柏克萊時就這麼覺得,而她現在又被這畫面提醒了一次,年幼的孩子是會讓人分心的,甚至會被視為敵人也說不定。在這裡的年輕人大都具有好勝心,又加上學業的高壓,沒有剩餘的精力來生養孩子。
布蘭達原以為選擇已婚學生宿舍做為她的第二個家,比較符合自己身為媽媽和太太的身份。但從她同學們的角度來看,布蘭達卻成了很精明,甚至有點計算過度的人。他們雖然貧窮,卻是很努力的知識分子,他們可能以為布蘭達在打如意算盤,一方面爭取到校園裡夢寐以求的便宜公寓,又有先生和媽媽在校園以外照顧她的孩子,布蘭達不用因為需要照顧家庭而分心,又能自在地追求學術研究。
把車停在車道後,安妮塔、米爾頓和兩個孩子,從休旅車的後車廂,搬出一些物品到布蘭達的新家:一箱廚房用具、兩個小箱子和工作有關的東西,還有書本和兩個塞滿衣服的大皮箱。米爾頓將布蘭達的兩個大皮箱搬進室內,但不想一路搬進臥室,他把皮箱整齊的放在窗邊的沙發上。安妮塔將廚房用具帶進室內,放在厨房爐灶旁邊,與她一絲不苟的個性相反。她根本不想費心打開箱子,或瀏覽四周的電器用品。她只將箱子放在地板上,就轉身回到前院。
辛蒂抱著兩個裝在小鏡框的照片走進房門,然後放在廚房桌上。一張照片是在今年年初拍的獨照,她自信地站在幼兒園的溜滑梯上面。辛蒂似乎沒有意識到,她實際上很接近溜滑梯邊緣,一不小心就可能掉到下面的沙堆裡。第二張照片也是辛蒂挑的。這張是她和庫柏在庫柏蒂諾的房子拍的,仙蒂把手環繞著弟弟,擺出比他們實際年齡還要老成的姿勢。儘管有辛蒂的手臂支撐,在照片裡才一歲多的庫柏,似乎還是很困難地站著。
米爾頓、安妮塔和兩個孩子幫布蘭達把東西搬到公寓後,他們承諾很快就會再來「探望」她。接著,米爾頓熟練地將幼兒安全椅從他的BMW拿出來,放在休旅車的第二排座位上。安妮塔坐在副駕駛座上把安全帶繫上,兩個孩子這時也跳進車裡。然後,他們就離開了。「太倉促了!」,布蘭達心中感覺不太舒坦。現在才星期天早上十一點半而已!
「為什麼他們這麼快就離開?我們還沒吃午飯呢!」
又一次,一如她整個夏天絕望了無數次,布蘭達用她的「區分化理論法」澆熄了這些負面的想法。
「他們因為暫時無法以過去的方式跟我說話,所以需要快速離開。他們將盡快接受這個改變,然後以新的方式與我溝通。」
布蘭達回到屋裡,開始整理一些物品。她帶著一個小背包,裝著她的筆記型電腦和配件。她慢慢走到米爾頓搬進來的行李箱旁,接著把辛蒂留下的照片移到餐桌上,再把媽媽放在廚房的箱子搬進來。
她機械式地打開安妮塔留下的箱子,幾乎像個孩子一樣,專注於媽媽熱切地想要她學習的東西,以便得到認可和喜愛。箱子裡面有鐵鍋、兩個不同尺寸的碗和小煎鍋。布蘭達緩緩地將四個炊具都放在爐子上,然後走到裝著剩餘物品的箱子。前一周,她就買了四組便宜的盤子和餐具、一個裝鹽的調味瓶、幾個畫有香港天際線的杯墊,鍋鏟、湯匙和水瓶墊。布蘭達看起來像是以慢動作沿著地面滑行,她深陷憂傷,以至於這些簡單的物品顯得比實際上重很多。
突然地,布蘭達把鏟子放在廚房的桌上,把頭靠在上面,然後無法控制地啜泣和抽搐,她從不曾如此地失控的哭過。在斷斷續續地抽泣中,她慢慢地從廚房摸索走到客廳的舊沙發旁。眼淚從她的臉頰緩緩地留下來,她以微弱和顫抖的聲音問自己:「我在做什麼?我到底在做了什麼……? 」
四十五分鐘後,她感覺腳已麻木時,布蘭達突然聽到有輕輕的敲門聲。眼睛哭得腫腫的,腳站不穩,她慢慢移到門口,並遲疑地打開門。
「嗨!我是歐爾佳。我們住隔壁。」
「嗨!歐爾佳,我是布蘭達。」
「我只是來打個招呼,我們來自烏克蘭。我先生是物理系的,我們有兩個小孩。」
「我也有兩個小孩,但他們現在沒有跟我在一起。」
「我有看到妳搬進來,所以我想要說聲嗨!一切都還好嗎?妳看起來剛哭過。」
「很高興妳來看我。我正在拆箱,等我安頓好就會去拜訪妳。我很想見見妳的孩子。」
布蘭達優雅又果斷地向歐爾佳說再見後,又一波的傷感襲上心頭。在沒有孩子、先生和媽媽的保護下,她感到孤寂又空虛。
布蘭達情緒瀕臨崩潰時,有件事奇蹟地在她心裡浮現,像一顆新種子開始發芽。一開始造成她極度疼痛的感覺,慢慢轉變成不同的生活象徵:一個充滿無限可能性的新生活的開始。日子一天天過去,布蘭達發現自己還是能記起那天轉換生活象徵的影像。
這並不是說,她的生活突然地變好,其實從來沒有不好。從這點來看,她選擇的路,給了她更好的生活價值觀,也似乎能挑戰她自己最大潛能,大多數的人甚至從來沒有看見如此遼闊的山景。出人意料地,布蘭達提高了自我意識。這和她身為媽媽、太太或女兒沒有任何關係。更確切地說,她突然地意識到了,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潛力。
她的新鄰居歐爾佳‧莫羅茲打斷了她不愉快的思潮,布蘭達開始準備接下來新家需要的實用物品。她發現自己餓了,而且需要囤積一些基本糧食。隨著突然爆發的能量和決心,她先放棄整理計劃,拿起BMW的鑰匙,往門外走去。她決定去買一周的日常用品。她聽說在幾英里以外,沙特克大街有一家不錯的雜貨店。
「哇!」隔壁的歐爾佳和孩子們異口同聲地說:「妳的車好漂亮!妳一定很有錢。」
布蘭達一時無法反應過來,不知道該如何應付這説話誠實又刺耳的新鄰居,只好淡淡地向她打招呼,再以最快的速度鑽進車裡。只不過一個小時左右的時間,和歐爾佳短短的兩次見面卻為布蘭達在柏克萊的最初幾個月定了主題。
第一,和歐爾佳第一次見面的時刻也就是布蘭達新生命的開始。就像一顆含有飽滿水分和營養,即將慢慢長成大樹的橡樹種子,布蘭達開啓了她的上升軌道,一個永不停止自省、分析,理解世俗和考慮周到又善良的生活方式。
第二個主題則跟「錢的問題」有關,在歐爾佳對柏克萊的紅色BMW發表令人不愉快的評論時觸發。
她說「妳一定很有錢」是什麼意思?我有錢並不關她的事。布蘭達這麼想。
她真正的經濟狀況是否比一般同學好,並不是重點;以一個柏克萊博士生而言,更重要的是了解與接受大部份柏克萊人對金錢、財富的意識形態。 在來柏克萊之前,布蘭達已經潛意識的接受了矽谷人對金錢的看法,而這些看法和校園内大多數人對金錢的態度有不可解的矛盾。在研究所第一年期間,布蘭達重新定義她對「金錢問題」的理解:
在柏克萊那些認同「富人」的人,和那些決意與「窮人」結盟的人,有極大的思想差距。
布蘭達很快就發現,和大學相關的人群中,沒有誰真的很窮,所以在這個團體中,沒有人是真正的「窮人」。不過,在這大學城裏有很多工人、學生和居民,這些不富裕而且時時受到財務挑戰的人,在政治思想上,與對財富有野心的人鮮明的劃清立場。
布蘭達在柏克萊的第一個課程是關於「金錢問題」再教育。這個課程與真正面對貧困無關,卻和理解「貧困的政治」(politics of poor)有關。
一個人的政治立場是什麼,又選擇什麼樣的財富象徵來支持或否定一個人的政治立場?
身為香港移民,布蘭達在童年就被教導,或意識到人類可能墜入的貧窮深淵。她的父母以自身經驗告訴她和吉兒真正的貧窮是什麼,他們教導孩子們避免讓任何事、人、想法和符號來遮掩貧窮的可怕真面目,不要被政治謊言和口號誤導而相信貧窮有浪漫的一面這一類假象。布蘭達記得媽媽每天告訴她貧窮有多麼可恥,如果可以掌控的話,她和吉兒絕對不能以戲謔的態度對待貧困。
因此,布蘭達的再教育,大部分是重新理解她父母的經驗,這些經驗不是那些在美國出生的人能了解的。
布蘭達30歲時,第一次面對柏克萊經濟和政治風氣。這個問題挑戰了她小時候對貧窮的認知。她學到的是:要嘛你有錢並且「富有」;要嘛你沒有錢且「貧窮」。北加州大學小鎮的風氣是:
最重要的不見得是你實際上有錢與否,而是你是否想通對於金錢和財富的態度。換句話說,一個人對於平等與否的看法,是你如何在校園生活中適當地表達自己。
因為這台紅色的BMW,使得布蘭達從第一天搬進柏克萊就得面對這個現象。從歐爾佳對於「有錢人」的評論,布蘭達認為,身為藝術史研究所一年級的博士生,在這神聖的柏克萊山丘,開著紅色的BMW不太合乎身分。如果布蘭達開普通的車,會更妥當些。開一輛較普通的車象徵布蘭達和大部份柏克萊文科研究生一樣,具有相同的意識形態。
這個不平等的議題挑戰了布蘭達。這台紅色的BMW系列跑車一直讓米爾頓在庫柏蒂諾上班場合很自豪。但停在一邊是廉價的嬰兒設備,一邊是把車道作為臨時游泳池的塑膠浴缸的已婚學生宿舍,這台BMW很顯然地跟這個環境脫節了。
幾個星期前,一向注重細節的布蘭達,在庫柏蒂諾無意中想到車子的問題。既然要把孩子們和米爾頓留在庫柏蒂諾,她應該選跑車,把休旅車留給他們。米爾頓和安妮塔帶孩子們參加各種活動,會需要休旅車。在庫柏蒂諾,每個人幾乎都談論且開著高級車。她知道米爾頓需要休旅車,而不是跑車。布蘭達認為他能夠適應,而且很快地會感激布蘭妲的縝密心思,預見帶孩子時會需要較大的車。
細心的布蘭達卻沒想到,她象徵財富和繁榮的跑車往北開30英里,停在柏克萊的已婚學生宿舍時會與周圍環境如此不協調。在重思想的柏克萊,擁有財富的象徵反而成了累贅。所以,布蘭達在柏克萊的第一天,她人生中第一次面對「錢的問題」,且意識到周遭的激進想法:
有時候想法比實質的東西更重要。
當然,這個發現對布蘭達來說也有種解放的感覺,身為一位充滿潛力的藝術歷史學生,意識到這種想法是令人愉悅的。突然間,所有認識她的人都會覺得她的想法可以跟累積的物質、財富一樣重要;或者她選擇成為藝術歷史學家(她須學習、教學和討論想法)可能與經商致富一樣重要。
布蘭達從雜貨店回來時,這個發現已經在她體内發酵─-她需要儘快出售紅色的BMW,換一輛能配合她身為媽媽和學生身分的車。再者,她將有好幾個週末會和孩子們在一起,所以有一輛更實用的車帶孩子們參加各種活動是必要的。
為什麼我沒早想到呢?我可以在柏克萊或靠近奧克蘭的電報街上其中一家汽車代理商換一台適合的車。
過了一會兒,她放下東西,並決定打電話給米爾頓。
「嗨,米爾頓!我是布蘭達。」
「我知道!妳還好嗎?」
「還可以吧。我試著安頓好一切。如果我將BMW拿去換另一台車,你會介意嗎?我覺得在這裡開這種車不合適。」
米爾頓停頓了好一會兒,讓布蘭達知道,她觸碰了他的痛處。
「喔!好吧!雖然我很喜歡那輛車,但是我也正準備把它換了。我沒有意見。」
「謝謝,米爾頓! 或許明天晚上再聊囉!」布蘭達說完,就掛電話了。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再見柏克萊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90 |
二手中文書 |
$ 237 |
現代小說 |
$ 255 |
小說/文學 |
$ 264 |
中文書 |
$ 264 |
Literature & Fiction |
$ 270 |
現代小說 |
$ 270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再見柏克萊
她,兩個孩子的媽,跨進三十歲門檻時,
勇敢地隻身前往柏克萊追求學海之夢。
她蓄滿能量,引領家人,走向新家園。
大象,從古老印度開始,被認為是吉祥動物。
象群逐水源而居,由年長母象帶領,
不時必須走往新水源建立新家園。
布蘭達和米爾頓帶著孩子返回美國的安樂窩,米爾頓的公司即將上市,收入優渥,一家四口過著平穩的生活。
但熱愛藝術的布蘭達,懷有做研究的夢想。本書描寫這位三十歲面臨人生轉型期的女子,如何在接獲夢寐以求的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南亞藝術歷史系的入學通知書後,一方面追尋夢想,一方面應付來自社會、家庭的壓力。
她成功重返校園,實現自我,並將家人帶往新家園,一如印度象群的母象。
作者簡介:
郝洛吉(Roger Hale)‧錢德純(Elizabeth Chien-Hale)
三十年前,他們兩人於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相識、相戀,進而結婚。當年,郝洛吉在柏克萊攻讀印度歷史博士學位,錢德純研習工程及語言學。如今,郝洛吉白天教學,利用餘暇寫作。錢德純是專利律師,也是一名語言學者。過去三十年來,他們兩人待過印度、香港、中國、台灣,最後決定以美國加州聖荷西為家。
兩人第一本合作小説是《來去印度:三個旅人的故事》(四塊玉文創,2015),書中的兩個人物,黃光遠(米爾頓)和王布蘭達,成了他們合作的第二本小説《再見柏克萊》的主角。《再見柏克萊》描寫黃家夫婦從印度回到了美國庫柏蒂諾後的生活。根據作者本身多年的觀察、親身體驗、思考和相互討論,寫出了年輕夫婦在家庭和事業中遇到的衝突和相互扶持,以及反映出中國和印度文化的交集。
TOP
章節試閱
柏克萊新生活
在八月底的周日上午,從庫柏蒂諾開車前往柏克萊,本來應該是個值得慶祝的時刻。布蘭達卻莫名地有種像要參加葬禮的難受感。米爾頓帶了辛蒂,開著紅色BMW跑車在前面,布蘭達、庫柏和安妮塔則在休旅車裡緊跟著。那天早上,米爾頓小心翼翼地將布蘭達整齊地放在大門口的行李箱放進已塞滿東西的休旅車後車廂。
米爾頓在前一天就清理好他紅色BMW裡面的東西,並到史蒂文斯溪大道的洗車廠,要求「全套服務」。米爾頓就像矽谷其他大多數優秀的工程師一樣,在過去五年裡,已經跟他的車建立緊密關係。前幾天,他同意為了布蘭達而放棄自...
在八月底的周日上午,從庫柏蒂諾開車前往柏克萊,本來應該是個值得慶祝的時刻。布蘭達卻莫名地有種像要參加葬禮的難受感。米爾頓帶了辛蒂,開著紅色BMW跑車在前面,布蘭達、庫柏和安妮塔則在休旅車裡緊跟著。那天早上,米爾頓小心翼翼地將布蘭達整齊地放在大門口的行李箱放進已塞滿東西的休旅車後車廂。
米爾頓在前一天就清理好他紅色BMW裡面的東西,並到史蒂文斯溪大道的洗車廠,要求「全套服務」。米爾頓就像矽谷其他大多數優秀的工程師一樣,在過去五年裡,已經跟他的車建立緊密關係。前幾天,他同意為了布蘭達而放棄自...
»看全部
TOP
作者序
前言
我和太太錢德純(Elizabeth Chien-Hale)於二O一五年一月在台灣出了一本中文短篇小說《來去印度:三個旅人的故事》。隔年,我們將原作做了一些修改,在二O一六年九月以英文標題《Three Chinese Travellers in India》,由一家新德里的出版社在印度發表英文版。書中描述三位擁有中國血統的旅人在印度追夢的故事,他們分別是來自台灣的年輕女郎、住在中國北京即將退休的男士,以及美國矽谷工作的年輕男工程師。每個人前往印度的原因不同,而且待在那裏的時間長短也不一。
在Three Chinese Travellers in India中,第二個故事的重要角色...
我和太太錢德純(Elizabeth Chien-Hale)於二O一五年一月在台灣出了一本中文短篇小說《來去印度:三個旅人的故事》。隔年,我們將原作做了一些修改,在二O一六年九月以英文標題《Three Chinese Travellers in India》,由一家新德里的出版社在印度發表英文版。書中描述三位擁有中國血統的旅人在印度追夢的故事,他們分別是來自台灣的年輕女郎、住在中國北京即將退休的男士,以及美國矽谷工作的年輕男工程師。每個人前往印度的原因不同,而且待在那裏的時間長短也不一。
在Three Chinese Travellers in India中,第二個故事的重要角色...
»看全部
TOP
目錄
前言
Chapter 1柏克萊我來了
Chapter 2柏克萊新生活
Chapter 3柏克萊新天地
Chapter 4柏克萊新人脈
Chapter 5布蘭達與媽媽
Chapter 6庫柏蒂諾的夏日時光
Chapter 7布達蘭與米爾頓
Chapter 8柏克萊的第二年
Chapter 9印度研究之一:坦加布爾、馬杜賴和亨比村
Chapter 10印度研究之二:撰寫博士論文
Chapter 11歸鄉!活水泉源
Chapter 1柏克萊我來了
Chapter 2柏克萊新生活
Chapter 3柏克萊新天地
Chapter 4柏克萊新人脈
Chapter 5布蘭達與媽媽
Chapter 6庫柏蒂諾的夏日時光
Chapter 7布達蘭與米爾頓
Chapter 8柏克萊的第二年
Chapter 9印度研究之一:坦加布爾、馬杜賴和亨比村
Chapter 10印度研究之二:撰寫博士論文
Chapter 11歸鄉!活水泉源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郝洛吉、錢德純
- 出版社: 四塊玉文創 出版日期:2018-03-12 ISBN/ISSN:9789869576598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40頁 開數:17*23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