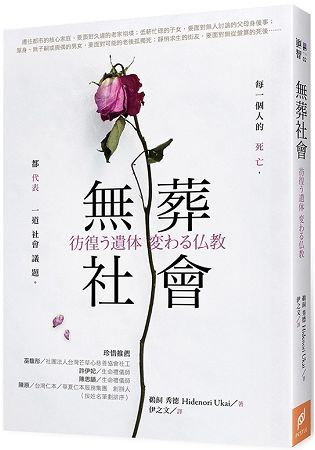當火葬場從未如此不敷使用,
反映著我們願意花多少時間心力好好道別?
隨著新世代的經濟能力與人際網絡改變,開始有人傾向簡化喪葬,並視之為與社會連結的終止──不造成麻煩與節省花費的乾脆作法,成了某些人選擇喪葬形式的首要條件。省略葬禮步驟讓亡者直接湧向火葬場,醫院也不足以容納尚未能火化的遺體。如果有親族子嗣安排後事的亡者,或許會被盡力妥善安置,然而日本也開始出現子嗣在亡者火化後,不知如何接續安排,便將骨灰罈刻意遺忘在電車置物架……
排不到火葬場、不會舉行的慎重葬禮、親族連葬禮都不會聚首討論;死亡尚且淡薄,生而在世時,又能體會到多少支持與陪伴?如此從死亡透出生存世界的不易。
身處科技、醫學、經濟革新都不斷超出想像,似乎無所不能的時代,
有沒有可能實現不願孤單死去的生命心願?
孤獨死不是單身者的專利。即便有子嗣也不能保證老後生活條件,有配偶者亦可能在喪偶後重新建立一人生活;老後的存款和經濟能力,可能無法維繫生活品質。隨著死亡越趨真實,有人希望死後能被好好安置,考量學術單位會一併祭祀大體老師,便登記同意死後捐贈為大體。
社會條件無以讓人安心面臨老年生活,當新聞報導孤獨死的狀況總是非常悽慘,屍水穢物滲透進整間屋舍物品的紋理,然而真實現場只有更加駭人;難道生前努力過日子,死後只能成為社會棄如敝屣的孤獨死屍嗎?這股恐懼推動了大體捐贈風潮,大體數量多到學術單位來不及消化,有些大體捐贈數年後才被解剖。大體捐贈原是一種奉獻心意,卻扭曲成了交付後事的途徑。
遺骨從土葬轉變到靈骨塔,
現在,更多人想與樹合一,或乾脆消失在汪洋之中。
由於考量無人祭祀、不想造成麻煩或是經濟能力條件,樹葬與海葬成了新興選擇。但是,哪一片海域願意成為海葬地點呢?當地有沒有漁民,會不會影響漁獲銷售?日本當地規定不可在推廣海葬業務時,列出海域地點;然而也有社群主動成為海葬地點,藉由喪葬帶來的人潮,意圖振興沒落的濱海小鎮。
如果我們可以正面討論死亡,是不是在消除死亡代表的孤獨之餘,還可以翻轉死亡帶來的「負面影響」;不再迴避死亡,打破禁忌疆界的社群,更有機會找到出口。
多數人敬而遠之的無家可歸者,
你不知道他們怎麼生存,更不明白他們如何面臨死亡。
書中以援助無家可歸者的佛教團體「一匙會」為例,作者參與了一匙會每月兩次的例行援助工作,和志工一起煮飯、做飯糰,接著上街分送給無家可歸者。飯糰並非定點發送,堅持「不是請他們來拿」,而是「帶去給他們」,一位位親自送到身邊,送到他們生活的地方,便可同時獲知他們的其他需求。
一匙會也因為慢慢參與無家可歸者的生活,得知了他們對死亡的看法──如果死後仍然可以和街頭夥伴在一起,身後事會被尊重地安排,竟然提升了某些人對生活的追求力量。這是一匙會在日本的經驗。
那麼,在台灣呢?
社會上每個對死亡漠不關心的人,創造了無葬社會。
我們如何面對死亡,最終反映了社會如何看待生命。
本書特色
1.聚焦死亡與喪葬長年來被忽略的議題。比起選擇何種葬禮,這個時代更迫切的問題是──無力承接死亡!低薪時代爭取足以買房的居住正義、最低工資的漲幅……但是度過了生存還不是最後一關;多數人只規劃到退休金額,但你是否想過,有多少人即將付不出喪葬費。
2.每一個人的死亡,都是一道社會議題。遷往都市的核心家庭,如何面對久違的老家祖墳;低薪忙碌的子女,如何面對無人討論的父母身後事;單身、無子嗣或喪偶的男女,如何面對可能的老後孤獨死;靜悄求生的街友,如何面對無從盤算的死後……
3.從相關產業看見社會如何因應死亡。遺物整理業者,看見生活物件如何連結亡者和遺族的心;禮儀業者,看見如何與珍惜之人共度最後時光;遺體保存業者,看見高齡化的死亡人數逐年攀升,並且都市生活無法讓遺體返回自宅安歇的難處。
作者簡介:
鵜飼 秀德(Ukai Hidenori)
1974年(昭和49年)6月生於京都市右京區。
自成城大學文藝學系畢業後進入報知新聞社,分發到社會新聞部門。2005年(平成17年),轉職進入日經BP社,先後擔任經濟雜誌《日經商務週刊》記者等職務。2016年(平成28年)4月起,擔任資訊雜誌《日經休閒》副總編輯,活用曾在社會案件、政治、經濟、宗教、文化等領域廣泛採訪的經驗,負責撰寫多篇企劃型報導。近年關注北方領土爭議,三度進入現場採訪。
在此同時,也擁有淨土宗僧侶的身分。1994年(平成6年)起入行淨土宗少僧都養成講座(全3期),1996年(平成8年)於淨土宗傳宗傳戒道場(加行)成滿。現為京都市嵯峨的正覺寺副住持。(譯註:入行、加行、成滿皆為淨土宗用語。)
曾於大學或宗教界舉辦多場演講。現任京都市景觀市民會議委員。
著有《寺院消滅:失落的「地方」與「宗教」》(暫譯,寺院消滅──失われる「地方」と「宗教」)(2015年,日經BP社出版)。
譯者簡介:
伊之文
翻譯生涯邁入第八年,挑戰過的領域包括親子教育、心理勵志、醫療保健、文學小說與童書,覺得自己能譯完《無葬社會》是功德一件。
工作邀約與譯文賜教:jptrans.tw@gmail.com
噗浪:www.plurk.com/inohumi(譯恐遲遲龜)
章節試閱
日漸稀薄的家庭關係帶來孤獨死
住在北海道旭川市的川田雄二(五十七歲,化名),最近經常和妻子討論「如何迎接臨終」。川田的叔叔幾年前於八十六歲時孤獨死,然後他們夫妻又經歷了看護父親的經驗,對於「老後」和「死亡」的意識便升高了。
三年前,川田的叔叔在自家淋到熱水,於瀕死狀態下被人發現。他叔叔一輩子單身,靠著接受生活保護度日;因為非常討厭醫院,硬要回家而讓病況惡化,最後在無人照護的情況下過世。高齡者的「獨居」和「貧困」,讓他們經常與生命危險為伍。
川田還來不及為叔叔的死感到悲傷,就換成要辛苦地看護父親。他父親罹患失智症、前列腺癌和糖尿病,被認定為「失能等級5」(無人看護就幾乎不可能進行日常生活的狀態)。他父母住在釧路市內,離旭川很遠。原本是由高齡母親在「老老看護」的狀態下照顧父親,但也已經達到了極限。
川田的母親原本是出了名的愛乾淨,卻因為疲於看護而弄壞了身體,過著置身在灰塵與壁蝨之間的生活,看不下去的川田為父母在札幌市內租了提供看護服務的高齡者住宅。
川田的兄弟姊妹分別住在札幌或旭川,卻不積極協助照顧父母。
他姊姊斷然說道:「是你擅自把他們帶回來的,不要丟給我們!」姊弟關係就此破裂。川田的妻子每兩天會從旭川去一次札幌照顧父親,這樣的生活持續了兩年。最後,他父親留下一句「我撐不下去了,我想死」便過世了。
年邁母親在不久的將來,也可能會孤獨死或需要人看護。不,豈只如此,因為叔叔和父親的死,川田和妻子開始對老後感到不安。川田雖然有孩子,但畢竟是核心家庭,所以只要夫妻其中一方先過世,另一方就成了孤單一人。
基於這兩次經驗,川田夫妻「不想給孩子帶來麻煩」的想法越來越強烈,他們完全不打算讓孩子來照顧老後的自己。「我和太太想在七十歲以前死去。如果可以,先由我照顧妻子,然後我想在不麻煩孩子的情況下獨自死去。」
兩千七百萬名孤獨死預備軍
從JR新宿車站出來,走在山手線沿線的新大久保地區,可以看到一處巨大的集合住宅。這是都營的百人町三丁目、四丁目公寓,通稱「戶山社區」。在L字形的建地內蓋了十六棟大樓。
「這裡每個月都會發現高齡者的孤獨死遺體,一年有二十件左右。新宿區的孤獨死大約有三分之一發生在這個社區,完全是異常事態。」身為社區居民之一,同時也是致力於孤獨死對策的NPO法人「人人連結會」會長本庄有由(七十八歲),如此半自嘲地說著。
戶山社區的人口約有三千兩百人,大概有兩千三百個世帶,亦即七成以上居民是獨居狀態;就連自治會組織也由於高齡化而解散,即使社區裡有高齡者死亡,很少馬上就發現。
儘管本庄這麼說,但他的妻子已經先行過世,只剩自己在社區裡過著獨居生活;本庄幾年前曾因為心臟病病倒,自己其實也離孤獨死很近。讓本庄坐立難安,進而創立NPO的契機發生在十年前,當時他目擊了某個悲慘現場──在本庄居住的大樓高樓層,一名七十二歲男性在死後五十天被人發現;當時是十二月,但由於開著暖氣,腐敗速度很快。「那景象非常慘烈。那位男性是在床上過世的,但房間裡卻像是灑了重油般的狀態,人都沒有形狀了。即使是冬天,蛆和蒼蠅仍然從陽台爬了出來。強烈的臭味附在我身上洗不掉,連續三天吃不下飯。」
回過神來,這個社區已經接連出現這種孤獨死了。
孤獨死在不同自治體有著不同定義。以新宿區來說,死後十五天以上才被發現的稱為「孤獨死」,死後十五天內被發現的稱為「孤立死」。由於這個社區沒有自治會,所以無法確切掌握孤立死和孤獨死的總數,不過本庄說「恐怕有幾百件吧!」。
無家可歸者的社會映照出日本實態
從下午兩點半起,一匙會開始準備煮飯救濟街友,志工一個接一個地聚集到光照院來。用大鍋炊煮有志之士捐贈的二十升白米,做成每個三百克的特大飯糰,這樣的飯糰每次都要做兩百個以上,光是這樣就是要花上三到四小時的重度勞動。
這些飯糰會分給街友每人一個,最近還有在日越南人佛教徒參與活動,這時就會多了手工製的炸春捲當作配菜。如果有人需要,也會給予市售藥品或內衣。這對每個街友來說,或許只是「少少一匙」的援助,但他們總是期盼著一匙會每個月兩次的到來。
不是「請他們來拿」,而是「帶去給他們」,這一點據說很重要。
如果讓街友親自前來,在發放食物的地方排隊,可以想見會引起地方居民反彈。另外,也因為有些人是高齡者或身體不適而無法前來排隊,直接送到他們枕邊可說是最確實的做法。不僅如此。要掌握街友的真實樣貌,實際拜訪他們的「住處」是最好的。
他們都是背負著各式各樣的過去才成了街友。出了意外導致身體有障礙的人、遭到裁員而使生活陷入困境的人、沒有親人的高齡者、小時候被父母虐待而生病的人、過去曾沾染犯罪的人、逃離家暴丈夫的女性……不得不過著街友生活的人太多了,說不定我們有一天也會面臨相同境遇。
然而,有許多人基於某些因素而無法住進那些社會福利設施,事實上也的確還有許多街友存在。
日本發生的各種事情,也反映在無家可歸者的社會中。在筆者參加一匙會活動的這天,工作人員總共有十幾位,包括上野在內,總共分成五條路線(山谷地區、淺草附近和隅田川沿岸等等)來分發食物。共有二百零五位街友領到了飯糰。
雖然與街友對話的時間很有限,但若問他們身體狀況如何,還是有很多人會回答身體不舒服。從一匙會開始活動已經過了七年,許多工作人員和街友都熟識了。除了感冒藥、胃藥和藥膏之外,工作人員還會準備對抗花粉症的口罩、內衣和糖果等等,不夠時會記錄在筆記本上,日後再把物資確實交到本人手上。
我前去拜訪時,附近大樓的溫度計顯示十三度,許多街友都感冒了,也有很多人表示胃腸不適。
他們會對同樣身為街友的人表示關心。經常有街友告訴我們:「我拿到了,可是那個人還沒拿到哦!」抱著獨善其身想法的街友反而是少數。
無家可歸者之間強韌的牽繫
二○○八年(平成二十年)正月,吉水來到新宿中央公園。雖然此時正逢過年,但是對街友而言,這段時間不但沒有行政支援,工作也中斷,不僅不值得開心,更是一段面臨生死的嚴苛時光。為了援助這些街友,NPO相關人士和支援者在公園裡搭起帳篷,準備好要發放食物和接受醫療諮詢。
這時,一位男性街友的訴說讓吉水受到很大的衝擊:「反正我們都會橫屍街頭,只會變成無緣佛而已。但是,一想到死後也能和過世的夥伴或現在的夥伴一直在一起,我就能夠更努力地活下去。」
臨終的瞬間也是如此。他們痛切地希望,臨終時不是一個人在街頭死去,而是想要受到夥伴的看顧。
「我覺得街友之間的牽繫極為強韌,他們那種既非血緣也非地緣的夥伴意識非常強烈。這樣的牽繫是他們活下去的必備要素,那位街友教會了我這一點。雖然這說起來很理所當然,但朋友死了會覺得悲傷,如果夥伴死在自己眼前,也會想要弔唁他。啊啊――這就是人情吧!和尚不是經常說嗎?『假如決定了死後的去處,就能活力充沛地活在當下。』我以為自己懂得這個道理,還對檀家這麼提倡。然而透過和街友對話,我才變得能夠自信地說出那句話。然後,我便下定決心要以一個宗教家的身分,以實際行動支援無家可歸者。」
許多無家可歸者的臨終充滿了悲哀。有夥伴看顧的人還算好的。假如死在街頭卻沒被夥伴發現,就會由行政人員公事公辦地接收遺體,在火葬場有空的時間火葬,接著通知家人;如果沒有人要接收,遺骨就會安置在某處靈園的無緣塔中祭拜。「從過去到現在,有許多街友的存在就在死後被消除了。」吉水如此說明。
日漸稀薄的家庭關係帶來孤獨死
住在北海道旭川市的川田雄二(五十七歲,化名),最近經常和妻子討論「如何迎接臨終」。川田的叔叔幾年前於八十六歲時孤獨死,然後他們夫妻又經歷了看護父親的經驗,對於「老後」和「死亡」的意識便升高了。
三年前,川田的叔叔在自家淋到熱水,於瀕死狀態下被人發現。他叔叔一輩子單身,靠著接受生活保護度日;因為非常討厭醫院,硬要回家而讓病況惡化,最後在無人照護的情況下過世。高齡者的「獨居」和「貧困」,讓他們經常與生命危險為伍。
川田還來不及為叔叔的死感到悲傷,就換成要辛苦地看護父親。...
目錄
作者序
第一章 徬徨的遺體與遺骨
火葬得等上十天的現況
遺體旅館繁榮的時代
增加的大體捐贈與被丟棄的遺骨
超高齡社會所帶來的孤獨死悲劇
「重設」孤獨死現場的人們
第二章 逐漸變遷的喪葬
沒有喪禮的葬儀場
有著一萬具遺骨的都心大樓
浮在日本海上的散骨島
理想的墓在新潟
集結無數的遺骨做成佛像
「僧侶宅配」讓吃不飽的僧侶動起來
佛具商所看見的「寺院消滅」
第三章 締結緣份的人
預防孤獨死的緣份形式
供養街友的僧侶
在難民營興建圖書館
地域再生與寺院
連結都市與地方寺院
第四章 佛教的存在意義――專訪佐佐木閑
日本佛教特殊的成立過程
為了活在現在者的佛教
作為社會收容處的佛教
以「戒律」精神來檢討現代日本
本質沒變,是型態變了
後記
相關資料
參考文獻
作者序
第一章 徬徨的遺體與遺骨
火葬得等上十天的現況
遺體旅館繁榮的時代
增加的大體捐贈與被丟棄的遺骨
超高齡社會所帶來的孤獨死悲劇
「重設」孤獨死現場的人們
第二章 逐漸變遷的喪葬
沒有喪禮的葬儀場
有著一萬具遺骨的都心大樓
浮在日本海上的散骨島
理想的墓在新潟
集結無數的遺骨做成佛像
「僧侶宅配」讓吃不飽的僧侶動起來
佛具商所看見的「寺院消滅」
第三章 締結緣份的人
預防孤獨死的緣份形式
供養街友的僧侶
在難民營興建圖書館
地域再生與寺院
連結都市與地方寺院
第四章 佛教的存在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