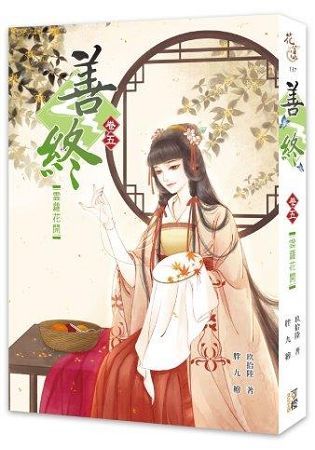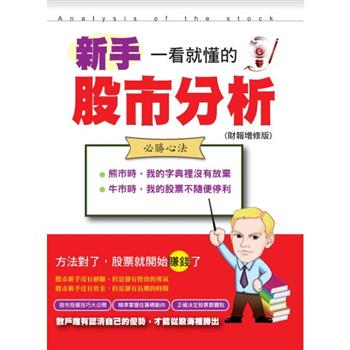宅門內部的血緣鬥爭,世家之間的利益糾葛,與兒女情長的愛恨纏綿,
起點女頻言情天后[玖拾陸],最細膩動人的重生之作!
穆連瀟帶著失蹤九年的穆連康和妻兒回京,途經桐城,終於從穆堂的口中知道了當年的真相。滿門忠烈的由來竟是如此可怕,他從未想過,原來至親亦能心狠至此。
定遠侯府喜迎兒孫賦歸,唯獨二房冷眼旁觀,母子再見的戲碼感動不了他們,可隔不了多久,卻有更驚天的消息劈頭蓋臉的砸了過來!
當事態逐漸與前世有所不同,杜雲蘿卻怕了。不能再提前預防、無法再預測心理,即便如今二房勢弱,她也不禁擔心未來的日子真能如此順利?敵人斷不會就此罷休,但已不知將來變化的她,該如何面對接下來暗藏的危機?她知道,一定還有什麼在等待著他們……
【人物介紹】
杜雲蘿
杜家三房杜懷禮嫡女,杜家最小的五姑娘,母親甄氏。前世驕縱,與周遭人皆不能真心交好,出嫁後更與娘家斷絕關係,雖與丈夫穆連瀟恩愛,卻年紀輕輕成了寡婦,得了貞節牌坊一座。重生回到說親前,一改脾氣,成為貼心懂事的掌上明珠,並決心在此生與穆連瀟共同面對背後的敵人。
穆連瀟
定遠侯世子,穆府三爺。父親穆元策隨老定遠侯戰死,母親周氏。少年俊朗,性情溫和直率,能文亦能武。逐漸體認到侯府內的不單純,在古梅里之戰中更是受到自己人的偷襲,重傷回歸後,開始著手調查過往的真相。
穆連康
定遠侯府三房嫡長子,母親徐氏。九年前與穆連瀟在迎靈的回程中失蹤,不知下落。幸而多年後於嶺東與穆連瀟相認,但卻失去記憶,已有妻兒。與其父面貌神似,身形魁梧,武藝極高。
穆連慧
定遠侯府二房嫡女,為連字輩唯一姑娘,受封嘉柔鄉君。同為再活一世之人,看似不願再循前世軌跡,行事卻令人摸不透。今生改嫁平陽侯么孫晉尚。
葉毓之
景國公府小公爺的庶長子,安冉縣主的兄長。自幼被廖姨娘當成景國公接班人培養,能文能武,個性亦十分坦蕩直率。在景國公府的刻意打壓之下,獨自前往嶺東跟隨黃大將軍,打下相當不錯的戰績。
作者簡介:
玖拾陸
死宅一名,愛烤肉愛火鍋,愛筆下的各種角色。
擅長古言,愛女主,也愛各款女配,相信不管什麼出身、什麼性格的「女配」,都有追求自己理想和幸福的機會,為此,96一直在努力。
在《善終》之後,古言破案的《棠錦》也要結束了,近期在構思一個全新的故事,書名很可愛,叫《威武不能娶》,一樣是甜寵文,希望能比《善終》更甜三分,也希望有機會能讓大家看到這兩本書。
再次感謝打開這本書的你。
繪者
胖九
大家好,我是胖九,一個平日愛好吃肉、睡覺、逗貓的宅女。比較迷糊,反應慢半拍,記憶力差,常被朋友稱為「金魚腦袋」。歡迎各位編輯大人來約稿~喜歡我作品的朋友們也請來找我聊天吧~微博@胖九愛吃肉。
章節試閱
風毓院裡,穆元謀和練氏一道用了午飯。
自打穆連慧嫁出去之後,練氏總算不會時不時被氣得胸口疼了,只是看著空空的東跨院,心裡就牽掛。這就是討債鬼,在眼前時她氣得厲害,見不到了又放不下。
練氏只好把心思擺在了等穆連誠回來上。眼瞅著入了臘月了,總歸就是這幾天。
董嬤嬤打了簾子進來,練氏抬頭問她:「老董,是不是連誠回來了?」
「老爺、太太。」董嬤嬤垂手道:「是世子送了信回來,說是啟程時耽擱了,要年後抵京。」
穆元謀放下手中茶盞,抿唇道:「是連瀟寫的?」
董嬤嬤縮了縮脖子:「奴婢是聽柏節堂裡的人說的,老太君和大太太看了信,應當是世子的手書沒錯。」
穆元謀的眼神一沉,揮了揮手,讓董嬤嬤退出去。
屋裡的珠姍和朱嬤嬤也機靈,跟著退了,裡頭只剩下穆元謀與練氏。
練氏只知道穆元謀在山峪關有安排,可具體是什麼安排,要何時動手,如何行事,穆元謀沒有跟她解釋仔細。這會兒聽了董嬤嬤這幾句話,也不曉得事情是成了還是沒有成。
張嘴想問一句,但見穆元謀緊繃著臉,練氏嚥了口唾沫,沒有問出口。
反正,穆元謀想說了就會說,不想說,她追著問,豈不是又成了沉不住氣的人了?
那還不如先忍著。
練氏眼觀鼻、鼻觀心,努力把穆連瀟的事扔到腦後去,只想著穆連誠,一時半會兒倒也沒有那麼急切了。
穆元謀的指腹沿著茶盞口子劃著。他沒有收到棋子的消息。那一封信之後,就再沒有消息了。
穆元謀沒有急切,頻繁的書信來往才容易叫人抓住把柄,只要能按計畫奇襲,棋子偷襲了穆連瀟,那計畫就成了。在事成之後,棋子到底是生是死,去了哪裡,他並不關心。
或者說,死了最好,死人才不會洩漏秘密。
棋子沒有送信回來,也許是死在了大漠裡,讓穆元謀再無後顧之憂。
而現在,柏節堂裡收到了穆連瀟的信。
奇襲成了?他還活著?他甚至還能動手寫信?
穆元謀捏緊茶盞,若非手勁不足,他幾乎要把那茶盞捏碎了。
那個沒用的東西!什麼混成了伍長,什麼成竹在胸,連偷襲都不會,讓穆連瀟活著回來了!
也不知道他露了底沒有?
要是讓穆連瀟抓到了把柄,那他們定然會層層抽絲剝繭,看穿當年穆連康的失蹤不是意外。
穆元謀重重把茶盞放在桌上,動靜之大,嚇了練氏一跳。
練氏白著臉看他,見他面色不善,猶豫著問了聲:「老爺這是怎麼了?」
穆元謀上下打量了練氏一眼。
失去了棋子的訊息,他等於是斷了一臂,暫時失了嶺東、失了穆連瀟和穆連康的信息。
想要運籌帷幄,最要緊的就是消息的掌握,而現在……
穆元謀覺得不舒服,這種未知的感覺很不舒服。
只是這一切他並不想告訴練氏,以練氏的城府,讓她知道他對前頭的訊息失控了,說不定就自己嚇自己,在吳老太君跟前露餡了。
穆元謀徐徐吐出一口氣來。
以前瞧著還好,一旦遇事,他就對練氏不滿起來。若練氏能更機敏些、更穩重些……
「沒什麼,他們年後回來也一樣。」穆元謀沉聲丟下這句話,站起身來,理了理衣襬,背手往外頭走。
練氏被他丟在裡頭,他又只留下這麼一句輕飄飄的話,叫她瞪大了眼睛。
他們夫妻多年,練氏知道穆元謀的脾性,他剛才的臉色,絕不是「沒什麼」。
明明有事,而且是與長房、與爵位爭奪有關的事情,穆元謀竟然敷衍她,不與她說實話!
思及此處,練氏的心猛地就是一痛。
穆元謀走得快,並沒有察覺到練氏的狀況。
守在外頭的朱嬤嬤見穆元謀出去了,便打了簾子進來伺候練氏。
剛撩開一個角,朱嬤嬤就瞧見練氏捧著心口在大口喘氣,嚇得她白了臉,趕緊上前替練氏又是揉心口又是拍背。
「太太,這是怎麼了?要不要請大夫?」朱嬤嬤嘴上問著,心裡不由得七上八下的。
自打穆連慧嫁人之後,府裡就沒什麼能讓練氏又恨又氣又無處宣洩的事了。
這些日子,練氏喘不過氣的狀況已經好了很多,怎麼突然之間……
定是為了穆元謀,定是為了長房寄回來的信。
練氏緊緊抓著朱嬤嬤的手腕,喘了好一會兒,才脫力的歪在榻子上,就著朱嬤嬤的手喝了水。
這一番喘氣,讓練氏嘴唇發紫、眼角通紅,她好不容易平靜下來,道:「老朱,老爺為什麼不與我說道說道?」
朱嬤嬤哪裡弄得懂穆元謀在想什麼,皺著眉頭,挑了句好話:「老爺定是為了不叫太太擔心,太太這兩年,別的都挺好的,就是總喘不上氣來,老爺也是看在眼裡的,老爺是顧忌著您的身體。」
練氏哼了一聲:「妳別為他說好話了,這是顧忌我?真要顧忌我,我都喘成這樣了,他都能拍拍衣襬就走了?」
「許是老爺沒有注意到。」朱嬤嬤硬著頭皮道。
練氏咬著後槽牙:「他當然注意不到,在他眼裡,我還比不上他衣襬上的一粒灰塵!他就是故意不跟我說道,我不值得他商量了是不是?」
練氏說著說著,胸口的悶氣又泛了上來,心角跟針扎一樣,說不上痛,就是不舒服。
偏偏那不舒服感是在胸腔裡頭,在外頭揉著,跟隔靴搔癢似的,沒什麼大用處。
練氏喘了良久,才又慢慢穩下來:「我這輩子,就是來還債的!慧兒嫁出去,輪到他甩我臉色了。我真是欠了他們這幾個,就沒一個讓我省心。」
朱嬤嬤訕訕笑了笑:「您別這麼說,二爺回來聽見了,多傷心呀。」
「連誠?」提起長子,練氏的臉色總算好看了些,「也就他好一些,他媳婦性子軟,不會給我氣受,不過蔣家那裡,哼!」
「太太。」朱嬤嬤開解道:「到底是沒落的人家,早就不曉得規矩了,虧得二奶奶是在我們府中養大的,您和老太君沒少提點她,把她教養得好好的。」
這話練氏聽得還算順耳,她對蔣玉暖基本還算滿意的。
「沒辦法,還指望著他們給我養老呢。」練氏哼笑,「這回連誠回來,我也沒別的念想,趕緊給我添個孫兒要緊。那邊一個延哥兒、一個洄哥兒,聽起來就鬧心。」
朱嬤嬤又勸了幾句,珠姍進來,笑盈盈道:「太太,前頭剛剛傳了話來,說是二爺回府了。」
練氏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來,心也不疼了,氣也不喘了,道:「老朱啊,給我重新梳個頭,別這麼亂糟糟的,讓連誠看出我身子不好,他好不容易才回來,我可不能叫他擔心了。」
朱嬤嬤見練氏來了精神,趕緊應聲:「太太,奴婢扶您去內室裡。」
練氏梳了頭,對著鏡子照了照,又抹了些胭脂掩蓋蒼白的臉色,這才滿意了,坐在次間裡等著。
西洋鐘挪了一刻又一刻,等了半個多時辰,穆連誠也沒有來。
練氏與珠姍道:「去問問,連誠是不是先回尚欣院了?」
珠姍去問了,回來稟道:「太太,爺沒有回後院,還在前頭,似乎是在老爺書房裡說話。」
練氏木然的眨了眨眼睛。
又等了半個時辰,穆連誠才過來,他身上整齊乾淨,看來是梳洗過的。
練氏明白,穆連誠定是在前頭梳洗,不然,風塵僕僕的,他可進不了穆元謀的書房,走不到他老子跟前。
「瘦了。」練氏仔細看了看兒子,心疼起來。
穆連誠皺眉道:「母親看起來精神不佳,是不是身子不舒服?」
練氏聽了這話,心裡暖得一塌糊塗。
丈夫、女兒,都不及長子貼心,竟然一眼就瞧出來她身體不好。
「沒有的事,母親一切如常。」練氏笑了起來,「連誠啊,你在前頭和你父親說了些什麼?」
穆連誠眸色一沉,穆元謀吩咐過他,有些事情不用跟練氏講,免得女人家心思重,叫人看出來。
「說了些北疆的事情。」穆連誠道。
練氏衝口道:「他就沒跟你說連瀟和連康的事?」
穆連誠一時沉默。
練氏才舒服了一小會兒的心口又猛地一陣痛。
她還當長子是個好的,原來到頭來,一樣會瞞著她,一樣不肯跟她說實話。
失望從眸中一閃而過,練氏臉上依舊掛著笑,道:「聽說了嗎?」
穆連誠斟酌著答道:「聽說他們回程耽擱了。」
只有這麼一句,再往深的就沒有了。
練氏再也難以掩飾失望之情,長長嘆了一口氣:「行了,你先去給老太君請安吧,我有些乏,歇一會兒。」
穆連誠以為練氏是身體不舒服,又怕她再追問,便順著練氏的意思,關心了幾句,退出去了。
等人一走,練氏歪倒在榻子上,心裡沉甸甸的。
既然他們父子都瞞著她,那就瞞著吧,回頭出了什麼差池,也不用怪她。
◎
臘月過半,各家都忙著準備過年,穆連瀟他們還在官道上趕路。
雖然沒有叫大雪擋了行程,但道路濕滑,行得並不快。
除夕夜時,宿在了沿途一座小城的驛館裡。
外頭鞭炮熱鬧,莊珂笑著與杜雲蘿道:「原來關內過年是這個樣子的呀。」
杜雲蘿亦笑了:「上元前的每一天,都很熱鬧。上元那日更是,街上全是各式各樣的花燈,好看極了,可惜我們不能在上元前抵京,若不然,大嫂還能看一看花燈。」
莊珂見她說得興致勃勃,湊過來低聲問她:「三叔帶妳去看過燈?」
杜雲蘿眸子一轉,倒也沒否認,反而是把前年上元的事情仔仔細細講了。
他們觀燈遇見了葉毓之,葉毓之聽從穆連瀟的建議遠赴山峪關,最終也是葉毓之在沙漠裡遇見了穆連康。
都說過年穿新衣,他們在路途中就沒那麼講究了,而延哥兒和洄哥兒還不到對壓歲錢歡喜的年紀,被那震耳欲聾的鞭炮聲嚇得大哭。為此,兩家人便不在城中多休息幾日了,繼續往桐城趕。
馬車駛入桐城時,已經是正月二十二了。
因著有穆連康一家在,便沒有去甄家打擾,只尋了驛館住下。
安頓好了,杜雲蘿才往甄家遞了帖子。
陳氏和王氏在二門上迎他們。
筵喜堂裡,侯老太太翹首盼著,見杜雲蘿抱著延哥兒走進來,趕忙道:「好孩子,快到外祖母這裡來。」
杜雲蘿上前幾步,先把延哥兒放下,跪下給侯老太太磕了頭。
侯老太太熱淚盈眶:「曉得妳跟著去了嶺東,我這心就一直擔著,如今好了,總算是回來了。妳母親也真是的,妳都回來了,也不知道提前來跟我說一聲。」
杜雲蘿搖著頭笑了:「我們從嶺東過來,還未到京城呢。」
王氏噗哧笑了:「老太太,您看,雲蘿這是惦記著您,先來看您了。」
侯老太太哈哈大笑,又道:「雲蘿,妳外祖父聽曲兒去了,等他回來,一定高興。」
杜雲蘿驚喜道:「外祖父能出門聽曲了?」
「是啊。」陳氏堆著笑,道:「能坐著轎子出門,就能去聽曲了,老爺陪著去的,就在前街的戲樓裡包了個雅間,搭個軟榻,老太爺要是累了,就能躺著聽。」
杜雲蘿由衷歡喜。
上了年紀的人,尤其是大病之後,最怕沒有念想,對什麼都失去興趣了,那人生就不長了。
像甄老太爺這樣,還記得聽曲兒,想著遛鳥兒,那肯定是一日比一日好的。
「外祖母。」杜雲蘿見王氏抱著延哥兒逗趣去了,便與侯老太太說了要緊事,「我婆家的大伯,之前不是失蹤了九年嗎?這一回尋到了,跟著我們從嶺東回京。只是以前的事情他一點兒也不記得了,我想讓邢御醫給他瞧瞧。」
在杜雲蘿要嫁給穆連瀟時,侯老太太就打聽了定遠侯府的事了,驚訝道:「尋回來了?這還真是天無絕人之路。讓邢御醫好好給他診斷診斷,妳還跟外祖母客氣什麼。」
「世子的身子也要讓他看看。」杜雲蘿曉得等下穆連瀟來請安時,背上的傷一定會被侯老太太看出來,乾脆也不隱瞞,直接說了,「在嶺東受了傷,沒有全好。」
正說著話,甄文謙和甄文淵陪著穆連瀟過來。
穆連瀟給侯老太太行了禮,說了不少北疆和嶺東的風土人情給侯老太太添樂子。
等甄老太爺回來,杜雲蘿把延哥兒抱到他跟前,道:「外祖父,這是我們延哥兒。」
甄老太爺丟開了拐杖,伸手想接延哥兒過去,又怕自己手上突然勁頭不夠。
杜雲蘿看在眼中,讓延哥兒坐在甄老太爺腿上,自個兒又扶著些。
延哥兒不怕生,見誰都是咧著嘴大笑,甄老太爺樂壞了。
杜雲蘿陪著穆連瀟去尋邢御醫。
邢御醫在教寧哥兒認字。在甄家生活舒心,寧哥兒圓潤了許多,看起來憨憨的,很是招人喜歡。
見穆連瀟來尋他,邢御醫把寧哥兒打發去了院子裡耍玩。
看了眼穆連瀟,邢御醫皺眉道:「你的背怎麼彎了?剛當了爹,就要跟老頭子比著當祖父了?」
穆連瀟在一旁的椅子上坐下,道:「來尋邢御醫,就是想讓御醫看看我的背傷。被人從背後砍了一刀,又迷失在大漠裡,耽誤了治療,後來讓軍醫包紮調養了,身上其餘傷處沒有什麼不適,唯有背,我總挺不直。」
邢御醫見屋裡也算暖和,就讓穆連瀟脫了上衣。
穆連瀟的背後有一道斜長的傷痕,雖然已經癒合了,但邢御醫看得出來,當時這傷口很深,足可見骨。
「當時耽誤了醫治?」邢御醫的眉頭皺緊了。
穆連瀟頷首。
杜雲蘿想了想,補充道:「在大漠裡尋到世子的親隨簡單替他包紮過,只是大漠裡全是黃沙,不少沙土染了傷口,後來回到關內,又掰開傷口重新清洗。」
這幾句話,光從嘴裡說出來,杜雲蘿就心驚膽顫,兩條腿發痠了。
邢御醫又具體問了受傷的經過和細節,道:「你們心太急了!」
杜雲蘿和穆連瀟交換了個眼神。
「傷筋動骨一百天,你們把這當成是大夫瞎說的嗎?」邢御醫哼道:「受傷後,還跟韃子打了一架拚了個你死我活,又被馬馱著走了幾天,沒把你顛散架就不錯了。第二次處置傷口,你只等到皮肉癒合就迫不及待的返京,可裡頭的筋骨還傷著呢。好在沒稀裡糊塗的想硬把背挺起來,不然一輩子都別想站直了。哎,我知道你們這些當將士的,邊關戰事急,沒有時間給傷患慢慢休養。治傷也是,死不了人就行,人手跟不上的時候,還有放棄不救的。」
說起邊關軍醫們的生活,邢御醫侃侃而談,頗有一番見識,說到了最後,就是一句話,戰事已了,穆連瀟為何非要心急火燎的回京來,多養些日子也不至於如此。
穆連瀟苦笑,提到了穆連康:「還要請邢御醫替我大哥看診,他能想起以前的事情嗎?」
「大哥?」邢御醫瞪大了眼睛,待反應過來那是失蹤了九年的穆連康,他嘖了一聲,睨了杜雲蘿一眼,「深宅大院就是是非多。」
杜雲蘿明白邢御醫指的是她曾被下過藥的事情,苦笑不語。
穆連瀟看在眼中,按捺著沒有追問。
依邢御醫的意思,穆連瀟在背上的筋骨完全癒合前,應當以休養為主,能躺著就千萬別站著。
「我再教你一些舒展筋骨的法子,記得,一定要等背上不痛了,再來練。」邢御醫仔細叮囑著,「要不然,成了個羅鍋,再想直起來就難了。」
有這句話在,杜雲蘿懸著的心也算是落下了。
邢御醫從不說大話,他說能休養好,就一定能養回來。
在甄家用過了晚飯,穆連瀟和杜雲蘿才帶著延哥兒回了驛館。
翌日一早,穆連瀟和穆連康要上青連寺,邢御醫照著昨日說好的,一早就過來了。
邢御醫對使用輪椅非常熟練,遇見門檻時,只要有人搭好了木板,他無須借力其他人,可以在宅子裡來去自如。
穆連康和邢御醫見了禮。
邢御醫仔細回想了一番,嘆道:「看起來和小時候還挺像的。」
穆連康笑了。
莊珂聽聞御醫來了,把孩子們交給了洪金誠家的,自個兒過來看狀況。
邢御醫聽見腳步聲,轉頭看去,見那年輕婦人推門進來,背著光,隱隱約約看清了莊珂的樣子,一時愣住了。
穆連康把邢御醫的反應看在眼中,道:「大人,這是內子。」
莊珂給邢御醫見禮。
等迎著光,邢御醫看清楚了莊珂的眼睛,碧色如湖水,他恍然道:「這是有胡人血統?」
莊珂頷首,解釋道:「我的母親是胡人,父親是漢人。」
邢御醫緩緩點頭:「看著有那麼一點點眼熟。」
只是有一點兒眼熟,具體像誰,又是在哪裡見過,邢御醫已經想不起來了,即便知道莊珂姓莊,他也沒有半點兒印象了。
唯一知道的,是莊珂的五官與邢御醫曾經見過的一人有些相似。
那人是男是女,多大年紀,邢御醫苦思冥想也沒有結果。
莊珂自個兒並不在意,比起父親的身分,她更想知道,穆連康的記憶能不能尋回來。
邢御醫讓穆連康散了髮髻,雙手插入他的長髮之中,一點一點按壓腦杓。
他查得仔細,沒有放過一寸一毫。
等查完了,邢御醫道:「就算以前腦袋受過傷,現在也已經好了。記憶是很奇怪的東西,它就在腦子裡,但是想不起來的時候,你拿腦門子撞牆,也想不起來。就像這位娘子,我分明是見過與她容貌相近之人,但我回憶不起來。大公子能不能想起,很難說。也許一輩子不能,也許明日裡就突然明白了。強求不得。」
莊珂頗為遺憾,穆連康反過頭去安慰她:「記不起來也無妨,比起從前我連自己是誰都不知道的時候,好歹現在的我,有家可歸。」
穆連瀟向邢御醫道謝,讓九溪送邢御醫回甄家。
曉得他們兄弟要上青連寺,邢御醫睨了杜雲蘿一眼,見杜雲蘿對他頷首,邢御醫喚住了穆連瀟。
「那位空明師父,他不是啞巴,他沒有啞。」邢御醫道。
穆連瀟愣怔。他還未拜託邢御醫給穆堂診斷,為何邢御醫已經知道了?
穆連瀟看向杜雲蘿,杜雲蘿淺淺笑了笑。
因著穆連瀟的背傷,他們兄弟坐馬車上山。
抵達青連寺時,穆連瀟帶著穆連康去了後山竹林。
林子深處,穆堂苦行的屋子比前回來時更加破爛,這些年,穆堂似乎無心修繕,由著這屋子越來越破。苦行僧,他是一個真正的苦行僧了,勞筋骨、餓體膚。
穆堂站在屋前,雙手合十,他背對著穆連康和穆連瀟,彼此都看不到對方的神色。
「穆堂。」穆連瀟喚他。
穆堂沒有動。
穆連康看了穆連瀟一眼,喚道:「穆堂。」
聲音如一把尖刀,一下子撕裂了穆堂的神經,他的身子一怔,僵硬著轉過身來。
已經九年,就算穆連康的聲音與九年前有了不少變化,但穆堂還是聽出來了,他瞪大眼睛看著穆連康。
「我想知道來龍去脈。」穆連康說道。
穆連瀟靜靜盯著穆堂的反應,最初的驚訝過後,他在穆堂眼中讀到的不是惶恐,而是慶幸,彷彿穆連康活著站在穆堂的前面,對穆堂來說,是一件盼了又盼的事情。
穆堂只是用這樣的眼神看著穆連康,卻沒有說一個字。
穆連瀟沉聲道:「我知道你沒有啞,這幾年間,我問過你許多次,你都不肯開口,現在大哥已經回來了,你也不說嗎?」
穆堂嘴唇囁囁,眼角的紋路被淚水浸濕,他還是搖了搖頭。
「你在怕什麼?」穆連瀟問道。
穆堂這一次出聲了,給他們一句「阿彌陀佛」,他常年不曾開口,突然說話,語調奇怪,咬字模糊,若不是這句佛號簡單,穆連康和穆連瀟都聽不懂穆堂在說什麼。
穆連瀟暗暗鬆了一口氣,能有一句佛號,已經是往前邁了一大步了。
之前在穆堂「啞」後,這幾年裡,他就沒聽過穆堂說一個字。
他看得出來,穆堂有所動搖,起碼在看到穆連康的那一刻,穆堂動搖了。
「我們從嶺東回來……」穆連瀟仔仔細細說起了他和穆連康重逢的經過,說山峪關,說韃子,說古梅里。
穆堂眼中的淚水越積越多,最後重重砸下,無聲痛哭。
他抹了一把眼淚,抬起頭來深深吸了一口氣,哆哆嗦嗦道:「韃子大敗了嗎?」
穆堂說了三遍,穆連瀟才聽懂,頷首道:「大敗了。」
「爵位是誰的?」穆堂又問。
穆連瀟道:「我有妻有兒,也有戰功,足以承爵。」
「世子,你能勝過他嗎?」
他?穆堂沒有點名,但穆連瀟已經明白,他指的是穆元謀。
穆堂會這麼說,當年穆連康失蹤的元凶已然浮出水面,但穆連瀟想知道得更多,他想聽穆堂把所有事情原原本本說出來。
穆連瀟攥緊了垂在身側的手,道:「二叔父嗎?我必須勝過。」
穆連康微怔。
穆堂垂著頭一言不發。良久,他道:「世子,其實你已經懂了,不是嗎?」
話說到了這裡,穆堂沒有繼續隱瞞,他已經沒有隱瞞的必要了。
當年,穆元謀讓穆堂在從北疆回京的路上殺了穆連康。
穆堂並不願意,他父母雙亡,又無妻兒,了無牽掛,原本是可以誓死不從的,可看著迎靈回京的隨從們,穆堂明白了。
穆元謀說什麼都不會讓穆連康進入京城的,不是他穆堂動手,也會有其他人。
穆堂沒有帶著穆連康和穆連瀟單獨回到京城的信心,也無法那樣做。
一旦那樣行事,後果可以預見。
穆元銘斷七之夜,穆堂敲暈了穆連康,把他遠遠帶離了營地,扔在雪地裡,潛意識裡,他還是盼著穆連康能夠活下來,活下來,躲開穆元謀的毒手。
事情他做了,內心煎熬卻無法躲過,回京的這一路,穆堂飽受折磨,他唯一的念想就是給吳老太君和徐氏磕最後一個頭,然後以死謝罪。
京城漫天白紙,多少人都知道去迎靈的穆連康失蹤了。
穆堂欲自盡時被青連寺的住持大師勸下,住持說,贖罪不是只有自殺一條路。
醍醐灌頂。穆堂跟著住持大師回了青連寺,出家為僧,法號空明。
「我一直在等,等到可以說的這一天。」穆堂的聲音顫得厲害,一字一字都像是用盡了全身的力氣,「我想過,也許一輩子都等不到,世子,若你一事無成,我老死在青連寺,都不會說出真相。」
穆連瀟抿住雙唇,他突然意識到,穆堂想告訴他的,遠比他以為的會更多,也更讓他吃驚。
在說了穆連康失蹤的真相之後,穆堂還能再說些什麼?
穆連瀟倒吸了一口涼氣。
穆堂上前幾步,目光在穆連康和穆連瀟的臉上來回掃過,最後死死盯著穆連瀟的眼睛:「老侯爺、大老爺、三老爺是戰死,也不是戰死。」
晴空霹靂一樣的話,在穆連康和穆連瀟的腦海裡炸開了。
風毓院裡,穆元謀和練氏一道用了午飯。
自打穆連慧嫁出去之後,練氏總算不會時不時被氣得胸口疼了,只是看著空空的東跨院,心裡就牽掛。這就是討債鬼,在眼前時她氣得厲害,見不到了又放不下。
練氏只好把心思擺在了等穆連誠回來上。眼瞅著入了臘月了,總歸就是這幾天。
董嬤嬤打了簾子進來,練氏抬頭問她:「老董,是不是連誠回來了?」
「老爺、太太。」董嬤嬤垂手道:「是世子送了信回來,說是啟程時耽擱了,要年後抵京。」
穆元謀放下手中茶盞,抿唇道:「是連瀟寫的?」
董嬤嬤縮了縮脖子:「奴婢是聽柏節堂裡的人說的,老太君...
目錄
第一章 真相大白
第二章 落葉歸根
第三章 宮裡認親
第四章 善意提醒
第五章 平陽侯府
第六章 牽起紅線
第七章 雙喜臨門
第八章 隔牆有耳
第九章 瓶兒出嫁
第十章 再添一子
第一章 真相大白
第二章 落葉歸根
第三章 宮裡認親
第四章 善意提醒
第五章 平陽侯府
第六章 牽起紅線
第七章 雙喜臨門
第八章 隔牆有耳
第九章 瓶兒出嫁
第十章 再添一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