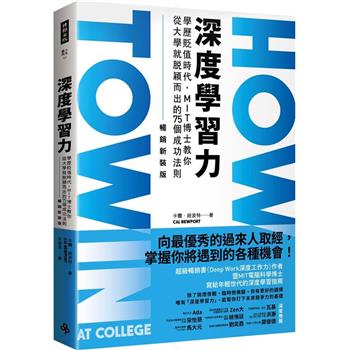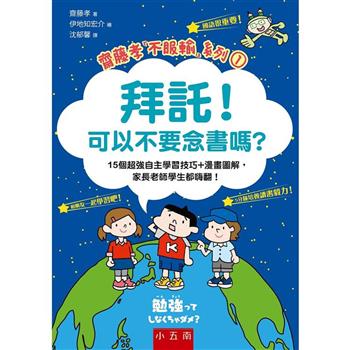杜雲蘿在花開一般的年紀守寡,得了貞節牌坊一座,年老之時,才知征戰沙場的丈夫之死竟是一場陰謀,她想要報仇,仇人卻早已故去,無仇可報。
牌坊倒塌,她的意識消散、呼吸漸淺,心中念的卻還是她的摯愛,若是能再重來,她絕不讓丈夫枉死、絕不讓仇人善終!
──於是,她回來了。
睜開眼的時候仍是雲蘿花開的三月,人事卻回到了與定遠侯世子穆連瀟議親的那年。這一次,她要滿心歡喜的待嫁,再也不讓心機叵測之人害了杜家、害了定遠侯府。
她深愛一生卻有緣無份的丈夫,終於……又回到她的身邊了。
本套書包含:
卷一 杜家嬌女
卷二 我心悅汝
卷三 新婚燕爾
卷四 邊關歲月
卷五 雲蘿花開
卷六 善始善終(完)
本書特色
宅門內部的血緣鬥爭,世家之間的利益糾葛,與兒女情長的愛恨纏綿,
起點女頻言情天后[玖拾陸],最細膩動人的重生之作!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善終 套書【1-6卷】(完)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善終 套書【1-6卷】(完)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玖拾陸
死宅一名,愛烤肉愛火鍋,愛筆下的各種角色。
擅長古言,愛女主,也愛各款女配,相信不管什麼出身、什麼性格的「女配」,都有追求自己理想和幸福的機會,為此,96一直在努力。
在《善終》之後,古言破案的《棠錦》也要結束了,近期在構思一個全新的故事,書名很可愛,叫《威武不能娶》,一樣是甜寵文,希望能比《善終》更甜三分,也希望有機會能讓大家看到這兩本書。
再次感謝打開這本書的你。
繪者簡介
胖九
大家好,我是胖九,一個平日愛好吃肉、睡覺、逗貓的宅女。比較迷糊,反應慢半拍,記憶力差,常被朋友稱為「金魚腦袋」。歡迎各位編輯大人來約稿~喜歡我作品的朋友們也請來找我聊天吧~微博@胖九愛吃肉。
玖拾陸
死宅一名,愛烤肉愛火鍋,愛筆下的各種角色。
擅長古言,愛女主,也愛各款女配,相信不管什麼出身、什麼性格的「女配」,都有追求自己理想和幸福的機會,為此,96一直在努力。
在《善終》之後,古言破案的《棠錦》也要結束了,近期在構思一個全新的故事,書名很可愛,叫《威武不能娶》,一樣是甜寵文,希望能比《善終》更甜三分,也希望有機會能讓大家看到這兩本書。
再次感謝打開這本書的你。
繪者簡介
胖九
大家好,我是胖九,一個平日愛好吃肉、睡覺、逗貓的宅女。比較迷糊,反應慢半拍,記憶力差,常被朋友稱為「金魚腦袋」。歡迎各位編輯大人來約稿~喜歡我作品的朋友們也請來找我聊天吧~微博@胖九愛吃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