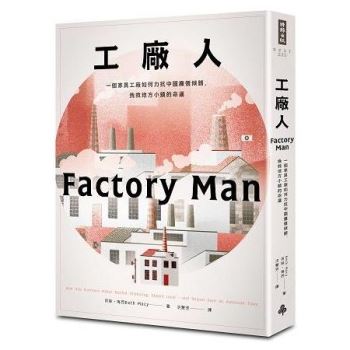一個無根的嬰孩,兩個藏事的太監,四個爭寵的皇子。
大奕皇宮內,不為人知的情緣秘事,幕起了──
大奕皇宮內,不為人知的情緣秘事,幕起了──
小小的小麟子走路還會歪著呢,已經當起了御膳房的小小太監。她有兩個太監爸爸,白臉黑臉,自幼為她把屎把尿,在禁祕的皇宮內帶大了她,對她都是極好的。
見過的人雖少,養成了不擅說話的性子,卻是相當親和又討喜。原本是輪不著她親近皇子身邊的,也不知怎的就入了四皇子楚鄒的眼,當起了他專屬的點膳小太監。
她明明不該接近被厭離冷落的四皇子,卻因他總是把自己做的膳食一口不剩地吃完,覺得自己的手藝終於有人捧場,便更加賣力地為著她的主子爺變換菜樣,日日不落。
她不知自己的存在本須斂藏,直到有一天,她莫名成了皇子們爭執的原因,太子之位的風暴,正悄悄地向她襲來……
本書特色
原以為是牆頭不起眼的雜草,卻在風雨飄搖中堅韌地長成了明豔的花朵──
且看無父無母的女扮男裝小太監如何成為將來足立東宮的太子妃!
晉江名家[玉胡蘆]細細述說紫禁城內的宮闈秘事,文辭細膩,讀來令人如歷其境、如聞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