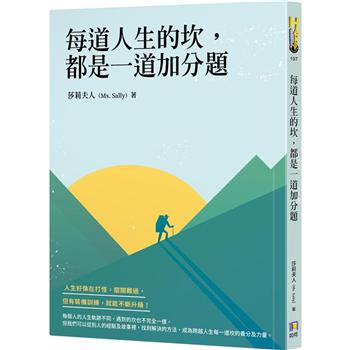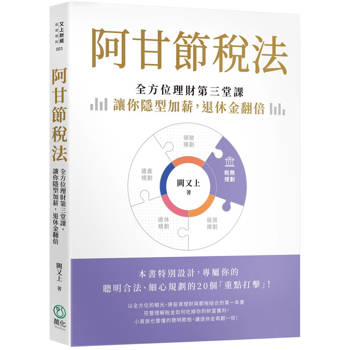義律進入商館後發現各國商人沒有被抓被殺之虞,包圍商館的清軍封堵了所有路口,但號令嚴明,不闖入樓內、不損壞器物,不拘捕、不打罵、不傷害任何人,僅將夷商軟禁在樓內。武力營救人質似乎成了多餘之舉,義律反而惴惴不安起來。
他曾給佈雷克艦長下過命令,若六天內得不到消息,可以採用適當方式前來營救。在扶胥碼頭巡視時又曾授意「忠勇號」船長馬奎斯組織各船水艄,一俟清軍大開殺戒就以武力抵抗,衝破攔阻,營救商館裡的同胞。
可現在看來,事情顯然並沒有壞到那種地步。萬一佈雷克艦長和馬奎斯船長因為消息不明,採取極端行動,整個局面就會失控,各國商人和水艄就可能因一場意外的衝突大量傷亡,他無論如何都承擔不起這麼重大的責任!
斷水斷糧斷蔬菜比鈍刀割肉還教人難受。商館裡沒有水井,廚房裡沒有存貨,肉蛋菜蔬僅夠食用兩天,夷商們很快陷入缺水缺食的窘境。商館與珠江僅有一箭之遙,但清軍弁兵橫槍挎刀封鎖了江岸。就算讓他們取水,江水也不宜飲用,因為江面上船舶如梭,到處漂浮著穢物垃圾和死貓死狗。
到了第三天,商館裡的所有水缸水櫃一清見底,人們像陷入沙漠一樣嘴乾口澀,焦渴難耐,夷商們心旌動搖,一致要求義律拿出應急的辦法。
義律、參孫和馬儒翰在小會議室裡商議如何應對這場突發的危機。義律灰藍色的眼睛飽含著陰鬱和不安,肩上的擔子沉重無比,幾乎要把他壓垮。
馬儒翰舔了舔乾澀的嘴唇,「欽差大臣是個冷酷無情、意志如鐵的人,不繳鴉片,他是不會善罷甘休的。」
參孫的嗓子同樣乾得要冒煙,「清軍把我們圍得鐵桶一般,任何消息都無法傳遞出去,我擔心萬一佈雷克艦長冒險闖入虎門,馬奎斯船長率眾呼應,就事大難收了。」
義律道:「是的。我曾經多次警告我們的同胞,在中國做鴉片生意如同火中取栗,但是,他們被貪慾矇蔽了雙眼。這場危機既意外,又在意料之中,只是沒想到來得如此猛烈。欽差大臣行事魯莽,竟然把《大清律》的連坐法應用於世界各國,讓無辜的商人和水艄也遭到軟禁。商館和扶胥碼頭有一千五六百外國人,多數是我國人和英屬印度人,這種舉動會引起各國政府的抗議和干涉,甚至讓禁煙論的同情者們眾叛親離。」
參孫歎,「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眼下我們只好忍受屈辱,勸說那些愛錢如命的商人繳出鴉片,好化解這場危機。」
馬儒翰皺眉,「有些人寧願捨命也不願捨財,躉船上的鴉片畢竟數量龐大,價值連城。」
義律思索片刻,「我們只好鋌而走險,用商務監督署的名義收繳所有鴉片,統一交給欽差大臣。」
參孫有點兒猶豫,「商務監督署是政府的辦事機關,商人們會索要收據和補償的。」
「給他們開收據,承諾我國政府將在適當時間以適當方式給予補償!」
這是項驚人的決定,大大超出參孫預料,他提醒道:「義律先生,我國政府不會用納稅人的錢補償在華僑商的損失,沒有這種先例,何況鴉片貿易在我國,也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
義律的臉色陰沉,「我只能當機立斷,當生命和財產不能兩全時,以生命為先。我擔心再過兩天,佈雷克艦長和馬奎斯船長耐不住性子,把天捅個大窟窿!我們必須想方設法通知他們,防止事態惡化。」
馬儒翰思索著,「只有承諾繳煙,才能恢復與外界的聯繫,否則,一張紙條都送不出去。」
義律吩咐:「馬儒翰先生,你寫一份通知,貼在商館的公告欄上,告訴全體在華英國臣民,商務監督署承諾在合適的時候以適當的方式由政府給予補償。明天早晨六點前,他們必須如數呈報擬上繳的鴉片,不肯繳煙的臣民,後果自負。」
馬儒翰有些擔憂,「義律先生,政府要是拒絕補償,你就騎虎難下了,會受到嚴厲的處分!」
參孫也勸道:「義律先生,你的決定事關重大,可能把政府拖入一場不期而至的戰爭,能不能換種辦法?」
義律緊蹙眉頭,「中國欽差大臣用暴力剝奪我國臣民的財產,威脅我國臣民的生命,我不得不向政府提議通過戰爭索賠。戰爭的法則是,誰戰敗誰賠款!」
參孫大為震驚,「義律先生,請你再仔細考慮一下。戰爭不是小孩子玩打仗遊戲,它比地震、風災、山崩海嘯還可怕,它的後果是災難性的!傷殘死亡,商業中止,還有人力、物力、財力的巨大消耗。中國是世界第一大國,與我國相隔一萬七千英里,軍隊的調動、後勤的保障、戰費的籌措、國際形勢、國內輿論等等,都得通盤考慮,稍有差池,就可能引發災難般的後果。」
義律把佩劍往桌上砰地一放,「我當然明白這種決定如同賭博!但我身為領事,在危機時刻有機斷之權。我將向外交大臣巴麥尊勛爵提議,對中國進行報復性打擊!我的決定可能有兩種後果,要麼以戰爭驚動世界,要麼以舉措不當被撤職查辦。」
參孫問:「如何處理甘結問題?」
義律道:「欽差大臣的《各國商人呈繳煙土諭》措辭粗糙寬泛。所謂『一經查出,貨即沒官,人即正法』,不具有法律的明晰性─什麼人,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什麼情況下,用什麼方式攜帶多少鴉片。有什麼人證、物證等等,都不規定,只是籠統地說『一經查出,人即正法』。萬一有人心懷孬意栽贓陷害,甚至不給當事人辯護的機會,就會有人被誤殺和冤殺。這一條與我們的法律背道而馳,不可接受。」
馬儒翰提醒道:「我們要是拒簽甘結,廣東官憲會停止與我國商人的貿易。」
義律道:「我將與十三行總商仔細討論甘結問題,要求他們作出修改。眼下先辦急事,用商務監督署的名義公告全體僑商,把準備上繳的鴉片如實上報,並交出原始發票。」
公告貼出後,所有商館立即燈火通明、人聲鼎沸,各國商人徹夜不眠,經過激烈的辯論後終於集體屈從。第二天早晨六點前,全體商人呈報了兩萬零三十七箱鴉片,其中查頓—馬地臣商行七千箱,顛地商行一千七百箱。幾家美國商行搭便車,請英國商人代繳一千五百餘箱。按照發票計價,貨值高達六百萬元!
伍紹榮與盧文蔚被關在南海縣大獄裡。他們是赫赫有名的官商,牢頭獄霸不敢欺負,南海知縣劉師陸與他們私交甚好,讓他們住在雅號裡。雅號是縣大獄裡的上等號間,光線好,清掃得乾淨,連鋪草都是新的,伙食單開,晚飯還加一壺水酒,只是沒有人身自由。
伍、盧兩家是姻親,盧文蔚和伍紹榮是舅甥關係,但在十三行做事仍用「某爺」互稱。二人百無聊賴,並排坐在草鋪上,有一搭沒一搭地閒扯。
「盧二爺,你卦打得準不準?」
「準。」說著,盧文蔚用鋪草打了一卦,恰好打中九五坎卦。卦辭是:坎不盈,祇既平,無咎。這是有驚無險之卦。
伍紹榮心裡稍微踏實,又疑惑道:「你說咱們犯了什麼罪?」
「勉強算是辦差不力之罪,未能說服夷商繳煙之罪。」
「這算罪嗎?」
盧文蔚無奈道:「上憲說你有罪你就有罪,無罪也有罪。上憲說你沒罪你就沒罪,有罪也沒罪。」
伍紹榮用手指撚著一根鋪草,「夷商不遵從林欽差的命令,他就把板子打在我們身上,這能怨我們嗎?我爹曾經說過,寧做一條狗,不做行商首。我當時不明白,後來才明白。嘉慶二十三年—那年我才六歲,是聽我爹說的—一條英國商船進口貿易,把四箱鴉片藏在夾板艙裡。我爹是那條船的保商,那條船在虎門緝查口矇混過關,在扶胥碼頭被稅丁查住。結果,我爹被罰十六萬,杖八十,全體行商連坐。
「道光元年,同泰行承保的夷船私帶鴉片,他們沒查出來,出具保結,被海關稅丁查出,罰款五十倍,所有行商連坐,結果同泰行破產。就為那事,皇上一道諭旨頒下,處分我爹,摘了他的三品頂戴。
「這種殃及身家性命的事,我們唯恐避之不及,哪敢冒顛躓的風險賺黑錢?林欽差卻無端懷疑我們查私縱私。說句良心話,我們上夷船查鴉片,明面上是宣諭,實際上是懇求,懇求夷商不要挾帶違禁之物,否則會殃及我們的身家性命。」
伍紹榮講得悲心喪氣,「哎,我爹不願當總商,我也不願,但商籍就像一塊狗皮膏藥牢牢黏在我的身上,揭不掉,扯不去,撕不爛,擺不脫。我想通過科舉步入仕途,但皇上飭令我家後代必須當行商,沒辦法,我只好像磨道裡的毛驢,不僅勞心勞力,還得隨時準備承受上憲的斥責和杖打。我是八字不照的苦命人,還當了倒楣的總商。苦啊—苦—!」他拍著胸脯發著牢騷叫著苦,彷彿要把一腔塊壘吐出去。
盧文蔚也跟著訴起苦來,「我爹盧觀恒也一樣。他是苦出身,四十歲才發家,創辦了廣利行,盛極一時,當了總商。他老人家年輕時最崇拜入祀鄉賢祠的人,因為祠堂裡有牌位的,都是品學兼優、德行高尚的鄉梓名人,每年春秋由地方官主持祭禮。
「我爹在世時,辦義學、贈義田、修路橋、賑災民,累計捐資七八十萬,可謂有功於桑梓,就是夢寐求著死後能在鄉賢祠有個牌位。他去世後,我們給廣東巡撫衙門寫了稟帖,請求在新會縣鄉賢祠為他老人家立個牌位,還花不少錢上下疏通。沒想到鄉民們不幹,煽動與我爹有舊怨的人到巡撫衙門告刁狀,說我家籍隸商戶,我爹不學詩、不知禮,不是孔孟之徒,不配入祀鄉賢祠,鬧得沸沸揚揚,最後竟然驚動了朝廷。嘉慶皇帝御筆親批,不准我爹入祀鄉賢祠 。
「咱們籍隸商戶,就是這麼受人擠對。依我看,林欽差是在給你小鞋穿,他召見行商時,你跟他爭禮儀,能爭嗎?別看咱們捐了五品頂戴,人家說你是商不是士,你還不得乖乖跪下。」
伍紹榮從草鋪拽出一根乾草葉,一面揉搓一面說:「可咱們畢竟是有官銜的人,披著官商兩張皮,代朝廷經理天子南庫。」
盧文蔚繼續嘮叨:「作為商,兄弟子侄們眼巴巴地盼著你賺大錢分紅利,賺錢了,皆大歡喜,要是賠錢了,三親六戚合夥罵你無良無德、無才無能,甚至懷疑你私吞銀子。作為官,民人雜役對你恭敬有加,但在官場上,你依然是不入流的角色。天子南庫不是好料理的,一出紕漏,所有板子都打在你身上,打得你皮開肉綻,但除了老婆、孩子,誰說句心痛話?
「就說鴉片,咱們明知夷商經營鴉片,但他們油滑得像泥鰍,偏不進口,只在國門口販賣。你有什麼辦法?驅趕,沒進你家地盤;不驅趕,眼睜睜地看著白銀外流。內務府要銀子,粵海關要稅賦,總督衙門和巡撫衙門要分成,行商們要賺錢,夷商們也要賺錢,還有廣州城的幾十萬丁口,全靠越洋貿易謀求生業。十三行幹的是吞刀吐火的生意,搞不好,就會自殘。
「當年你爹和我哥哥當總商,外人以為是天大的榮寵,卻不知曉多麼辛苦、多麼操勞。那種辛苦和操勞不是身乏,是心累,累得精神緊張,睡不著覺,就怕出紕漏被責打。我哥哥一心想辭去總商,卻辭不掉,只好以病求退,連哄帶勸把我推到檯面上。你爹花大把銀子想卸去總商,要不是你們兄弟二人接手,他還不照樣像磨道裡的毛驢一樣辛辛苦苦地轉悠。」
伍紹榮歎了口氣,「舊事不提了,提起來就傷心。眼下我擔心的是封港封艙,我們怡和行有五千傭工,勞薪耗損,人吃馬嚼的,封一天就得損失幾千兩銀子。」
盧文蔚也揪出一根鋪草在手指間揉搓,「我擔心的是商欠。我家的商欠有三十多萬,要是林欽差知道了,後果不可預料。要不是你們家替我家兜著,我們盧家早就像當年的麗泉行一樣流徙新疆了。」
伍紹榮咬牙切齒道:「我接替總商六年了,外表上看是榮華富貴,內心裡全是屈辱和怨毒。我真恨,恨不能請三百個道士念七七四十九天毒咒,把這商籍咒掉,恨不能請他們念九九八十一天毒咒,詛咒上憲天誅地滅!」
雖然沒點名,但盧文蔚知道他話中「上憲」指的是誰,忙小心翼翼把食指放在唇口,「噓!小點兒聲,隔牆有耳!」
伍紹榮霍然警醒,意識到牢房不是講私密話的地方,這才忐忑不安地環視四壁,彷彿有小鬼在隔牆偷聽。
恰巧這時,大門的鐵鍊猛地嘩啦啦一陣碎響,伍、盧二人心頭一悸,不由得一起朝甬道盡頭定睛細看,是牢頭用鑰匙開門。接著,敞亮處出現了一個熟悉的身影,是梁廷枏!
梁廷枏胸前掛著一柄放大鏡,背著雙手,昂首挺胸,派頭十足,比南海縣令還神氣。這副模樣在廣州城裡獨樹一幟,不僅本地官弁認得,連販夫走卒、牢頭雜役也過目不忘。
他一面往裡走一面問:「沒虐待兩位總商吧?」
牢頭陪著笑臉,「二位爺拔根毫毛,比我們的腰都粗,小的豈敢不恭敬。二位爺一進來,知縣大人就關照要好生侍候。」
梁廷枏滿意地說:「你算是明事理的。」
伍紹榮站起身,隔著木柵叫道:「梁先生,您怎麼來了?」
梁廷枏道:「我帶來欽差大臣的諭令,放你們出去。」
盧文蔚聞言,一陣驚喜,「五爺,我那卦算得精準,果然是有驚無險!」
待牢頭掏出鑰匙打開號間,梁廷枏一步踏進去,「崇曜啊,外邊的事知道嗎?」「崇曜」是伍紹榮讀書時梁廷枏給他起的學名,後來用作官名。
伍紹榮道:「知道一些。」伍、盧二人被拘後,家人探監時,曾把外面的情況告訴過他們。
梁廷枏用手指把伍紹榮衣服上沾黏到的草葉摘去,像師長關護學童,「義律同意繳煙了。好傢伙,兩萬多箱!」
伍紹榮驚得眼珠子一跳,「兩萬多箱?那得裝多少馬車!真的?」
「哪還有假!白紙黑字,蓋著夷文印鑒的上繳清單。商館斷水斷食整整三天,夷商熬不住了,不得不繳。你爹怕出人命,立即叫雜役給每棟商館送去兩桶清涼井水,三百多夷人像久旱逢甘霖似的簇擁過去,排著長龍依次舀水喝,鯨吸牛飲,喝得淨盡。」
梁廷枏陪著伍紹榮和盧文蔚往外走,邊走邊說話:「扶胥碼頭的各國水艄蠢動不止,林欽差、鄧督憲和豫關部怕出事,準備將包圍夷館的弁兵撤下調往黃埔島。鄧督憲提議放你們二人出去,把從商館裡撤出的八百傭工雜役編組成隊,分晝夜兩班,繼續包圍夷商。這兩天,一直是伍老爺和盧老爺在辦差,他們年高體弱,禁不起折騰。鄧督憲和豫關部說十三行公所是半個衙門,負有交通夷商查驗夷船傳諭憲令的責任,沒人料理不行。我也借機替你們美言幾句,林欽差耳朵根子一軟,便答應了。」
盧文蔚苦笑道:「五爺,你有個好老師,在我們大難當頭時,救了咱們一命。」
伍紹榮大夢初醒似的作了一個長揖,「多謝老師關照。」
| FindBook |
有 12 項符合
鴉片戰爭 肆之壹: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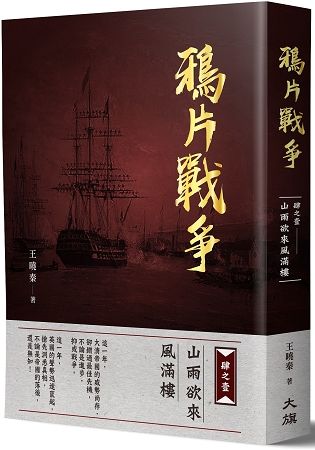 |
鴉片戰爭肆之壹:山雨欲來風滿樓 出版日期:2018-07-01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鴉片戰爭 肆之壹:山雨欲來風滿樓
扣除勝者的餘裕,減去敗者的藉口,添加軍者的悲歌,增補商者的無奈,成就這部飽含詩意的民族痛史。清朝道光年間,烏煙沖天,上至皇親貴胄,下至販夫走卒,無不吸食鴉片,抽得形銷骨立,幾成廢人,卻依舊沉迷其中,無法逃脫……
你以為這是道光皇帝誓除鴉片的原因?
錯!戰爭的關鍵,古往今來都沒變過,只有一個字──錢!
國庫要稅收,官員要應酬,商人要貿易,百姓要生存,
怎能放任最重要的白銀如滔滔洪流湧入外國人的口袋?
與其擔心煙毒,不如思考怎麼回收白銀;
與其管束夷商,不如徹查廣東的貪官汙吏。
早在林則徐遠赴廣東之前,早在隆隆炮聲響起之前,
充滿金錢味的煙硝,便已率先燃起!
作者簡介:
王曉秦
高級教師。畢業於四川外國語學院,長期在內蒙古師範大學和北京印刷學院進行教學與研究工作。
多年來致力於文史類作品的寫作與研究;精通英文,善於挖掘國外的史料,並與中國史料進行對比研究,成果頗豐。出版過長篇歷史小說《李鴻章大傳》等七本著述和十本譯著(含合著)。
TOP
章節試閱
義律進入商館後發現各國商人沒有被抓被殺之虞,包圍商館的清軍封堵了所有路口,但號令嚴明,不闖入樓內、不損壞器物,不拘捕、不打罵、不傷害任何人,僅將夷商軟禁在樓內。武力營救人質似乎成了多餘之舉,義律反而惴惴不安起來。
他曾給佈雷克艦長下過命令,若六天內得不到消息,可以採用適當方式前來營救。在扶胥碼頭巡視時又曾授意「忠勇號」船長馬奎斯組織各船水艄,一俟清軍大開殺戒就以武力抵抗,衝破攔阻,營救商館裡的同胞。
可現在看來,事情顯然並沒有壞到那種地步。萬一佈雷克艦長和馬奎斯船長因為消息不明,採取極端行動,整...
他曾給佈雷克艦長下過命令,若六天內得不到消息,可以採用適當方式前來營救。在扶胥碼頭巡視時又曾授意「忠勇號」船長馬奎斯組織各船水艄,一俟清軍大開殺戒就以武力抵抗,衝破攔阻,營救商館裡的同胞。
可現在看來,事情顯然並沒有壞到那種地步。萬一佈雷克艦長和馬奎斯船長因為消息不明,採取極端行動,整...
»看全部
TOP
推薦序
推薦序
史學家陳寅恪先生有「以詩證史」說,小說是廣義的詩,亦足證史。王曉秦先生這部新著《鴉片戰爭》,即是充滿詩意的歷史小說。他用如椽大筆,繪形寫神,潑墨重彩地勾畫出一幅鴉片戰爭全景圖:虎門禁煙,英酋遠征,突襲舟山,關閘事變,廣州內河戰火,廈門島上烽煙,浙江鏊兵,長江大戰,斡旋媾和,簽字《南京條約》等等。其場景廣闊,情節跌宕起伏,可驚可怖之衝突,可歌可泣之故事,紛至沓來,讓人不忍釋卷。
人物從中英兩國帝王將相,到鴻商巨賈、煙民海盜,乃至販夫走卒,個個刻畫生動,個性鮮活。
在宏大敘事中,作者激情迸射...
史學家陳寅恪先生有「以詩證史」說,小說是廣義的詩,亦足證史。王曉秦先生這部新著《鴉片戰爭》,即是充滿詩意的歷史小說。他用如椽大筆,繪形寫神,潑墨重彩地勾畫出一幅鴉片戰爭全景圖:虎門禁煙,英酋遠征,突襲舟山,關閘事變,廣州內河戰火,廈門島上烽煙,浙江鏊兵,長江大戰,斡旋媾和,簽字《南京條約》等等。其場景廣闊,情節跌宕起伏,可驚可怖之衝突,可歌可泣之故事,紛至沓來,讓人不忍釋卷。
人物從中英兩國帝王將相,到鴻商巨賈、煙民海盜,乃至販夫走卒,個個刻畫生動,個性鮮活。
在宏大敘事中,作者激情迸射...
»看全部
TOP
目錄
壹 兩總督邂逅相逢
貳 道光皇帝談禁煙
參 樞臣與疆臣
肆 權相回京
伍 紅頂掮客
陸 因義士事件
柒 天字碼頭迎欽差
捌 廣州名士
玖 廣州十三行的官商
拾 欽差大臣嚴訓行商
拾壹 令繳煙諭
拾貳 商步艱難
拾參 英國駐澳門商務監督
拾肆 嚴而不惡
拾伍 夷商繳煙
拾陸 水師提督嚴懲竊賊
拾柒 珠江行
拾捌 虎門—金鎖銅關
拾玖 揚州驛
廿 閒話清福
廿壹 舊部歸來
廿貳 虎門銷煙
廿參 觀風試
廿肆 水至清則無魚
貳 道光皇帝談禁煙
參 樞臣與疆臣
肆 權相回京
伍 紅頂掮客
陸 因義士事件
柒 天字碼頭迎欽差
捌 廣州名士
玖 廣州十三行的官商
拾 欽差大臣嚴訓行商
拾壹 令繳煙諭
拾貳 商步艱難
拾參 英國駐澳門商務監督
拾肆 嚴而不惡
拾伍 夷商繳煙
拾陸 水師提督嚴懲竊賊
拾柒 珠江行
拾捌 虎門—金鎖銅關
拾玖 揚州驛
廿 閒話清福
廿壹 舊部歸來
廿貳 虎門銷煙
廿參 觀風試
廿肆 水至清則無魚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王曉秦
- 出版社: 大旗出版 出版日期:2018-07-01 ISBN/ISSN:9789869598392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400頁 開數:25
- 類別: 中文書> 歷史地理> 中國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