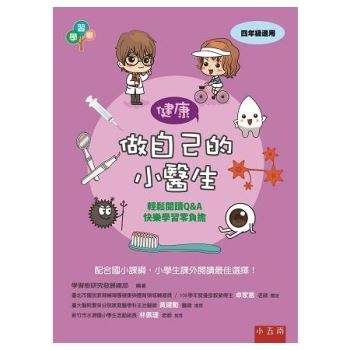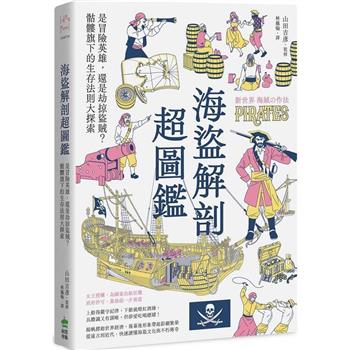當代法國最廣受愛戴的哲學家,Michel Serres 米榭‧塞荷, 於2019年6月1日,以88歲的高齡安詳辭世。《拇指姑娘》一書於2012在法國出版,至今已經銷售超過30萬冊,是塞荷畢生70餘本著作中最暢銷的一本書,引發一波對於新世代教育構想的熱烈討論。無境文化於2017年在台出版《拇指姑娘》,由法譯名家尉遲秀翻譯。本書為經過修訂後的第二版。
「要教導任何人任何事之前,至少得要先認識他。今天,出現在小學、中學、高中、大學裡的,是誰?」
《拇指姑娘》一書於2012在法國出版,至今已經銷售超過30萬冊,並且引發一波對於新世代教育構想的熱烈討論。作者Michel Serres(米榭‧塞荷)是史丹福大學教授、法蘭西文學院(Académie française)院士。是在大西洋兩岸都名重士林、又廣受一般讀者喜愛的當代哲學家。
Michel Serres認為,我們的社會已然經歷了兩次革命:先是從口傳到書寫,然後是從書寫過渡到印刷。現在這第三次革命,是因為新興科技的出現,催生了一種新的人類:他們如炫技般舞動著拇指,就可以通達上下古今的所有知識。作者暱稱這種新人類為「拇指姑娘」。
「拇指姑娘」的世界經歷了這麼巨大的變化,跟前兩次革命一樣,政治、社會以及認知方面的種種病變也將隨之而來。這就是危機浮現的時刻。拇指姑娘必須再去發明一種新的共同生活方式、新的機構、一種新的存在與認識的方法……必須開創一個新的時代,其中可預期的勝負結果,是不具名的複數人群,將凌駕在聲名顯赫的領導菁英之上;討論出來的知識,將凌駕在老師傳授的教條之上;一個去物質化、自由連接的社會,將凌駕在那單一方向的表演社會之上……
法國當代哲學大家,以他倍受愛戴的親切,生花妙筆下的睿智,向拇指姑娘提議一個跨世代的合作,一起去開創實踐這個烏托邦,那唯一有希望的現實。
法國在臺協會學術合作與文化處長Nicolas Bauquet(博凱)專文推薦。
| FindBook |
有 10 項符合
拇指姑娘(二版)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1 則評論 |
|
 |
拇指姑娘(第二版) 作者:米榭.塞荷 / 譯者:尉遲秀 出版社:無境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9-07-15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圖書名稱:拇指姑娘(二版)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Michel Serres 米榭‧塞荷
史丹福大學教授,法蘭西文學院(Académie française)院士。米榭‧塞荷出版了許多膾炙人口的哲學散文及科學史的著作。他不僅在法國家喻戶曉,譯成英文的作品也常常成為暢銷書。是少數能夠兼具科學以及文化的思考,對我們的世界提出深刻而白話的觀察,而在大西洋兩岸都名重士林又讓一般讀者喜愛的當代哲學家。
譯者簡介
尉遲秀
以翻譯為正業,從上世紀末工讀至今。
不務正業時,做過報社文化版記者、出版社主編、輔大譯研所講師、政府駐外人員。
譯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笑忘書》、《雅克和他的主人》、《不朽》、《戀酒事典》、《渴望之書》(合譯)、《HQ事件的真相》、《馬塞林為什麼會臉紅?》、《哈伍勒的秘密》、《童年》等書,近年開始投入童書及人文科學類的翻譯。
Michel Serres 米榭‧塞荷
史丹福大學教授,法蘭西文學院(Académie française)院士。米榭‧塞荷出版了許多膾炙人口的哲學散文及科學史的著作。他不僅在法國家喻戶曉,譯成英文的作品也常常成為暢銷書。是少數能夠兼具科學以及文化的思考,對我們的世界提出深刻而白話的觀察,而在大西洋兩岸都名重士林又讓一般讀者喜愛的當代哲學家。
譯者簡介
尉遲秀
以翻譯為正業,從上世紀末工讀至今。
不務正業時,做過報社文化版記者、出版社主編、輔大譯研所講師、政府駐外人員。
譯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笑忘書》、《雅克和他的主人》、《不朽》、《戀酒事典》、《渴望之書》(合譯)、《HQ事件的真相》、《馬塞林為什麼會臉紅?》、《哈伍勒的秘密》、《童年》等書,近年開始投入童書及人文科學類的翻譯。
序
推薦序
Nicolas Bauquet 博凱
歷史學博士
法國在臺協會學術合作與文化處處長 (2014-2018)
我原本是學院的史學研究者,如今成為了一名外交官;在世界的另一端,代表著法國,代表法國的藝術家、學者及科學家們。打我從事這個新的職業起,就竭盡所能的拼:促進聯繫、建立合作、籌劃及鼓勵。而在這十到十五年間,種種新的通訊工具改變了這個職業:眼睛盯著螢幕、指頭滑在手機,我加速時間,我縮短距離,我讓點子、聯絡、創意都數以倍計 – 我,還有我的合作對象、我的工作伙伴、連我的家人都一樣,都被做(Faire)的眩目迷離給捲了進去。但其實,那我還算是知識分子的過往,只在不久以前……那時我花時間去思考。閱讀許多書籍的時間。那時我會對一個思想追根究柢,而不是撲撈那些一閃而逝的點子。
這放棄所為何來?的確,是因為做(faire) 要比存在(être)容易。但同時是因為,像我當初那樣、及現下我這樣子的知識分子,已經不再覺得自己有能力去思考今日的世界。任何一個在這世界的漩渦中間稍稍駐足的人,都要覺得天旋地轉。天旋地轉,因為我們所認識的世界,它的各個面向改變之迅速。而種種信念有如紙牌城堡般的崩塌,也叫人天旋地轉。天旋地轉於驅動這已經滯礙難行的世界之種種元素,那無止無休的複雜性;而要想開始去理解這極速衝刺的將來到底駛向何方,所需要的知識之廣博浩瀚,還是叫人天旋地轉。必得需要幾十位的專家,幾千頁的書寫,才能夠開始思考(penser),重新再來。
此刻在我們手中的這本小書,多麼細緻,它的作者既不是資訊工程師,不是金融專家,也不是個科學家或是搞政治的。這個人不是什麼什麼的權威。這位哲學家,從很就以前,就對於存在與對於思考做了基進的選擇,尤其深切的是他在授業的選擇。Michel Serres 米榭・塞荷從來不是個權勢者,也不是個學究。帶著那每個法國人都熟悉而喜愛的細緻微笑,那散放喜悅的明耀雙眼,那引領我們進入一種思想的清晰溫柔嗓音,他行走世界;而那最被孜孜不倦傳遞的,是對自由的欣慕,以及對學生們的愛。
米榭・塞荷首先是個老師,而這本小書被構成的像是對這個新世代的一闕歌詠;歌詠這「拇指姑娘」的世代,以及這我們還如此難以去理解、去生活、去思考,這正在形成的新世界。在知識之階層體系崩壞的年代,傳承會變成什麼?當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可以去檢視那些權勢者,去表達他們的好惡時,權力又變成什麼?而在所有個體都可以有如數位聯絡的迅捷去重組他們的屬性,在這種時刻,我們的那些群體性將變成什麼?
在這本那麼小的書裡,沒有這些問題的答案。但裡面有一股力量,推著我們去思考,去迎接這個新世界的挑戰,帶著喜悅、自信去檢視,重新再來。就有如偉大的航海家們出發去發現那些新的世界。沒成為哲學家之前,在他很年輕的時候,米榭・塞荷曾經跑過船,遨遊在地球的四海之上。其實他一直都是,而如今他邀我們奔向海洋,重新再來。
閱讀愉快,也祝一路順風。
(翻譯:吳坤墉)
Nicolas Bauquet 博凱
歷史學博士
法國在臺協會學術合作與文化處處長 (2014-2018)
我原本是學院的史學研究者,如今成為了一名外交官;在世界的另一端,代表著法國,代表法國的藝術家、學者及科學家們。打我從事這個新的職業起,就竭盡所能的拼:促進聯繫、建立合作、籌劃及鼓勵。而在這十到十五年間,種種新的通訊工具改變了這個職業:眼睛盯著螢幕、指頭滑在手機,我加速時間,我縮短距離,我讓點子、聯絡、創意都數以倍計 – 我,還有我的合作對象、我的工作伙伴、連我的家人都一樣,都被做(Faire)的眩目迷離給捲了進去。但其實,那我還算是知識分子的過往,只在不久以前……那時我花時間去思考。閱讀許多書籍的時間。那時我會對一個思想追根究柢,而不是撲撈那些一閃而逝的點子。
這放棄所為何來?的確,是因為做(faire) 要比存在(être)容易。但同時是因為,像我當初那樣、及現下我這樣子的知識分子,已經不再覺得自己有能力去思考今日的世界。任何一個在這世界的漩渦中間稍稍駐足的人,都要覺得天旋地轉。天旋地轉,因為我們所認識的世界,它的各個面向改變之迅速。而種種信念有如紙牌城堡般的崩塌,也叫人天旋地轉。天旋地轉於驅動這已經滯礙難行的世界之種種元素,那無止無休的複雜性;而要想開始去理解這極速衝刺的將來到底駛向何方,所需要的知識之廣博浩瀚,還是叫人天旋地轉。必得需要幾十位的專家,幾千頁的書寫,才能夠開始思考(penser),重新再來。
此刻在我們手中的這本小書,多麼細緻,它的作者既不是資訊工程師,不是金融專家,也不是個科學家或是搞政治的。這個人不是什麼什麼的權威。這位哲學家,從很就以前,就對於存在與對於思考做了基進的選擇,尤其深切的是他在授業的選擇。Michel Serres 米榭・塞荷從來不是個權勢者,也不是個學究。帶著那每個法國人都熟悉而喜愛的細緻微笑,那散放喜悅的明耀雙眼,那引領我們進入一種思想的清晰溫柔嗓音,他行走世界;而那最被孜孜不倦傳遞的,是對自由的欣慕,以及對學生們的愛。
米榭・塞荷首先是個老師,而這本小書被構成的像是對這個新世代的一闕歌詠;歌詠這「拇指姑娘」的世代,以及這我們還如此難以去理解、去生活、去思考,這正在形成的新世界。在知識之階層體系崩壞的年代,傳承會變成什麼?當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可以去檢視那些權勢者,去表達他們的好惡時,權力又變成什麼?而在所有個體都可以有如數位聯絡的迅捷去重組他們的屬性,在這種時刻,我們的那些群體性將變成什麼?
在這本那麼小的書裡,沒有這些問題的答案。但裡面有一股力量,推著我們去思考,去迎接這個新世界的挑戰,帶著喜悅、自信去檢視,重新再來。就有如偉大的航海家們出發去發現那些新的世界。沒成為哲學家之前,在他很年輕的時候,米榭・塞荷曾經跑過船,遨遊在地球的四海之上。其實他一直都是,而如今他邀我們奔向海洋,重新再來。
閱讀愉快,也祝一路順風。
(翻譯:吳坤墉)
圖書評論 - 評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