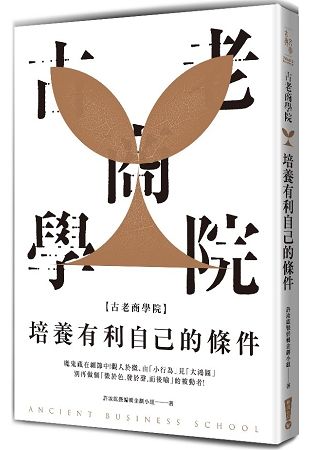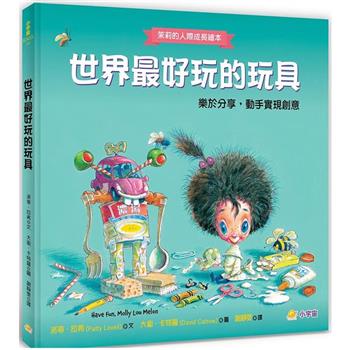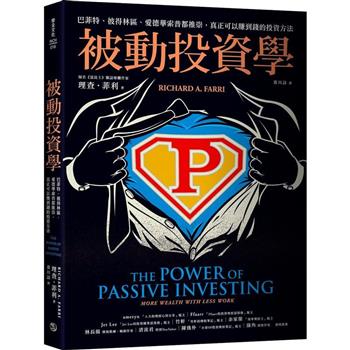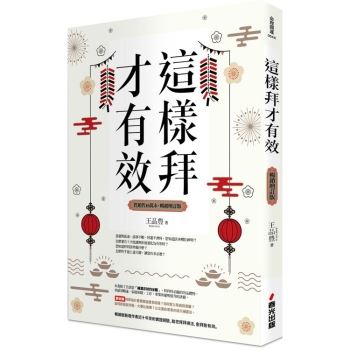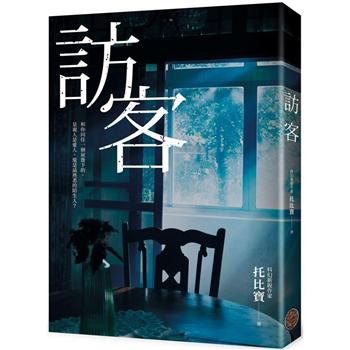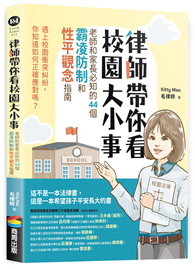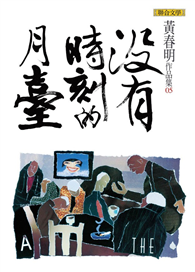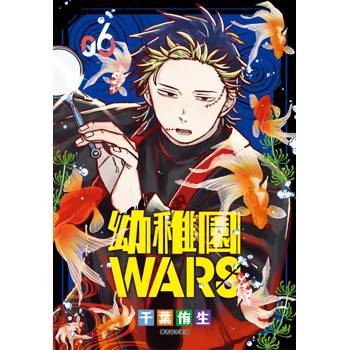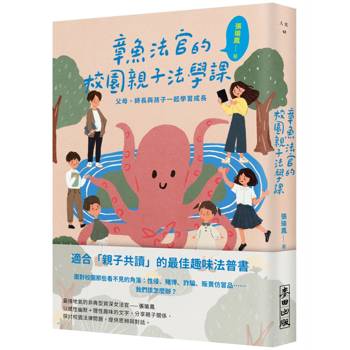為何這次被晉升的不是能力較強的陳經理,而是劉副理?
站在台上接受頒獎的居然是經常不見人影的小李!
每次出去開會,新來的小專員居然都可以拔得頭籌,把案子拿回來!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站在台上接受頒獎的居然是經常不見人影的小李!
每次出去開會,新來的小專員居然都可以拔得頭籌,把案子拿回來!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魔鬼藏在細節中
觀人於微、由「小行為」見「大鴻圖」
所謂,畫龍畫虎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在職場上有時看似諳合邏輯,但忽然一個逆轉,豬羊變色;有時感覺違背常理發展,卻一路順遂、扶搖直上。最怕的是,所有人都看明白了局勢,而你卻還在鼓中,以管窺天,如同穴居人看著壁上的影子起舞。
很多成功人士的舉手投足、大至佈局謀畫,小至言行談吐,其實都隱藏的許多玄機。羅馬並非一天造成,而大業亦非一蹴可幾,沒有天天日日的積累,也不會有平步青雲的一天。
專注,在培養自己的見微知著;淬鍊,從古人軼事中凝練成功智慧。
本書教你「如何走在職場的康莊大道」:
.看清身邊的小人
.發揮理性與感性
.謙虛實在最加分
.認真成就美麗
.培養智慧的眼光
別再做個「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的被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