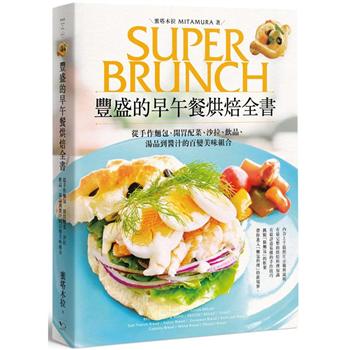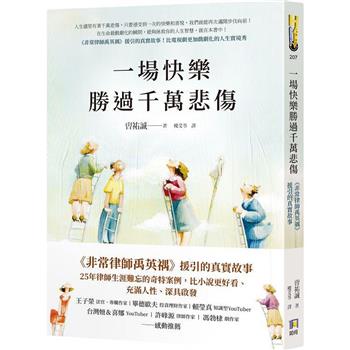編輯室報告
每一個死亡都有不同重量
每每聽聞韓國發生自殺事件,心中總有疑問:為什麼一個娛樂事業、經濟表現都充滿旺盛生命力的國家,有這麼多人尋短?是什麼原因讓他們不快樂?
後來我恰巧讀到陳慶德於udn鳴人堂的專欄文章,覺得可以將這系列文章收集成冊並加上新的內容,針對上述的疑問,為讀者(也為我自己)提供一個簡單的基礎概念。
一開始邀稿時,我便將這本書設定為概念書,字數與印刷尺寸都迷你,因此不求斬釘截鐵的定論,但希望能在有限篇幅中放入不同的觀看角度。編輯過程中,以作者觀點為骨幹,除了加強、調整當時因時效壓力而未盡完備的論點,也重新爬梳引用資料,以註釋的方式,提供對此議題有興趣的讀者延伸閱讀的方向。
期間,我邀請攝影師王志元一同前往書中提到的各個場景探勘、拍照,希望捕捉另一種韓國社會的面貌以供讀者參考。編輯遇上困難時,定居韓國的譯者陳雨汝也提供了諸多協助。至於設計師陳昭淵也提供個人觀點,以螞蟻吞食蜻蜓翅膀的畫面完整表達了「我們」的社會所帶來的巨大從眾壓力。經過將近一年的工作時間,最後完成了您手中這一本《他人即地獄:韓國人寂靜的自殺》。
在閱讀這本書之前,請容我先提醒您,為了方便討論,書中以「韓國人」作為一種集體標籤,去討論他們的生活與死亡。但真實人生不同於概念理解,無法「方便」解讀,更沒有一個足以概括而論的標籤。希望當您閱讀完之後,除了對於韓國社會的壓迫有所理解,也回望自身社會,理解每一個人所面臨的不同處境。
期待未來有更多類似的書種得以問世,讓我們閱讀「自殺作為社會事件」其背後所代表的意義與警訊。
編輯/陳夏民
序
在高自殺率的韓國社會,尋求臺灣未來之解法
「通過我,進入痛苦之城……拋棄一切希望吧,你們這些由此進入的人。」——但丁,《神曲‧地獄篇》。
提到韓國,大家想到什麼?
韓式烤肉很好吃?首爾很好逛?會吃狗肉?整形手術那麼多?抑或是街頭隨意可見可聽的明星歐巴歐膩(註:韓語音譯,指女生稱呼哥哥、姊姊)與K-Pop呢?
除了上述話題,近來更常聽見的是韓國成了「自殺共和國」:越來越多的韓國人,在學校,在家中,在停車場,在各式各樣的日常場所無聲響地死去。
我們經常聽到自殺不一定能解決問題,只看結果過於消極,更為要緊的是理解到底什麼原因促成了自殺。而高自殺率的背後,究竟有什麼值得解讀之處。
我們必須追問——為何如此?是怎麼樣的社會造就此風氣?韓國人一生面臨何種嚴厲的公審?貧富差距足以成為自殺的理由嗎?而又到底是怎麼樣的意識與思維,造成人們在生活遇到難關、壓力大就容易選擇自殺呢?
一個人輕生並非僅有一個簡單的原因。國民自嘲住在「自殺共和國」,也並非僅有一個簡單的理由,《他人即地獄》便是因應而生的作品。我試圖透過社會風氣、國民意識、韓語思維、生活壓力、年齡層、他人目光與生活樣態等各個角度,一一閱讀如學校、地鐵站、軍隊、漢江等自殺事件頻傳的場域,來拼構出「韓國人寂靜的自殺」背後的種種緣由。
自殺意圖恣意蔓延在韓國社會的同時,臺灣社會正因為許多因素,喊著要多向韓國學習。當我們欣賞韓國並試圖超越、學習,應也了解光鮮亮麗之下,為何有這麼多人選擇輕生。
接下來,請隨著我一同前往韓國社會各式場景,了解自殺風氣的生成。讓韓國成為我們的借鏡。也期待這樣一本小書,能夠帶給讀者們一個看待高自殺率社會的詮釋角度。
陳慶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