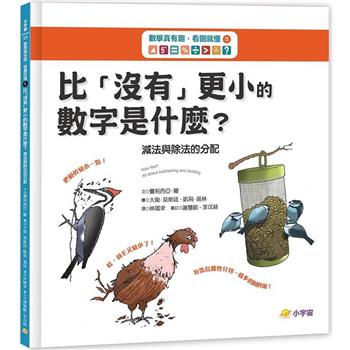HOT!《掌事》、《紙貴金迷》人氣作家清楓聆心最新作品
起點網站近80萬讀者點閱,讀者五顆★高評價推薦
讀者大讚:「出奇致勝,不落俗套的精彩!」
她,在復仇的路上,
他,在不想回家的路上,
一朝相遇,情未生,鬥智鬥命火花起……
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
──但有必要讓她家破人亡嗎?
橫行鳳來縣的桑家惡霸,因為莫名大火,一夕滅門,人稱報應不爽,
殊不知還剩下她──桑家么女節南,因為離家「學藝」逃過一劫。
身為惡霸後代,她堅決霸下去,不畏流言回家殮葬親人,隱忍查找蛛絲馬跡,
只是當她手刃仇人,走出大王嶺,卻在路上撿了一個迷路成性的世家公子……
這位桑家姑娘真是……特別。
不會作畫,卻在版畫舖子當學徒,還花錢請人代畫,
受全縣百姓厭惡,日日被告上衙門,
還住在燒得焦黑的慘案發生地,似乎不以為意。
回鄉收屍殮葬,可說是情理是孝道;替父兄挨罵受氣,是隱忍是籌謀,
他覺得,她是忍一時之氣,謀復仇大計,
果然──她不就在他面前殺人了嗎?
「王九公子,你最好忘了剛才之事,否則……」
「從今以後,我王泮林再不識桑六娘,妳我後會無期。」
他與她,以為從此各自天涯,
她走她的江湖路,他過他的望族公子生活,
卻不知一盤充滿陰謀的棋局正要展開,
他們不能避開,只能捲入……
| FindBook |
有 9 項符合
霸官:﹝卷一﹞紅衣青衫,大王膽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3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70 |
二手中文書 |
$ 262 |
文學作品 |
$ 276 |
愛情小說 |
$ 276 |
華文羅曼史 |
$ 277 |
言情小說 |
$ 277 |
古代小說 |
$ 308 |
中文書 |
$ 315 |
古代小說 |
$ 1050 |
華文羅曼史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圖書名稱:霸官:﹝卷一﹞紅衣青衫,大王膽
圖書評論 - 評分: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