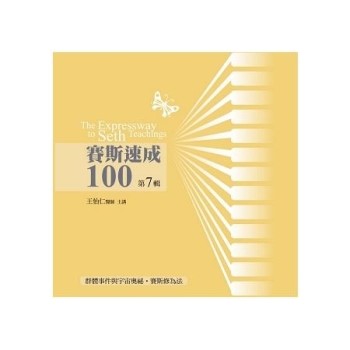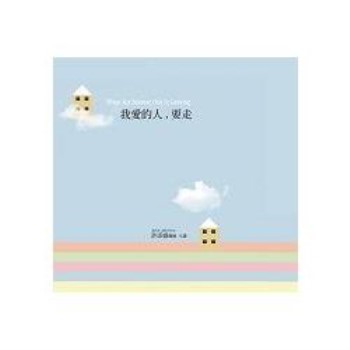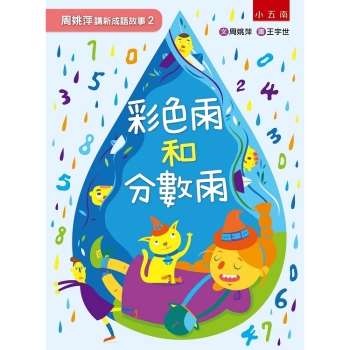臺灣紀錄片中的環境意識
日期:2016年9月17日
主講人:郭力昕(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副教授)
關於臺灣紀錄片中的環境意識與概念,我所關切的是從哈拉維(Donna Haraway)的資本紀(Capitalocene)角度出發,她指出環境問題是一種資本主義,是關於經濟、人類往哪裡去以謀求幸福生活的問題。
當今,環境問題是區域性或全球性的一個最大且最為迫切的政治議題,人類給自己創造出來的環境危機、存續危機,我認為已經超越國族、階級、勞資等各式問題,並不是說這些問題不存在,它們也很重要,而且可能與環境問題間接扣聯,但當我們活不下去的時候,其他的問題若過度關切,就容易疏忽環境問題的結構性,以至看不清其中的政治問題。
這個政治議題與每個人切身相關,沒有人逃得掉。不論你是哪一種國族主張;不論你是資本家或是社會底層人民;不論你的性別取向;不論你的任何身分……我們每個人都需要呼吸乾淨的空氣、喝乾淨的水、吃不受污染的農產品。否則,因為地球老化,海平面不斷升高,我們就得在陸沉於海裡的土地上討論這件事情了。
因此,關於此一基本生命權的討論,回到紀錄片裡面來看,涉及到我們的生命權為什麼無以為繼?我們的生命權被誰剝奪了?如何要回生命權?這也是紀錄片所具有的認識與行動之功能。而接下來將舉臺灣的一些紀錄片為例,看看這兩方面的一些表現。
環境議題是誰的責任?
首先,談談認識上的一些問題——環境破壞是誰的責任?在臺灣,多數人或者主流意識型態通常會將責任指涉到每一個人,即環境破壞每個人都有責任,所以要隨手做環保、隨手關燈、使用漱口杯刷牙、少用兩個塑膠袋等等,這些確實都對環境造成了破壞。但環境摧殘的主要因素,並非在個人的環保實踐上,雖然實踐是有幫助的。遂而有另一種立場指出個人非占主要因素,應該是製造重度污染的這些工廠老闆、企業資本家們的責任。
接著,我們就會提問,為什麼法令無法有效地節制他們呢?並繼續思考,其實責任應是在國家,具有政治權力能夠去改變環境政策,但法規趕不上環境破壞速度。例如工業所製造的空氣污染、水污染之檢驗與處罰方式,當只處罰一點點,企業根本無所謂,它的利潤是千萬倍,罰就罰。負責國家環境政策的人,他可能沒有足夠的認識,或是他縱容這些工廠繼續污染環境,原因可能是國家優先考慮了經濟發展,或者國家與這些企業是一個利益共同體,因為經濟發展有利於選票、政績,甚至可能有力於自己的口袋。
而對我來說,最終還是要回到每一個地球公民身上,但我們不具有地球公民的意識與責任,我們的公民是一個不行動的公民,面對環境破壞致使我們沒有辦法呼吸下去了,我們的人民並沒有做出行動。不做行動可能有幾個原因,第一,人民也迷信經濟增長,還是覺得國家的經濟富強是一個優先的價值,在國家更有錢的這個意義之下,有愈來愈多的罹癌風險出現在我們自身或周遭,使得這個意義強過了我們的生命,任它在這個被破壞的環境裡面,快速地枯萎、死亡,這是不可思議的,是一個奇怪、不理性的集體狀態。
第二,部分的公民站在一個自私的角度,消費今天、不管明天,把債留給子孫,明天地球毀滅了,我看不到沒關係,我今天舒服就好。或者,公民意識不是沒有,但人民總會覺得個人力量抵抗不了國家、環境政策,既然是自己沒辦法決定的事情,就像決定不了資本主義一樣,抵抗不了我就加入它,至少自求多福,一種較為虛無的作為,不相信行動力能夠帶來改變。
還有一個原因是絕大部分的公民欠缺基本的科學常識,包括我在內,關於污染在何處、會帶來什麼樣的災難、對身體有什麼影響……我們都少有認識,而這也就開始扣上了我們的影像議題。我們今天有許多的認識是來自新聞、紀錄片等各式各樣的影像,影像帶給我們的是一種看得見的問題。
而污染常常看不見,因為看不見,所以我們願意慢性的在環境中自殺或者被他殺,而這慢性其實在加速度,因為污染問題是愈加嚴重而不是減緩,但不能因為看不見就認為不是問題。例如細懸浮微粒(PM2.5),它小到可以鑽至你的血管裡去,讓你得肺腺癌,當你發現時,已經是末期。我們的一些認識常是來自於見證,那麼,我們該怎麼把汙染影像化呢?這不容易做到,但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問題。
我們都知道環境、水、食物、空氣不安全,我們也看到身邊其實愈來愈多人罹癌,甚至自己,但這只增加了恐慌,並沒有增加我們想要去分析、理解,也就不能夠產生有效的行動,因為恐慌帶來的行動,往往只是逃,逃到一個更安全的地方,但行動所針對的方向不對。
只見結果不談原因,紀錄片如何增進公民意識?
接下來說說影像到底如何讓我們看見?並促成我們行動的能量。我會以臺灣近年的紀錄片為例,在2008年之前,其實臺灣已有涉及環境的紀錄片,如反核議題、或是像慈濟大愛電視臺的記者曾追蹤新竹科學園區的廢料去向等,這些都具有認識意義的。
其中,有一類的紀錄片較為感性,有一種浪漫腔調,以美感化的影音、旁白方式,來看生態破壞。如媒體人陳文茜與廣告人孫大偉共同製作的《±2℃》,2010年開始在各大有線、無線電視頻道上不斷播放,學校也將之編為環境教材,網路上也可以看到;之後,齊柏林的《看見臺灣》在2013年年底上映,二個月的票房超過臺幣二億,成為臺灣票房最高的紀錄片。而這也是在臺灣觀看人次最多的兩部紀錄片。
《±2℃》由幾種風格混搭在一起,在背景音樂上,有感性的古典樂、也有好萊塢式的驚悚配樂,並搭配令人害怕的數據資料,呈現地球暖化的程度、在世界各地所造成的災害等等。紀錄片裡大量談到地球暖化的結果,卻沒有一句話提到原因,為什麼不提,因為提及就尷尬了,陳文茜一方面相信資本主義、經濟發展,而暖化正是這些發展意識的結果,但另一方面又製作了《±2℃》,這相當滑稽,讓人不曉得她的立場是什麼。
而感動的另一種表現,是搭配一首已經被過度濫用的1970年代臺灣民歌《美麗島》,胡德夫在滿布漂流木的海灘上,突兀的彈琴演唱,試圖傳達臺灣是個美麗寶島,我們不要破壞環境。又如採用幾米的插畫結合動畫,將嚴重的問題以溫暖、童趣的話語呈現,這對於孩童、青少年的環境教育還可以,但若仔細思考紀錄片的指涉對象究竟是誰時,又是令人感到混亂的。驚悚與臺灣文青式的感動混搭在《±2℃》中,算是紀錄片製作上的創舉。但在驚嚇和感動之後,觀眾仍不曉得要往哪些方向走。
《看見臺灣》是一部從頭到尾全在飛機上空拍的紀錄片,讓人看見臺灣的美麗,也看見臺灣國土遭受破壞等等。但其實紀錄片有超過二分之一的篇幅,不是看見美麗,而是看見吳念真旁白裡所謂的哀愁。將環境破壞用「哀愁」這字眼強調,有著一種文藝腔式的、對環境的浪漫關切:環境可能是讓臺灣無以為繼的一個問題,使用哀愁描述紀錄片裡所呈現的臺灣各地環境與土地破壞的景象,其實相當適切某種文藝腔調。
《看見臺灣》讓觀眾看到土地破壞的現象,同樣也不追問原因,並且有意的選擇與忽略一些事物,比如飛到墾丁,它就繞過了第三核能發電廠。而當你看到土地破壞的景象,但不追問原因的時候,就真的變成了一個哀愁。在從影像創作的角度來看,影像是個很弔詭的事情,雖然拍的是髒亂,但構圖起來還是很漂亮,呈現一種破壞、醜陋的美感,要是不去追問這些東西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不給其他資料的話,那就純粹變成一種視覺觀看,凝視我們的土地遭破壞,最後只是變成一個印象,觀眾看完很感傷卻沒有辦法知道更多一層,行動也是短暫的。這部紀錄片創造了臺灣政府的一些行動,馬上成立國土保育小組,但當隨著新聞轉到其他的社會事件後,大家也就淡忘、無人繼續追問小組的動向。
當影像創作變成環境行動
另外一種紀錄片形式,相對小眾,但可能相對有力量一些,能給較多的認識甚至行動的可能,影片揭露問題、見證污染的事實、參與環保運動,甚至記錄者同時也是參與者。以《遮蔽的天空》(2009)為例,導演紀文章是鹿港人,記錄了地方環保組織「反彰火聯盟」多年來反對臺灣電力公司在彰化縣彰濱工業區蓋「彰工火力發電廠」的環境運動。又如林家安記錄反六輕與八輕的《天堂》(2010),「輕」是輕油裂解廠的簡稱,生產乙烯等石化原料,供製造塑膠、合成纖維和化學品等,環保團體多年來一直在對抗五輕、六輕、八輕。
而柯金源的《空襲警報》(2013),英文片名很有意思,《Take My Breath Away》是一首英文歌名,本來是說對方太吸引人、令人屏息。導演從南到北,記錄臺灣西海岸的許多環境問題與行動。片中有一位雲林縣臺西鄉的漁民,因為自己的父母兄姐與兒子,全死於肝硬化,且自己也罹患此症,他不敢在家鄉住,因為這裡已是汙染非常嚴重的地方。於是,他不得已以一輛改裝為簡陋臥室的中型卡車為家,上面有一些基本的設施,偶爾回家換一下衣服,再開車到溪頭等地空氣品質較好的地方,過著漂泊的生活。另外,還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是拍攝金門中正國小科展學生團隊檢測金門的空氣,證明環境是互相連通、沒有辦法隔絕的。
當紀錄片可以成為行動時,那是一種什麼樣的行動?例如,今年由「PM2.5影像行動小組」發起的「脫口罩!找藍天」影像行動計畫,成員是在臺灣中部地區的影像工作者,有些是在學校教書的老師,如林泰州導演,是一名傑出的當代視覺藝術家,從事實驗性的影像創作,他在去年初接受電腦斷層掃描的檢查,發現肺裡有0.5公分的肺結節,醫生告訴他,如果肺結節長到一公分時,那就是肺癌。所以,他從去年開始,將創作重心轉向環境污染的影像記錄上。他同樣採取空拍的方式,透過影音敘事的藝術性手法,以雲林麥寮石化工業區為對象,拍攝一部《看不見的鬼島》(2015),揭露雲彰地區石化工業導致環境污染的問題所在。影展集結了包括資深導演蔡崇隆等共18位導演,拍攝了20部短片。
他們的行動包括在募資平臺上集資,截至今年6月,他們募資到80萬臺幣,雖然不多,但足以啟動全臺灣的巡迴放映計畫。我想就以這個例子作為結尾,當你的身體、你的生命權遭受威脅時,大家一起出來做有效的行動,雖未必一定有幫助,但是沒有行動萬萬不能。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影像軌跡.策展美學:春之當代藝論2015-2016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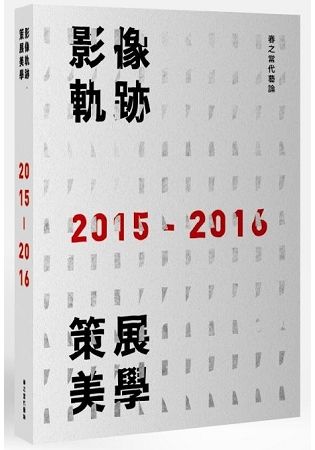 |
影像軌跡.策展美學:春之當代藝論2015-2016 出版日期:2018-06-25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458 |
Arts & Photography |
$ 493 |
藝術總論 |
$ 510 |
中文書 |
$ 522 |
藝術總論 |
$ 522 |
美術 |
$ 522 |
藝術設計 |
$ 551 |
藝術理論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影像軌跡.策展美學:春之當代藝論2015-2016
春之文化基金會自2013年起舉辦的「春之當代夜」系列講座,探討並累積了藝術評論、藝術創作、策展實踐、藝術史研究、博物館發展、以及建築與城市等多元議題的研究資料,希望藉此建立起台灣當代藝術與文化相關的檔案庫,並橫向連結臺灣與國際交流關係的網絡。
本書即集結了「春之當代夜」系列講座2015-2016年的發表成果,針對策展趨勢觀念與實務操作、涉及歷史或集體記憶的記錄影像討論、檔案作為創作概念與形式、當代社區與藝術生產,以及當代藝術與民間藝術等幾大當代議題,收錄侯王淑昭、龔彥、黑田雷兒(Kuroda Raiji)、徐文瑞、顧錚、龔卓軍、孫松榮、董冰峰、清水敏男(Toshio Shimizu)、郭力昕、許芳慈、趙川、李子寧、拉琥(Steve La Hood)、阮慶岳、洪子健、陳瀅如、孫華翔、李應平、陳伯義、張世倫、邱坤良、蕭瓊瑞、林承緯等24位專家學者的講座內容與專文。
TOP
章節試閱
臺灣紀錄片中的環境意識
日期:2016年9月17日
主講人:郭力昕(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副教授)
關於臺灣紀錄片中的環境意識與概念,我所關切的是從哈拉維(Donna Haraway)的資本紀(Capitalocene)角度出發,她指出環境問題是一種資本主義,是關於經濟、人類往哪裡去以謀求幸福生活的問題。
當今,環境問題是區域性或全球性的一個最大且最為迫切的政治議題,人類給自己創造出來的環境危機、存續危機,我認為已經超越國族、階級、勞資等各式問題,並不是說這些問題不存在,它們也很重要,而且可能與環境問題間接扣聯,但當我們活不...
日期:2016年9月17日
主講人:郭力昕(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副教授)
關於臺灣紀錄片中的環境意識與概念,我所關切的是從哈拉維(Donna Haraway)的資本紀(Capitalocene)角度出發,她指出環境問題是一種資本主義,是關於經濟、人類往哪裡去以謀求幸福生活的問題。
當今,環境問題是區域性或全球性的一個最大且最為迫切的政治議題,人類給自己創造出來的環境危機、存續危機,我認為已經超越國族、階級、勞資等各式問題,並不是說這些問題不存在,它們也很重要,而且可能與環境問題間接扣聯,但當我們活不...
»看全部
TOP
作者序
財團法人春之文化基金會董事長 侯王淑昭
《影像軌跡.策展美學:春之當代藝論2015-2016》一書的內容,選自2015年至2016年間舉辦的「春之當代夜」系列主題講座。「春之當代夜」是春之文化基金會自2013年起所規劃、舉辦的活動,我們邀請國內外藝文相關領域的專業人士共同參與,大家以殊異的理論視角、實踐經驗,分享其對藝術的思考,並與現場的觀眾共同探討、交流,之後,我們再以兩年為期,整理文字、精選講座內容,以《春之當代藝論》之刊名出版發行。
為了進一步串聯在地資源、促進國際對話、引發不同面向的當代議題討論,2015年至20...
《影像軌跡.策展美學:春之當代藝論2015-2016》一書的內容,選自2015年至2016年間舉辦的「春之當代夜」系列主題講座。「春之當代夜」是春之文化基金會自2013年起所規劃、舉辦的活動,我們邀請國內外藝文相關領域的專業人士共同參與,大家以殊異的理論視角、實踐經驗,分享其對藝術的思考,並與現場的觀眾共同探討、交流,之後,我們再以兩年為期,整理文字、精選講座內容,以《春之當代藝論》之刊名出版發行。
為了進一步串聯在地資源、促進國際對話、引發不同面向的當代議題討論,2015年至20...
»看全部
TOP
目錄
序|侯王淑昭
向後看向前走: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的策展試驗|龔彥
獅子身中蟲——福岡亞洲美術館所扮演的另一個角色|黑田雷兒(Kuroda Raiji)
什麼是好展覽?:論策展意識|徐文瑞
中國當代攝影思考記錄與記憶之關係|顧錚
給那不曾發生的:另一種台灣影像史|龔卓軍、孫松榮
禁止、反抗與自我組織:中國影像藝術檔案|董冰峰
藝術驅動城市創造力|侯王淑昭、清水敏男(Toshio Shimizu)
臺灣紀錄片中的環境意識|郭力昕
開啟等候室:塔西米克《灑了香水的惡夢》與福恩德斯《玻恩托克族輓歌》之後殖民式閱讀|...
向後看向前走: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的策展試驗|龔彥
獅子身中蟲——福岡亞洲美術館所扮演的另一個角色|黑田雷兒(Kuroda Raiji)
什麼是好展覽?:論策展意識|徐文瑞
中國當代攝影思考記錄與記憶之關係|顧錚
給那不曾發生的:另一種台灣影像史|龔卓軍、孫松榮
禁止、反抗與自我組織:中國影像藝術檔案|董冰峰
藝術驅動城市創造力|侯王淑昭、清水敏男(Toshio Shimizu)
臺灣紀錄片中的環境意識|郭力昕
開啟等候室:塔西米克《灑了香水的惡夢》與福恩德斯《玻恩托克族輓歌》之後殖民式閱讀|...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龔彥等人
- 出版社: 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8-06-25 ISBN/ISSN:9789869615594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00頁 開數:17*23
- 類別: 中文書> 藝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