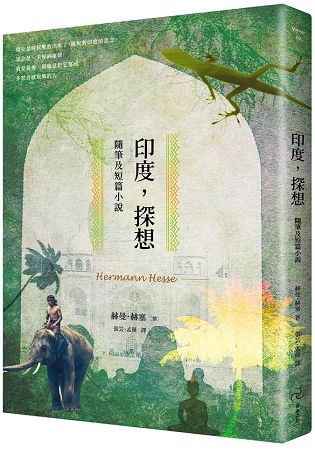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赫曼.赫塞 自東方之行歸來歷時十餘年
隨著創作《浪流者之歌》期間經歷的創作瓶頸、精神壓力
不斷寫下他腦中從不停止的思辯,不斷向印度探問、冀求回歸生命原鄉的試煉之作
是時候解放出來,擺脫對印度的思念。
思念是一美好的事情,我是最後一個願意把它當成多愁善感取樂的人。
但是感情和幻想有一個特點,實現某種升華之前,
它們的力量、美麗和價值在逐漸增強,此外它們又會越來越有惰性,
接著就會有其他幻想、其他情感從我們永不枯竭的靈魂深處升騰而出。
然後帶走這場印度遊戲,帶走對印度的懷念……
自1911年至亞洲旅行數月之後,赫塞對於東方、印度、中國的懷想,仍未停止,內在的追尋仍一直持續。他對於歐洲在精神靈性上的逐漸空洞化感到不滿,深信靈魂的答案就在東方。然而實際體驗了東方生活之後,他自承:
印度精神還不屬於我,我還沒有找到它,我還在尋找。當時我也正是為此離開了歐洲,因為我的旅行是一種逃避。我逃離歐洲,幾近憎惡,我討厭它毫無品味的審美,喧囂嘈雜的集市,倉促匆忙的焦躁不安,還有粗魯愚蠢的追求享樂。
我通往印度和中國的道路並非要搭乘郵輪和火車,我必須獨自找到所有那些神祕的橋梁。我必須停止在那裡尋求救贖、擺脫歐洲,必須停止在心中仇視歐洲,必須在感情和精神上擁有真正的歐洲和真正的東方,這條路持續了一年又一年,歷經多年的痛苦、不安、戰爭和絕望。
本書收錄這段期間的多篇隨筆,可以窺得赫塞一直以來對印度及中國文化的熱愛。赫塞嚴厲批判歐洲社會腐蝕人心的戰爭意識,也以慈悲之心看待受到西方國家侵入而使文化蒙塵的亞洲諸國,同時卻也在百年之前就已預見了中國這一民族在未來世界舞台上的捲土重來。
雖投入的是文學創作,赫塞也從未停止靈性的追尋,冀望從形上的心靈層次為人類尋得出路。本書收錄五篇短篇小說,其中〈新娘〉及〈羅伯特.阿吉翁〉是得自這段旅行中親身見聞,生動地描繪出因應當時愈來愈多歐洲人移居亞洲,生活及工作型態的大幅變化也碰撞出更多的文化磨擦。〈一位印度王的傳奇〉、〈森林人〉及〈印度式生命軌跡〉則像是《浪流者之歌》的前奏小品,赫塞透過小說型式將印度思想普遍的棄世修行、瑜伽靜心、輪迴等觀點融入故事之中,藉以探入源自印度的吠檀多哲學及之後對世界影響更大的佛教思想。
作者簡介:
赫曼.赫塞(Hermann Hesse, 1877-1962)
出生於德國南部的小鎮卡爾夫,曾就讀墨爾布隆神學校,因神經衰弱而輟學。1899年,自費出版了第一部詩集《浪漫主義之歌》,未獲得公眾認可;1904年,以第一部長篇小說《鄉愁》(Peter Camenzind,又譯《彼得.卡門欽得》,一舉成名。後來他辭去工作,專事寫作,先後完成《車輪下》(Unterm Rad, 1906)、《生命之歌》(Gertrud, 1910,又譯《蓋特露德》)、《藝術家的命運》(Roßhalde, 1914,又譯《羅斯哈爾特》)等早期重要作品。
1912年,赫塞移居瑞士並在1923年加入瑞士國籍。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赫塞的創作發生了明顯的變化,試圖從宗教、哲學和心理學方面探索人類精神解放的途徑。這時期的主要長篇小說有《徬徨少年時》(Demian, 1919,又譯《德米安》)、《流浪者之歌》(Siddhartha, 1922,又譯《悉達多》)、《荒原之狼》(Der Steppenwolf, 1927)、《知識與愛情》(Narziß und Goldmund, 1930,又譯《納爾齊斯與歌爾德蒙》)和《玻璃珠遊戲》(Das Glasperlenspiel, 1943)等。其中《荒原之狼》轟動歐美,被托馬斯.曼譽為德國的《尤利西斯》。1946年,赫塞獲得歌德文學獎,及諾貝爾文學獎。
譯者簡介:
張芸,德語文學博士,寧波大學外國語學院德語系教授。
孟薇,德語文學碩士,煙台大學外國語學院德語系講師。
章節試閱
印度訪客
尚未成熟便摘下的果實對我們毫無用處。我的一生有一半以上的時間都在從事印度和中國研究——並非要謀取學者之名,不過是習慣於汲取印度及中國文學創作和虔誠的芬芳。十一年前我曾去印度旅行,在那裡,我看見了棕櫚樹和寺廟,聞到梵香和檀香的味道,吃過略帶酸澀的芒果和軟糯可口的香蕉。可是,在我與這一切之間還隔著一層薄紗,置身於康提的僧眾之間,我依然像先前在歐洲的時候一樣,無法遏制地渴望真正的印度,渴望印度精神,渴望跟它有一次生動活潑的接觸。印度精神還不屬於我,我還沒有找到它,我還在尋找。當時我也正是為此離開了歐洲,因為我的旅行是一種逃避。我逃離歐洲,幾近憎惡,我討厭它毫無品味的審美、喧囂嘈雜的集市、倉促匆忙的焦躁不安,還有粗魯愚蠢的追求享樂。
我通往印度和中國的道路並非要搭乘郵輪和火車,我必須獨自找到所有那些神祕的橋梁。我必須停止在那裡尋求救贖、擺脫歐洲,必須停止在心中仇視歐洲,必須在感情和精神上擁有真正的歐洲和真正的東方。這條路持續了一年又一年,歷經多年的痛苦、不安、戰爭和絕望。
隨後這個時刻來到了,距離現在還不算久遠,那時我已不再嚮往錫蘭的棕櫚海灘和貝拿勒斯(瓦拉納西)寺廟林立的街道,不再希望自己是佛教徒或者道士並且得到一位聖人和法師的教導。這些全都變得不重要了,可敬的東方和病苦的西方之間、亞洲和歐洲之間最大的區別對我而言同樣不再重要。我認為,盡可能多地研究東方智慧和宗教祭禮已不再重要,我發現,當今無數老子的崇拜者對道的了解還不如歌德,而歌德從沒有聽說過「道」這個詞。我知道,歐洲跟亞洲一樣,存在一個隱祕而永恆的價值和精神的世界,這個世界既不會因發明了機車而更加美好,也不會因俾斯麥而毀滅,生活在這個永恆的世界裡是愉快的、正確的,這是一個平和的精神世界,歐洲和亞洲,《吠陀經》和《聖經》,佛陀和歌德在其中有著相同的比重。這裡開啟了法師對我的教導,學習還在繼續;這裡學無止境。可是我已經不再對印度抱有憧憬,不再寄希望逃離歐洲,現在,佛陀、《法句經》和《道德經》讓我覺得純粹和親切,不再難解困惑。
現在果實已經成熟,從我的生命之樹掉落。我隱去動機和姓名,也不說這一切如何實現,如何將我從隱居生活中再次衝入世間數日,新的人、新的關係如何突然間與我相遇。我只講述其中那段與印度有關的插曲。
****************
短篇小說: 印度式生命軌跡
羅摩是護持神的人形化身之一,這位毗濕奴在一次與魔王的激戰中用新月形箭將其殺死,而後又再次以人形踏入人類的輪迴循環中。他的名字叫拉華納,生活在恆河邊,是尚武的王公。他就是達薩的父親。達薩幼年喪母,父親隨即續弦,娶了一位美貌而野心勃勃的女子,她很快就給這位王公添丁,達薩從此就成為這位繼母的眼中釘。她不想讓長子達薩繼承大權,而一心希望自己的兒子那拉能夠登上王位。她處心積慮地離間達薩與父親的關系,一旦找到機會就立馬將達薩給趕開。
但拉華納宮中有一位身任宮廷祭司要職的婆羅門貴族華蘇德瓦,這位智者看透了她的用意,決意不讓她的心思得逞。華蘇德瓦憐惜這個小男孩,他覺得小王子繼承了其母的虔誠秉性和正義感。他時時暗中照看著小達薩,避免他受到傷害,還注意著一切機會,設法讓孩子脫離繼母的魔掌。
國王拉華納擁有一群用於獻祭梵天的母牛,牠們被視為神牛,所產的牛奶和奶油是用於供神的。全國最好的牧場為這群神牛所專享。一天,一位照看神牛的牧人將一批奶油運到宮中,並匯報說,放牧神牛的那塊牧場已經出現了乾旱的跡象,因此一部分牧人認為,應該把牛群趕到更遠處的深山裡面去,那裡水源豐富,青草鮮美,即便在最乾旱的時期,水源也不會枯竭。婆羅門華蘇德瓦與這位牧人相識多年,知道他是一個友善忠誠的人,便將小達薩托付於他。第二天,當小王子達薩失蹤,眾人遍尋不得之時,唯有華蘇德瓦和這位牧人知道這次失蹤的祕密。小男孩達薩被牧人帶進了山中。他們隨著緩緩行進的牛群向前走著,達薩很樂意加入牧人的行列,高高興興地跟著放牧。達薩成了一個小牧童,在放牧生活中逐漸長大。他幫著照料母牛,學著擠牛奶,和小牛犢一起嬉戲,睡臥在鮮花叢中,渴了就喝些甘甜的牛奶,光腳上沾著牛糞。達薩喜歡這種生活,他熟悉牧人和牛群,熟悉了樹林和各種樹木以及種種果實,他最喜愛芒果樹、野無花果和瓦楞伽樹,他在碧綠的荷花池塘中採摘甜嫩的鮮藕,每逢宗教節日就用火樹花朵給自己編織一只鮮紅的花環來戴上。他也熟悉了野獸的生活方式,懂得怎麼躲開老虎,怎麼與聰明的獴和開心的豪豬交朋友。雨季到來時,達薩便在山裡幽暗的遮風擋雨的小屋裡和其他孩子一起玩遊戲,唱歌,或者編織籃子和蘆席,用以消磨漫長的時光。達薩並沒有完全忘記自己先前的生活以及昔日的奢華宮廷,不過那些在他心中已經恍若隔世,猶如一場夢。
一日,牛群遷移到了另外一個地區,達薩跑到森林裡去,想尋找些美味蜂蜜。他自從認識了森林,便深深地愛上了森林,尤其是眼前這座森林,簡直美麗得驚人。陽光透過樹葉和枝杈如金蛇一般舞動;鳥兒的鳴唱、樹梢的風聲、猴子的叫聲,這一切奏出一首美妙的樂曲;光與聲於此交織成了一幅熠熠發光的神聖妙網。林間彌漫著各種各樣的氣味,花朵,樹木、葉片、流水、苔蘚、動物、果實、泥土和蘑菇的氣味,有的苦澀,有的甘甜,有的濃烈,有的恬靜,有的歡快,有的悲哀,有的刺鼻,有的柔和,種種氣息時而雜糅於一處,時而四下飄散。間或可以聽到一道清泉在不知何處的山谷中奔騰的聲響。偶爾可以望見一隻帶有黃黑斑點的綠蝴蝶飛翔在一團白傘形狀的花叢上。時而從密密的樹叢中傳來一根樹枝折斷的聲音,樹葉撲簌簌地飄落的聲響,傳來野獸在樹林深處發出的吼聲,或是一隻母猴在斥責自己的小猴的聲音。
達薩聽到忘神,一時間忘記了去尋找蜂蜜,他呆望著幾隻羽毛絢爛正在婉轉啼鳴的小鳥,突然發現了在高高羊齒植物間或隱或現的一條小路,那片高大的羊齒植物叢好似大森林中一座茂密的小森林,而那條狹窄的羊腸小道僅能容下一人行走。達薩小心翼翼地循著小路前行,走到一棵枝繁葉茂的大榕樹下,樹下有一座茅草屋,一座用羊齒植物枝葉編織和搭起來的尖頂帳篷。茅草屋邊的地上坐著一個人,那人身體筆直,紋絲不動地端坐著,雙手安放在盤起的雙足之間。他頭髮雪白,額頭寬闊,一雙眼睛平靜而專注地注視著地面;他的雙眼雖然是睜開的,但對事物卻視而不見,他在關注自己的內心。達薩知道,眼前這位是聖人和瑜伽僧人,他先前也遇到過這樣的聖人,知道他們是受惠於神道的令人尊敬的長者,應當向他們表示敬畏。但是這位聖人把自己隱居的茅屋建構得如此美麗,他那靜靜下垂的雙臂,筆直端坐的禪定姿態,都強烈地吸引了這個孩子,讓這個男孩覺得這位長者比以前見過的任何聖人都更為奇妙和可敬。他端坐不動,卻又似乎懸浮在空中,他目光空靈,卻又好像穿透一切事物,一種神聖的光暈將他籠罩著,這是一種尊嚴的光圈,一種熊熊燃燒的火焰和瑜伽法力交融而成的光波,這種神奇的感覺鎮住了男孩,使這個小男孩無法穿越,也不敢發出一聲問候或者驚叫來驚擾。聖人的莊嚴法身,從內部發射出的光彩,使他即使靜坐不動也以他為中心放射出一道道光波和光線,就像從月亮上射出的光芒一般。而他的法身也以一種積蓄而成的巨大神力、一種凝聚積存的意志力量,在他四周編織起了一張巨大的法網,以至於達薩覺得:眼前這位聖人只要發一個願望或產生一個念頭,就能夠殺死一個人,或者重新救治這個人。
這位瑜伽行者一動不動,好似一棵樹,然而樹葉和枝條總還要隨風擺動,他卻像石雕的神像一般在自己的位置上紋絲不動,這使得這個小男孩一見到這個僧人便同中了魔法,被這幅景象深深地吸引住了,他入定般一動不動地站在原處。達薩就這樣呆呆地站著,目不轉睛地注視著這位大師,看著一抹陽光塗在他的肩上,一絲光線投在他垂落的臂上,又注視著這光線一點一點地游開,新的光線再度移入,達薩驚奇地看著,慢慢地看明白了,眼前的這位僧人對光影無動於衷,他對附近森林中鳥兒的鳴唱、猴兒的啼叫也同樣無動於衷,就連那隻停在他臉上,嗅過他的皮膚,在他的面頰上爬行了一小段又飛走的棕色大野蜂,他都絲毫未察覺,他對森林裡多姿多彩的生命全都無動於衷。達薩覺察到,這裡的一切,目光所及,耳力所及,無論是美是醜,無論是可愛還是可憎,全然與這位僧人毫無瓜葛。雨水不會讓他覺得寒冷或者沮喪,火焰無法讓他覺得灼傷,他周圍的整個世界對於他而言,都只不過是無足輕重的表相。
於是,那男孩隱隱地感覺到:實際上這整個世界或許也僅僅是一種無關緊要的遊戲和表相,也只不過是從不可知的深處吹來的一陣微風,深水表層的些許波瀾,這種感覺並不是以一種思想,而是以一種切實的身體戰慄和些許眩暈從這位正在凝神注視著的牧童小王子身上掠過,這是一種對恐懼和危險的感覺,而同時又伴隨著一種強烈的渴望。因為他切實覺得眼前的瑜伽行者已經突破了世界的表層,已經越過表相世界下到了一切存在的基礎,探入了萬事萬物的內在奧祕之中。他已破除了人類感官知覺的魔網,無眼鼻耳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牢牢地固守居留在自己的本質實體中了。達薩雖然曾經受過婆羅門教的薰陶,獲得過神光照射的恩惠,卻並沒有能力用理性智慧來理解這種感覺,更不知道如何用語言加以表述,但是他切實感覺到了,如同一個人在極樂的時刻總會感到神就在自己近旁一樣。如今他通過對這位僧人產生的敬畏戰慄而感受到了這種神性,通過對這位僧人的愛慕,通過渴望如這位僧人一般入定感受到了這種神性。達薩站在那裡,這個老人以某種奇異的方式讓他想起了自己的身世,憶起了高牆大院的王公生活,他暗自神傷,呆呆地佇立在那片羊齒植物小叢林的邊上,忘卻了掠過天空的小鳥,忘卻了身旁竊竊私語的樹木,更忘記了附近的森林和遠處的牛群。他沉浸在神奇的魔力中定睛凝視著靜修者,完全被對方不可思議的寂靜和無從接近的神態所折服,也為他臉上那種清澈澄明,形態上的從容內斂,以及全身心投入修行的狀態嘆服。
印度訪客
尚未成熟便摘下的果實對我們毫無用處。我的一生有一半以上的時間都在從事印度和中國研究——並非要謀取學者之名,不過是習慣於汲取印度及中國文學創作和虔誠的芬芳。十一年前我曾去印度旅行,在那裡,我看見了棕櫚樹和寺廟,聞到梵香和檀香的味道,吃過略帶酸澀的芒果和軟糯可口的香蕉。可是,在我與這一切之間還隔著一層薄紗,置身於康提的僧眾之間,我依然像先前在歐洲的時候一樣,無法遏制地渴望真正的印度,渴望印度精神,渴望跟它有一次生動活潑的接觸。印度精神還不屬於我,我還沒有找到它,我還在尋找。當時我也正是為此...
目錄
我與印度及中國的關係
懷念印度
中國人
印度訪客
對亞洲的回憶
對印度的回憶
凱澤林的旅行日記
異域藝術
東方文學的傑作
印度智慧
印度童話
日記選摘
印度之魂
印度教
直視遠東
短篇小說──
一位印度王的傳奇
新娘
羅伯特•阿吉翁
森林人
印度式生命軌跡
我與印度及中國的關係
懷念印度
中國人
印度訪客
對亞洲的回憶
對印度的回憶
凱澤林的旅行日記
異域藝術
東方文學的傑作
印度智慧
印度童話
日記選摘
印度之魂
印度教
直視遠東
短篇小說──
一位印度王的傳奇
新娘
羅伯特•阿吉翁
森林人
印度式生命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