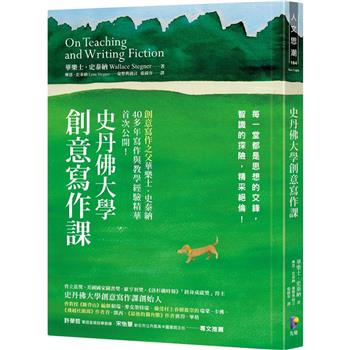本書從現代中國思想史的角度來審視胡適與林語堂,我們可以看到自由主義的兩個面向。且不問自由主義的定義究竟是什麼,胡適和林語堂在大方向上都是以爭取個人的獨立自主,反對獨裁暴力,提倡民主自由,容忍異己為其思想的主軸。
胡適所爭取的自由往往是就法律和政治制度而言,他透過學術研究,來說明自由民主是人類歷史發展的方向;而林語堂則常在所謂「精神或心靈的自由」上著墨,他試圖從文學和哲學的角度來論證自由快樂在人類生活中的價值,和生命中的意義。無論是「法律上的自由」還是「精神上的自由」,他們都堅信個人的自由和尊嚴,不能以「救國」「愛國」等名義,加以摧殘。
胡適和林語堂是現代中國思想史上自由主義的兩個代表人物,他們的思想對當今海峽兩岸都還有現實的意義。胡適的理性溫和固然是一個民主社會所必不可少的基本素質,而林語堂的幽默諷刺,為容忍與抗爭加進了潤滑劑,使容忍不致太不堪,而抗爭不致瀕於暴力。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自由的火種:胡適與林語堂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50 |
二手中文書 |
$ 316 |
台灣當代人物 |
$ 340 |
社會人文 |
$ 352 |
中文書 |
$ 352 |
Others |
$ 360 |
傳記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自由的火種:胡適與林語堂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周質平
1970年畢業於台北東吳大學中文系,1974年獲台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碩士學位,1982年獲美國印第安那大學中國文學博士。現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教授。研究晚明文學與中國近現代思想史。
中文著作:
《現代中國思潮與人物掠影》(台北:東吳大學,2015)
《現代人物與文化反思》(北京:九州,2013)
《光焰不熄—胡適思想與現代中國》(北京:九州,2012)
《胡適的情緣與晚境》(安徽:黃山書社,2008)
《現代人物與思潮》(台北:三民,2003)
《胡適與威廉斯:深情五十年》(台北:聯經,1998;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儒林新志》(台北:三民,1996)
《胡適叢論》(台北:三民,1992)
《公安派的文學批評及其發展》(台北:商務,1986)
編有:
《國史浮海開新錄:余英時教授榮退論文集》與Willard Peterson合編(台北:聯經,2002)
英文著作:
A Pragmatist and His Free Spirit (with Susan Egan)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2009)
Yuan Hung-tao and the Kung-an Schoo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
編有:
English Writings of Hu Shi,3 Vols.(ed.) (New York,London:Springer,2013)
A Collection of Hu Shih’s Unpublished English Essays and Speeches(ed.) (Taipei:Lianjing Publishing Co.,2001)
周質平
1970年畢業於台北東吳大學中文系,1974年獲台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碩士學位,1982年獲美國印第安那大學中國文學博士。現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教授。研究晚明文學與中國近現代思想史。
中文著作:
《現代中國思潮與人物掠影》(台北:東吳大學,2015)
《現代人物與文化反思》(北京:九州,2013)
《光焰不熄—胡適思想與現代中國》(北京:九州,2012)
《胡適的情緣與晚境》(安徽:黃山書社,2008)
《現代人物與思潮》(台北:三民,2003)
《胡適與威廉斯:深情五十年》(台北:聯經,1998;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儒林新志》(台北:三民,1996)
《胡適叢論》(台北:三民,1992)
《公安派的文學批評及其發展》(台北:商務,1986)
編有:
《國史浮海開新錄:余英時教授榮退論文集》與Willard Peterson合編(台北:聯經,2002)
英文著作:
A Pragmatist and His Free Spirit (with Susan Egan)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2009)
Yuan Hung-tao and the Kung-an Schoo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
編有:
English Writings of Hu Shi,3 Vols.(ed.) (New York,London:Springer,2013)
A Collection of Hu Shih’s Unpublished English Essays and Speeches(ed.) (Taipei:Lianjing Publishing Co.,2001)
目錄
序 吞聲的紀念:胡適與中國新文化運動研討會
胡適與林語堂
胡適的反共思想
林語堂的抗爭精神
張弛在自由與威權之間:胡適、林語堂與蔣介石
林語堂:在革命與懷舊之間
胡適、林語堂與傳記文學
林語堂與小品文
胡適英文筆下的中國文化
自由主義的薪傳:從胡適到余英時
胡適與吳敬恒
難進而易退:胡適的大使歲月
附錄 1:《胡適英文文存》成書經過
附錄 2:漢語教學史上的趙元任
胡適與林語堂
胡適的反共思想
林語堂的抗爭精神
張弛在自由與威權之間:胡適、林語堂與蔣介石
林語堂:在革命與懷舊之間
胡適、林語堂與傳記文學
林語堂與小品文
胡適英文筆下的中國文化
自由主義的薪傳:從胡適到余英時
胡適與吳敬恒
難進而易退:胡適的大使歲月
附錄 1:《胡適英文文存》成書經過
附錄 2:漢語教學史上的趙元任
序
吞聲的紀念:胡適與中國新文化運動研討會
2016年12月17日是胡適125歲生日紀念,北京大學歷史系主辦了一場為期兩天的「胡適與中國新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邀集了大陸,港臺及海外各地研究胡適和近現代中國思想史的專家學者六十人會聚一堂,來緬懷這位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開路人與奠基者。
回首1954年,這位被周揚定性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的最早的,最堅決的,最不可調和的敵人」,62年之後,居然又被請回了他所摯愛的北大,與會的學者都感到一定的欣慰。從1950年代初期的胡適思想批判,到七十年代晚期胡適研究的漸次開放,以至於今年在北大舉行研討會和「胡適與北大」的展覽。期間的進步是有目共睹的,這次讓胡適的「幽靈」回到北大,更有一定象徵的意義。
熱熱鬧鬧的研討會,設計精美的展覽不免給一般人一種錯覺,以為胡適思想已完全開放而胡適研究已無禁區和底線。但只要對胡適研究稍有涉獵的人一定都瞭解,胡適是近現代人物研究中,禁區最多,底線最高的一個人。這個禁區究竟是什麼?底線在哪裡?當道從來沒有明白的指出過。這條看似清楚,而實際模糊的底線,是碰觸不得的。正因為這條底線在顯隱之間,每個與會的人都小心翼翼地不去碰觸,結果在胡適研究的領域裡,形成了大家心照不宣的一種戒約:「反共」固然不能談,「批胡」也不宜提。在這兩大前提下,舉凡與共產黨官方歷史抵觸的大小事件都在刪禁之列。胡適對西安事變洞徹先機的分析及史達林策略之下,中共借抗戰之名,行坐大之實的歷史都從論文中消失得無影無蹤。
為了避免「尷尬」,誰都不提當年「不愉快」的舊事。在一片「和諧」的討論中,胡適思想密移暗度,所有的「違礙」都被剔除得乾乾淨淨。這種自覺或不自覺的「自我戒約」(self-imposed censorship)往往比有形的法令規章更為嚴格。表面上放言高論,而實際上吞聲自限。整個會場的氣氛,就像那兩天北京霧霾的紅色預警,迷茫之中帶著窒息,我們什麼時候才能看到藍天白雲?
1952年12月1日,胡適在臺北市編輯人協會歡迎會上說道:「要把自由看做空氣一樣的不可少」,這個比喻比「不自由毋寧死」更形象地說明自由在日常生活中,不可一時或缺的重要。但是一個長時生活在霧霾嚴重環境裡的人,對污染的忍受是很高的。只要我能呼吸,至於空氣新不新鮮,乾不乾淨,似乎無關緊要。對這樣的一個人來說,霧霾毋寧是「常態」,對藍天白雲則不敢奢望。我相信許多中國知識人覺得食有魚,住有房,出有車,對當前的生活充分的滿意,至於能不能批評當道,實在是很次要的事。就像籠中鳥,幾十年下來,已經失掉了翱翔的能力,而安於籠中的安逸了。胡適在同一天的講話上,還提到:
我說言論自由同一切自由一樣,都是要各人自己去爭取的。言論自由並不因為法律上有規定,或者憲法上有這一條文,就可以得來,就是有規定也是沒有用的。言論自由都是爭取來的。(《胡適言論集乙編》,臺北:自由中國社,1953,頁93-94)
1929年,國民黨的勢力如日中天,胡適在《新月》雜誌上發表了一系列激烈批評國民黨和孫中山的文字,而後與羅隆基,梁實秋等人的文章集印成《人權論集》,在序中他明白的指出:「我們所要建立的是批評國民黨的自由和批評孫中山的自由。上帝我們尚且可以批評,何況國民黨與孫中山?」今天,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發源地的北大紀念胡適,最值得我們緬懷效法的就是這個「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批評精神。
1959年,胡適發表《容忍與自由》,他的警句是「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這話當然顛撲不破,然而有了容忍,卻未必有自由。這也是不爭的事實。容忍而不能繼之以抗爭,這樣的容忍,則反為壓迫者所用。至於「容忍」二字,需分而論之,「容」是對異己的「包容」,是大度的體現;而「忍」則是「隱忍」,是強權之下,不得已的權宜。中國老百姓「忍」有餘,而「容」不足。而當道則「容」、「忍」兩缺。
中國大陸學術界的「自我戒約」,很容易讓人聯想到美國人所常說的「政治上的正確」(politicalcorrectness)。表面上,這兩者有相類似的地方,都是要求人說「得體」的話。但深一層推敲,則兩者約束之所自來,卻又截然不同。中國學界的自我戒約,是對當道「旨意」的揣摩和迎合,唯恐碰觸到那條無形的底線;動機是純「政治」的;而美國人所說的「政治上的正確」,其實和「政治」是不甚相關的。主要是對長久以來輿論所形成的一種是非,不敢輕犯其鋒。這兩者對言論自由都是一種妨礙,前者是有形的,而後者是無形的。
這次研討會結集了一本692頁的論文集,堪稱皇皇巨著,就像2003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胡適全集》,44冊的等身巨構竟無一篇胡適中英文反共的力作。用這樣一手遮天的笨拙手段來處理一位負國際重望的知名學者。套用一句胡適常說的話,真是「誣古人,誤今人」!
今天我們在中國大陸紀念胡適,其意義與其說是學術的,不如說是政治的。胡適的哲學史,文學史,禪宗史,小說考證,《水經注》考證都是開山的典範巨著,但畢竟時移境異,在有些領域,已經有了後出轉精的論著。換句話說,在學術上,胡適已經盡到了歷史的責任。唯獨他在民主,自由,人權上的堅持與追求,在中國大陸始終還沒有實現過。就整個言論自由的尺度而言,今天的大陸,還不及五四時期的北洋與三十年代的國民黨。
在當代中國史的分期上,最近有所謂「兩個三十年」的說法:1949-1979是第一個三十年,1979-2009是第二個三十年。對這兩個三十年的評價,見仁見智。但就現代中國思想史與學術史而言,1919-1949這三十年才是黃金時代。所有政治上的主義和學術上的論爭都在這三十年裡發生,成長。從白話文言的消長,到科學玄學的論爭,從世界語的推行到無政府主義的流行,以至於共產黨的成立,《古史辨》的出版,安陽的考古發掘。在文學上,則詩歌,小說,散文,戲劇的重要作品也都在這三十年裡出版,真有先秦「百家爭鳴」,大師輩出的氣象。
1949年,「天下一統」之後,繼之以規模大過於「始皇帝」千百倍的「焚書坑儒」,中國的知識界,一夜之間成了真正魯迅所說「無聲的中國」。最近幾年,在大陸有所謂「民國熱」,據我的推測,有不少是婉轉曲折的表示對後兩個三十年的失望,而對1919-1949這三十年的追懷。胡適領導的白話文運動曾使「無聲」的舊中國變為「有聲」,今天我們在大陸紀念胡適及《文學改良芻議》發表百年。我們希望新中國在言論上可以由「有禁」變到「無禁」。
我有幾位北京朋友將二三十年代舊雜誌的封面翻版,用綿紙集印在一起,取名《故紙溫暖》。我將這個小冊子握在手中,溫暖之中,也有無限的辛酸。想不到當年代表黑暗罪惡「舊中國」的民國,而今竟成了不少文化人「溫暖」的追憶了。所謂「學術無禁區」,至今是個未曾實現過的「中國夢」,這句「口頭禪」帶給人的聯想絕不是「言論自由」,而是「引蛇出洞」,是六十年前那場讓千千萬萬中國人家破人亡的「反右」噩夢。
會場上,有幸結識一位84歲高齡,當年被打成右派的北大哲學教授。他在論文及著作中極力推崇蔡元培,胡適兼容並包,學術獨立的辦學理念。對自己二十幾年非人的遭遇,則輕描淡寫,一筆帶過。我對他的敬意,油然而生。我看到的不止是一個個人的悲慘境遇,而是幾代中國知識份子九死一生,輾轉溝壑的歷歷在目。一個有人味的社會,是允許人有不做烈士的自由的。在這樣的言論環境裡,我們何忍再以氣節相責!
在研討會上,有一位中央黨校的老師發表《胡適與國民黨的黨化教育》一文,在口頭報告時,他煞費苦心的想為國民黨的黨化教育略做辯護:黨化教育並非一無是處,至少「漲了工資」。我心想:今天共產黨的黨化教育不但漲了工資,還給了汽車洋房,豈是當年國民黨所能相提並論?金錢固然買不到陳寅恪所標榜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但獨立和自由卻往往可以為汽車洋房所出賣。不久前,當今知名的學者作家競以手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示忠誠,就是黨化教育並非「一無是處」最好的說明。
1931年,梅貽琦在清華大學校長就職演說中說:「所謂『大學』者,非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近二十年來,校園裡,「大樓」林立,而獨無「大師」,「大學」云乎哉?大師所需要的是自由的學術環境,沒有學術上的自由,何來大師?
五四前後的北大是全國風氣的引領者,新文學,新思想皆自北大來。而今北大是「上意」的迎合者,從「引領」到「迎合」,道盡二十世紀中國知識人的滄桑!
復旦大學特聘教授,中國發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張維為在2014年作過一次《中國人,你要自信》的演講,在網上流傳。其實,需要有信心的並不是集體的「中國人」,而是共產黨。如果,中國,真的如張維為所說,已經是一個舉足輕重的大國,強國。那麼執政黨就應該對現有的制度充滿信心,幾個學者的發言或文章是不足以撼動社會穩定和執政黨的名聲的。所有的言論審查制度,都緣於「槍桿子」怕「筆桿子」,因此,言論的禁忌越多,槍桿子就越顯得「外強中乾」。
八年前,2008年12月17日,由北京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與安徽績溪縣政府在績溪徽商賓館舉辦了一個紀念胡適117周年冥誕的小型學術研討會,與會的三十幾位胡適思想的研究者和愛好者一致認為,現在是為胡適正式平反的時候了。績溪縣政府並倡議,在胡適的家鄉成立胡適紀念館,這對許多與會的人而言,自然是件值得欣慰的事。但在我,卻還是不無擔憂的。
立銅像,建紀念館當然是對死者的崇敬,但紀念館所展現出來的那個人,到底有幾分是他的本來面目,就很值得商榷了。就如同2003年出版的《胡適全集》,只要對胡適著作稍有瞭解的人都能看出:《全集》不全。《全集》之所以不全,如果是因為有遺文軼稿散落人間,無從搜求,這自然只有從缺,但《胡適全集》之所以不全,原因全不在此,而是出於編選者的「苦心」,對胡適思想中有所「違礙」的地方,進行梳理,篩選,所有1949年以後,反共的文字,無論中英文,一概在「禁毀」之列。結果,從《胡適全集》來看胡適,一個以反共名世的思想家,反共這一點,幾乎不見蹤影!
講胡適思想而不提反共,猶如講毛澤東思想而不提「階級鬥爭」,講鄧小平理論而不提「改革開放」,都忽略了關鍵和精華之所在。這豈不成了胡適在《自由主義是什麼》一文中所說的,「長阪坡裡沒有趙子龍,空城計裡沒有諸葛亮」,這齣戲就唱得有些荒腔走板了。
我擔心,一旦胡適紀念館成立,呈現在參觀者面前的胡適是個遠比《全集》取樣更小,尺度更嚴的胡適。這樣的胡適,容貌或許依舊,而精神全失。從這個角度來看,胡適紀念館在中國大陸至今全無蹤影,也未必是件壞事。立銅像,建紀念館多少帶點偶像化的意味,但偶像和傀儡之間往往只是一線之隔。
1926年,亦即魯迅死前十年,他即有此了悟,在《無花的薔薇》中,他指出:「待到偉大的人物成為化石,人們都稱他偉人時,他已經變了傀儡了。」然而,魯迅自己卻防止不了被「傀儡化」的過程。在這一點上,胡適比魯迅幸運得多。
1937年,毛澤東在延安陝北公學紀念魯迅逝世周年大會上講話,發表《論魯迅》一文,評價魯迅為「中國的第一等聖人」,與孔子相提並論,孔子是「封建社會的聖人」,而魯迅則是「現代中國的聖人」。(《毛澤東文集》北京:人民,1993,卷2,頁43。)並在延安成立了魯迅圖書館,開辦了魯迅師範學校。這是毛澤東計畫用魯迅來為共產黨作為「打手」的第一步。1940年1月,毛發表《新民主主義論》,正式給了魯迅「三家五最」的「諡號」,「三家」即「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五最」即「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從此魯迅走進了神龕。1942年5月,毛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魯迅成了「一切共產黨員,一切革命家,一切的文藝工作者」學習的榜樣了,這時,神龕中的魯迅表面上是頂禮膜拜的對象,而實際上,則成了共產黨手中的一個傀儡了。
反觀胡適,不但全集不全,紀念館在大陸不見蹤影,五四紀念碑上沒有他的浮雕,北大也沒有他的銅像,但是,這點身後的蕭條與冷落,正是魯迅所不可及處,也是胡適獨立自主最好的說明。
至於為胡適平反,眼下是「民逼官反」,是廣大的學術界要求當道為當年的冤案,錯案給以重新的審視。其實,胡適蓋棺已五十五年,平反與否,對死者已無任何意義,胡適的歷史地位,也不會因平反與否而有所增減。倒是當道在這個「辨冤白謗」的過程中,若真能體現知錯改錯的勇氣和魄力,是可以為自身的合法性增加一塊可觀的砝碼的。換句話說,為胡適這樣一個標誌性的人物作出正式的平反,受益的不是死者,而是當年判他有罪的當道。
《胡適全集》之不能全,胡適思想至今有所違礙,正是胡適不曾過時最好的說明,等到胡適那些民主自由的主張在中國全無違礙,成了稀鬆平常的常識的那一天,也就是胡適思想過時的時候了。我們盼著這一天很快的到來。
胡適和林語堂是現代中國思想史上自由主義的兩個代表人物,他們的思想對當今海峽兩岸都還有現實的意義。胡適的理性溫和固然是一個民主社會所必不可少的基本素質,而林語堂的幽默諷刺,為容忍與抗爭加進了潤滑劑,使容忍不致太不堪,而抗爭不致瀕於暴力。我將過去幾年來圍繞著胡適和林語堂思想研究文字集印成冊,正是希望這兩位上世紀自由主義的典型,還能為海峽兩岸發展成為一個祥和樂利,多樣並存的社會起到一些引領的作用。
本書能夠在台灣出版要特別感謝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王汎森兄的推介,和允晨出版公司廖志峰先生的支持。謹此深致謝忱。
2016年12月17日是胡適125歲生日紀念,北京大學歷史系主辦了一場為期兩天的「胡適與中國新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邀集了大陸,港臺及海外各地研究胡適和近現代中國思想史的專家學者六十人會聚一堂,來緬懷這位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開路人與奠基者。
回首1954年,這位被周揚定性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的最早的,最堅決的,最不可調和的敵人」,62年之後,居然又被請回了他所摯愛的北大,與會的學者都感到一定的欣慰。從1950年代初期的胡適思想批判,到七十年代晚期胡適研究的漸次開放,以至於今年在北大舉行研討會和「胡適與北大」的展覽。期間的進步是有目共睹的,這次讓胡適的「幽靈」回到北大,更有一定象徵的意義。
熱熱鬧鬧的研討會,設計精美的展覽不免給一般人一種錯覺,以為胡適思想已完全開放而胡適研究已無禁區和底線。但只要對胡適研究稍有涉獵的人一定都瞭解,胡適是近現代人物研究中,禁區最多,底線最高的一個人。這個禁區究竟是什麼?底線在哪裡?當道從來沒有明白的指出過。這條看似清楚,而實際模糊的底線,是碰觸不得的。正因為這條底線在顯隱之間,每個與會的人都小心翼翼地不去碰觸,結果在胡適研究的領域裡,形成了大家心照不宣的一種戒約:「反共」固然不能談,「批胡」也不宜提。在這兩大前提下,舉凡與共產黨官方歷史抵觸的大小事件都在刪禁之列。胡適對西安事變洞徹先機的分析及史達林策略之下,中共借抗戰之名,行坐大之實的歷史都從論文中消失得無影無蹤。
為了避免「尷尬」,誰都不提當年「不愉快」的舊事。在一片「和諧」的討論中,胡適思想密移暗度,所有的「違礙」都被剔除得乾乾淨淨。這種自覺或不自覺的「自我戒約」(self-imposed censorship)往往比有形的法令規章更為嚴格。表面上放言高論,而實際上吞聲自限。整個會場的氣氛,就像那兩天北京霧霾的紅色預警,迷茫之中帶著窒息,我們什麼時候才能看到藍天白雲?
1952年12月1日,胡適在臺北市編輯人協會歡迎會上說道:「要把自由看做空氣一樣的不可少」,這個比喻比「不自由毋寧死」更形象地說明自由在日常生活中,不可一時或缺的重要。但是一個長時生活在霧霾嚴重環境裡的人,對污染的忍受是很高的。只要我能呼吸,至於空氣新不新鮮,乾不乾淨,似乎無關緊要。對這樣的一個人來說,霧霾毋寧是「常態」,對藍天白雲則不敢奢望。我相信許多中國知識人覺得食有魚,住有房,出有車,對當前的生活充分的滿意,至於能不能批評當道,實在是很次要的事。就像籠中鳥,幾十年下來,已經失掉了翱翔的能力,而安於籠中的安逸了。胡適在同一天的講話上,還提到:
我說言論自由同一切自由一樣,都是要各人自己去爭取的。言論自由並不因為法律上有規定,或者憲法上有這一條文,就可以得來,就是有規定也是沒有用的。言論自由都是爭取來的。(《胡適言論集乙編》,臺北:自由中國社,1953,頁93-94)
1929年,國民黨的勢力如日中天,胡適在《新月》雜誌上發表了一系列激烈批評國民黨和孫中山的文字,而後與羅隆基,梁實秋等人的文章集印成《人權論集》,在序中他明白的指出:「我們所要建立的是批評國民黨的自由和批評孫中山的自由。上帝我們尚且可以批評,何況國民黨與孫中山?」今天,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發源地的北大紀念胡適,最值得我們緬懷效法的就是這個「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批評精神。
1959年,胡適發表《容忍與自由》,他的警句是「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這話當然顛撲不破,然而有了容忍,卻未必有自由。這也是不爭的事實。容忍而不能繼之以抗爭,這樣的容忍,則反為壓迫者所用。至於「容忍」二字,需分而論之,「容」是對異己的「包容」,是大度的體現;而「忍」則是「隱忍」,是強權之下,不得已的權宜。中國老百姓「忍」有餘,而「容」不足。而當道則「容」、「忍」兩缺。
中國大陸學術界的「自我戒約」,很容易讓人聯想到美國人所常說的「政治上的正確」(politicalcorrectness)。表面上,這兩者有相類似的地方,都是要求人說「得體」的話。但深一層推敲,則兩者約束之所自來,卻又截然不同。中國學界的自我戒約,是對當道「旨意」的揣摩和迎合,唯恐碰觸到那條無形的底線;動機是純「政治」的;而美國人所說的「政治上的正確」,其實和「政治」是不甚相關的。主要是對長久以來輿論所形成的一種是非,不敢輕犯其鋒。這兩者對言論自由都是一種妨礙,前者是有形的,而後者是無形的。
這次研討會結集了一本692頁的論文集,堪稱皇皇巨著,就像2003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胡適全集》,44冊的等身巨構竟無一篇胡適中英文反共的力作。用這樣一手遮天的笨拙手段來處理一位負國際重望的知名學者。套用一句胡適常說的話,真是「誣古人,誤今人」!
今天我們在中國大陸紀念胡適,其意義與其說是學術的,不如說是政治的。胡適的哲學史,文學史,禪宗史,小說考證,《水經注》考證都是開山的典範巨著,但畢竟時移境異,在有些領域,已經有了後出轉精的論著。換句話說,在學術上,胡適已經盡到了歷史的責任。唯獨他在民主,自由,人權上的堅持與追求,在中國大陸始終還沒有實現過。就整個言論自由的尺度而言,今天的大陸,還不及五四時期的北洋與三十年代的國民黨。
在當代中國史的分期上,最近有所謂「兩個三十年」的說法:1949-1979是第一個三十年,1979-2009是第二個三十年。對這兩個三十年的評價,見仁見智。但就現代中國思想史與學術史而言,1919-1949這三十年才是黃金時代。所有政治上的主義和學術上的論爭都在這三十年裡發生,成長。從白話文言的消長,到科學玄學的論爭,從世界語的推行到無政府主義的流行,以至於共產黨的成立,《古史辨》的出版,安陽的考古發掘。在文學上,則詩歌,小說,散文,戲劇的重要作品也都在這三十年裡出版,真有先秦「百家爭鳴」,大師輩出的氣象。
1949年,「天下一統」之後,繼之以規模大過於「始皇帝」千百倍的「焚書坑儒」,中國的知識界,一夜之間成了真正魯迅所說「無聲的中國」。最近幾年,在大陸有所謂「民國熱」,據我的推測,有不少是婉轉曲折的表示對後兩個三十年的失望,而對1919-1949這三十年的追懷。胡適領導的白話文運動曾使「無聲」的舊中國變為「有聲」,今天我們在大陸紀念胡適及《文學改良芻議》發表百年。我們希望新中國在言論上可以由「有禁」變到「無禁」。
我有幾位北京朋友將二三十年代舊雜誌的封面翻版,用綿紙集印在一起,取名《故紙溫暖》。我將這個小冊子握在手中,溫暖之中,也有無限的辛酸。想不到當年代表黑暗罪惡「舊中國」的民國,而今竟成了不少文化人「溫暖」的追憶了。所謂「學術無禁區」,至今是個未曾實現過的「中國夢」,這句「口頭禪」帶給人的聯想絕不是「言論自由」,而是「引蛇出洞」,是六十年前那場讓千千萬萬中國人家破人亡的「反右」噩夢。
會場上,有幸結識一位84歲高齡,當年被打成右派的北大哲學教授。他在論文及著作中極力推崇蔡元培,胡適兼容並包,學術獨立的辦學理念。對自己二十幾年非人的遭遇,則輕描淡寫,一筆帶過。我對他的敬意,油然而生。我看到的不止是一個個人的悲慘境遇,而是幾代中國知識份子九死一生,輾轉溝壑的歷歷在目。一個有人味的社會,是允許人有不做烈士的自由的。在這樣的言論環境裡,我們何忍再以氣節相責!
在研討會上,有一位中央黨校的老師發表《胡適與國民黨的黨化教育》一文,在口頭報告時,他煞費苦心的想為國民黨的黨化教育略做辯護:黨化教育並非一無是處,至少「漲了工資」。我心想:今天共產黨的黨化教育不但漲了工資,還給了汽車洋房,豈是當年國民黨所能相提並論?金錢固然買不到陳寅恪所標榜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但獨立和自由卻往往可以為汽車洋房所出賣。不久前,當今知名的學者作家競以手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示忠誠,就是黨化教育並非「一無是處」最好的說明。
1931年,梅貽琦在清華大學校長就職演說中說:「所謂『大學』者,非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近二十年來,校園裡,「大樓」林立,而獨無「大師」,「大學」云乎哉?大師所需要的是自由的學術環境,沒有學術上的自由,何來大師?
五四前後的北大是全國風氣的引領者,新文學,新思想皆自北大來。而今北大是「上意」的迎合者,從「引領」到「迎合」,道盡二十世紀中國知識人的滄桑!
復旦大學特聘教授,中國發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張維為在2014年作過一次《中國人,你要自信》的演講,在網上流傳。其實,需要有信心的並不是集體的「中國人」,而是共產黨。如果,中國,真的如張維為所說,已經是一個舉足輕重的大國,強國。那麼執政黨就應該對現有的制度充滿信心,幾個學者的發言或文章是不足以撼動社會穩定和執政黨的名聲的。所有的言論審查制度,都緣於「槍桿子」怕「筆桿子」,因此,言論的禁忌越多,槍桿子就越顯得「外強中乾」。
八年前,2008年12月17日,由北京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與安徽績溪縣政府在績溪徽商賓館舉辦了一個紀念胡適117周年冥誕的小型學術研討會,與會的三十幾位胡適思想的研究者和愛好者一致認為,現在是為胡適正式平反的時候了。績溪縣政府並倡議,在胡適的家鄉成立胡適紀念館,這對許多與會的人而言,自然是件值得欣慰的事。但在我,卻還是不無擔憂的。
立銅像,建紀念館當然是對死者的崇敬,但紀念館所展現出來的那個人,到底有幾分是他的本來面目,就很值得商榷了。就如同2003年出版的《胡適全集》,只要對胡適著作稍有瞭解的人都能看出:《全集》不全。《全集》之所以不全,如果是因為有遺文軼稿散落人間,無從搜求,這自然只有從缺,但《胡適全集》之所以不全,原因全不在此,而是出於編選者的「苦心」,對胡適思想中有所「違礙」的地方,進行梳理,篩選,所有1949年以後,反共的文字,無論中英文,一概在「禁毀」之列。結果,從《胡適全集》來看胡適,一個以反共名世的思想家,反共這一點,幾乎不見蹤影!
講胡適思想而不提反共,猶如講毛澤東思想而不提「階級鬥爭」,講鄧小平理論而不提「改革開放」,都忽略了關鍵和精華之所在。這豈不成了胡適在《自由主義是什麼》一文中所說的,「長阪坡裡沒有趙子龍,空城計裡沒有諸葛亮」,這齣戲就唱得有些荒腔走板了。
我擔心,一旦胡適紀念館成立,呈現在參觀者面前的胡適是個遠比《全集》取樣更小,尺度更嚴的胡適。這樣的胡適,容貌或許依舊,而精神全失。從這個角度來看,胡適紀念館在中國大陸至今全無蹤影,也未必是件壞事。立銅像,建紀念館多少帶點偶像化的意味,但偶像和傀儡之間往往只是一線之隔。
1926年,亦即魯迅死前十年,他即有此了悟,在《無花的薔薇》中,他指出:「待到偉大的人物成為化石,人們都稱他偉人時,他已經變了傀儡了。」然而,魯迅自己卻防止不了被「傀儡化」的過程。在這一點上,胡適比魯迅幸運得多。
1937年,毛澤東在延安陝北公學紀念魯迅逝世周年大會上講話,發表《論魯迅》一文,評價魯迅為「中國的第一等聖人」,與孔子相提並論,孔子是「封建社會的聖人」,而魯迅則是「現代中國的聖人」。(《毛澤東文集》北京:人民,1993,卷2,頁43。)並在延安成立了魯迅圖書館,開辦了魯迅師範學校。這是毛澤東計畫用魯迅來為共產黨作為「打手」的第一步。1940年1月,毛發表《新民主主義論》,正式給了魯迅「三家五最」的「諡號」,「三家」即「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五最」即「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從此魯迅走進了神龕。1942年5月,毛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魯迅成了「一切共產黨員,一切革命家,一切的文藝工作者」學習的榜樣了,這時,神龕中的魯迅表面上是頂禮膜拜的對象,而實際上,則成了共產黨手中的一個傀儡了。
反觀胡適,不但全集不全,紀念館在大陸不見蹤影,五四紀念碑上沒有他的浮雕,北大也沒有他的銅像,但是,這點身後的蕭條與冷落,正是魯迅所不可及處,也是胡適獨立自主最好的說明。
至於為胡適平反,眼下是「民逼官反」,是廣大的學術界要求當道為當年的冤案,錯案給以重新的審視。其實,胡適蓋棺已五十五年,平反與否,對死者已無任何意義,胡適的歷史地位,也不會因平反與否而有所增減。倒是當道在這個「辨冤白謗」的過程中,若真能體現知錯改錯的勇氣和魄力,是可以為自身的合法性增加一塊可觀的砝碼的。換句話說,為胡適這樣一個標誌性的人物作出正式的平反,受益的不是死者,而是當年判他有罪的當道。
《胡適全集》之不能全,胡適思想至今有所違礙,正是胡適不曾過時最好的說明,等到胡適那些民主自由的主張在中國全無違礙,成了稀鬆平常的常識的那一天,也就是胡適思想過時的時候了。我們盼著這一天很快的到來。
胡適和林語堂是現代中國思想史上自由主義的兩個代表人物,他們的思想對當今海峽兩岸都還有現實的意義。胡適的理性溫和固然是一個民主社會所必不可少的基本素質,而林語堂的幽默諷刺,為容忍與抗爭加進了潤滑劑,使容忍不致太不堪,而抗爭不致瀕於暴力。我將過去幾年來圍繞著胡適和林語堂思想研究文字集印成冊,正是希望這兩位上世紀自由主義的典型,還能為海峽兩岸發展成為一個祥和樂利,多樣並存的社會起到一些引領的作用。
本書能夠在台灣出版要特別感謝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王汎森兄的推介,和允晨出版公司廖志峰先生的支持。謹此深致謝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