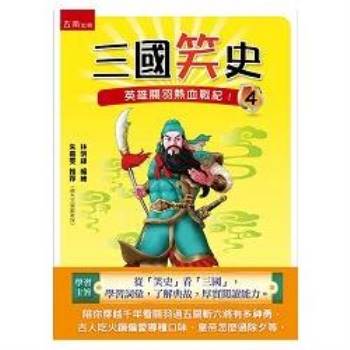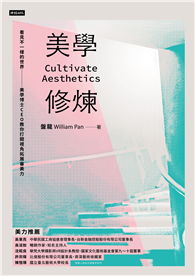一部荒誕的、中國式公路電影似的小說,
戲謔的筆法讓現實與過去、真實和超現實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不清。——明鏡周刊二○一二年法蘭克福書業和平獎得主廖亦武又一撼世鉅作,「時代三部曲」的最終曲,佳評如潮,明鏡週刊、德意志電台、法蘭克福匯報、世界日報……等各大媒體,熱烈推薦。
問:在《輪迴的螞蟻》中,有一個老和尚教你怎麼吹簫。吹簫改變了你的生活嗎?
答:世界是一個大監獄,如果你內心不自由,就永遠找不到自由,這是老和尚說的。
我在吹簫中回憶過去,我的確被改變了。我也希望我在天上的朋友劉曉波看到我的改變。看到我在為他的妻子劉霞的自由而努力。我知道如果不努力,她會死在國內,我也會永遠愧疚,追悔,那麼,得到的自由也將轉瞬失去。總之,為他人的尊嚴和自由而奮戰,自己也將獲得尊嚴和自由。——新奧斯納布呂克日報
《輪迴的螞蟻》講述了作者從前的自我。它把老威的虛構故事和中國的大歷史交織在一塊,發展為一部荒誕的、中國式公路電影似的小說,戲謔的筆法讓現實與過去、真實和超現實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不清。它充滿極其高超的幽默,而老威在當中扮演了一個妙不可言的反英雄。——明鏡周刊
獄中歲月依舊是這部小說的枝幹之一。小說的創作始於作者服刑中的 1992 年。今年 58 歲的他,在前言中描述怎樣偷偷把螞蟻大小的字跡填滿破爛不堪的紙片,以此在內心深處重建剝奪不去的尊嚴和自由—這讓他的靈肉挺過家常便飯似的虐待和酷刑,地獄之旅成為這部書的出發點—在身體不能走的時候,心也要不斷向前,只有心自由了,遙遠的風中回聲才將撲面而來,飛舞的亡靈也將撲面而來。如果把這部跌宕起伏又哲思深沉的傑作簡化成一個便於評論的文學標籤,就太可惜了。作者高超的敘事技巧讓人驚嘆不已,從毫無掩飾的直白到極其晦暗的嘲諷,在這部書裡你能見識各種迥異的講述風格,隨處橫溢的非凡想像讓人不得不折服。它往往漫不經心地將讀者帶上意料不到的旅程:奇幻的、荒誕的、甚至是惡作劇的,每一場景都充滿幽默、戲謔和極端放肆。——德意志電台
諷刺,激烈,甚至咆哮不已,直到最後的螞蟻上山的盡頭之歌—夾雜在這些險象橫生的畫面中的,是直白露骨的性描寫,這在遠東文學中,比在西方文學中要常見得多。廖亦武在小說裏的扭曲處理,反而讓我們更容易認清中國人壓抑的本質。——法蘭克福匯報
作者簡介:
廖亦武,1958年生於四川鹽亭,因在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凌晨寫作並朗誦著名長詩《大屠殺》,以及組織拍攝詩歌電影《安魂》而被捕,判刑四年,受盡折磨,曾在獄中自殺兩次。刑滿後多次化名出版《沉淪的聖殿》、《中國底層訪談錄》等書,成為中國第一禁書作家。
2007年,紐約的文學經紀人彼得.伯恩斯坦在《巴黎評論》看到黃文翻譯的《中國底層訪談錄》片段後,取得該書英文版權,並從此成為廖亦武作品經紀人。
2008年5月該書英文版The Corpse Walker: Real Life Stories: China From the Bottom Up出版,讓地下作家廖亦武在海外一夜成名。可在中國,他的言行依然受到嚴格封殺,曾17次被禁止出國。2011年7月,因準備在美國和德國出版《上帝是紅色的》和《六四:我的證詞》,受到警方再次判刑坐牢的威脅,不得不買通黑社會,輾轉越南逃亡德國。流亡後的廖亦武,在英、法、德、西、葡、義等三十多個國家都有多種著作出版,特別在德國及法國,以一年一本的速度出版有《六四:我的證詞》、《子彈鴉片》、《洞洞舞女和川菜廚子》、《上帝是紅色的》、《這個帝國必須分裂》、《毛時代的愛情》、《鄧時代的地下詩人》,並獲得德國書業和平獎、雪爾兄妹獎、卡普欽斯基國際報導文學獎、法國抵抗詩人奬等十多個重要獎項。在伯恩斯坦看來,廖亦武不僅是有作品被翻譯成多種外語的中國當代作家中最優秀、最具挑戰性和創新的一位,更是一位勇敢大膽的有著獨立意志的人,任何時候都會捍衛自己自由言論和自由思考的權利(Liao is not only a fine writer but a courageous and brave and individual willing to stand up at every turn for his right to speak and think freely)。
章節試閱
卷一 獄中手稿
痲瘋病想念毛主席
歷史是什麼?按照學院派學者的觀點,歷史就是書籍,記載正史和野史的書籍。在書籍之外,考古學家不斷發現、挖掘古蹟,尋找補充、論證、糾正書籍的實物。書籍給人一種永恆的幻覺,所以歷朝歷代的統治者治國的頭等大事就是把文化置於權力的籠罩下,歷史上為寫書而殺頭坐牢的人太多了,僅僅被掐掉卵蛋的《史記》作者司馬遷應該感到幸福。老威在短暫的人生中,經常看到一本黨史,一本國史,一本教科書隨當權者的更替而不斷塗抹修改,作為詩人,他相信在書籍之外,有一種傳統悄悄持續著,藉助於人類的繁衍和想像。
在烏江上游,有一個村落叫頭渡,老威偶然聽父親講那是自己的祖陵所在地,就決意去尋根。他拿出一本最詳細的川東地形圖,查來查去沒結果,只好寫信約當地詩人茍明軍一道結伴出發。公元1986年某月某日,二人從長江和烏江的交匯碼頭溯流而上,客船半夜啟航,老威一覺醒來已是翌日早晨。江面狹窄,波濤湍急,有時小火輪掙扎怒吼了老半天卻前進不了幾寸,兩岸奇峰陡立,凌空的怪石刺激著老威的想像。三五成群的農民在這些怪石間攀援,播種,如自然之書上的活動漢字。茍明軍解釋道,那是蠻王的後裔,習俗與漢人截然不同,他們相信人死之後,將回到祖先那兒,而每個新生兒都是遠古祖先的化身。
在一個叫蠻王洞的簡陋碼頭下船,時已深秋,卻有幾個光屁股小孩目不轉睛地瞪著他倆,臉相如紫色泥巴捏成的面具。離碼頭不遠的臨江巖洞裡,黑黝黝地塑著一個肚臍眼巨大的土偶,據說那就是蠻王,巴人的始祖。春秋末期,強秦滅掉蜀國和巴國,巴國王在臨終叮囑自己的五個兒子溯烏江而上,與當地土族雜居以逃避秦兵的追擊,五人中有四人先後被害,只有最小的孩子在土族的掩護下,苟延殘喘,保留了種。類似的傳說在民間越傳越多,形成了與官方文化格格不入的、帶著濃厚巫術色彩的口頭文化。那些民間藝人歌唱著、行吟著、加工著、想像著,並將記憶中的作品傳給下一代,讓他們永世不忘戰敗者的輓歌。
長江以南的大部份地區地形複雜,多雨多愁,瘴氣瀰漫,從神話傳說中的蚩尤大戰黃帝開始,烏江等流域就是歷代戰敗者擦洗創傷的地方。國家需要一種理性和秩序,儘管有時理性和秩序出於瘋子之手。而南方巫術是直覺的,本能的,感性的,它不加選擇地反抗所有的秩序,世世代代的慘敗已深入骨髓,在那些民間歌者原始的喉管裡,祖先或個人的某次悲劇被無限擴張,成為整個人類註定的結局。〈招魂歌〉裡無魂可招又不得不招魂的夢囈與老威的精神處境相同。
老威學當地人的樣子向蠻王進了一炷香,校準指南針,然後進入暗無天日的原始森林。在寂靜中不知走了多久,當腿肚子感到痠脹時,他們迷路了。為了抑制莫名的煩躁,老威唱起了〈世界的末日〉:
為什麼海浪要拍打沙灘?
為什麼鳥兒在枝頭啁啾?
它們不知道這是世界的末日。
為什麼陽光像星光一般寒冷?
為什麼老威在森林中迷路?
因為不知道世界的末日。
為什麼……
他喜歡隨著興趣編造歌詞,順著一個好聽的曲調一直唱,唱個夠。茍明軍卻始終在前面一聲不吭地走,光著膀子,耐力非常好。就這樣他們走了兩天兩夜或者三天三夜,在支撐不住的時候,無意中撞入了密林深處的一個痲瘋病院。這個活墳墓是他們的天堂,他們冒充記者宿了一夜,免費補充食物和水,重新校正了指南針。正要重新上路,高牆內突然掀起陣陣怪誕的喧譁。老威瞅見一個爛掉半邊鼻子的傢伙在鐵窗裡一閃,旋即大叫:「快來呀,毛主席派人看我們來了!毛主席,我們日夜盼望您!」老威一楞,納悶竟有如此閉塞的精神病院。高牆內又爆起震天的狂吼:「我們要見毛主席的人!我們要告狀!」「工作組的同志! 他們整得我好慘喲!」老威還沒反應過來,茍明軍卻先笑了,現在是公元 1986 年,黨的領導人已換過好幾屆了。
管理人員為安定人心,索性將計就計,懇求二人假戲真做,但按規定不準拍照、錄音和記錄。老威雖然內心發毛,然而已受人恩惠,只好換上院方提供的中山裝和藍色工作帽,挺胸凹腹,進入痲瘋患者聚居的內院。崗哨森嚴,滿目腐朽,一大群缺鼻少嘴爛耳朵或從頭潰敗到腳的怪物蜂擁而來,將他們包圍。好在這些病人自慚形穢,都在安全距離外跪下。幾十雙舉著《控告信》的手伸過來,老威草草瀏覽,內容大同小異,都是向心中的紅太陽傾訴自己的不幸遭遇。接著二人在管理人員的嚴密監護下,被帶入惡臭充溢的病員監室,一個已成骷髏的臨終老人正用迴光返照的安詳微笑迎接他。他走過去,老人知趣地縮回手。老威憐憫地望著這個缺少頭髮和臉皮的怪物,兩朵黯火從那眉骨下顫跳出來,管理人員俯下身子輕輕道:「老王,毛主席派人看你了。」老威此時也進入角色,點頭道:「主席關心你們哩,他從北京中南海特地派我來。」
兩顆濁淚淌下模糊的眼洞,而更加模糊的嘴洞擠出「毛主席」三個字。這情景令老威聯想到童年學過的某篇二戰課文,一個八路軍戰士在保衛延安的戰鬥中身負重傷,生命垂危之際,向護士吐露了平生最大的祕密願望,見毛主席。恰好毛主席知道了,連夜騎馬趕到,大汗淋漓地出現在病床前,接受了彌留者的臨終禮拜。戰士握住那柔若無骨的肥手,像童話中的小男孩,叫著偶像的名字,無比快活地升天了。
老威作為紅太陽的欽差大臣圓滿完成院方的任務,並且同痲瘋病人們一起照了相,當然照片和大疊情感濃烈的信件永遠交不到紅太陽那兒。不同的時間、地點,由不同的人物上演的相同的獨幕劇使他顫慄,幸好時光沒有倒流,眼下是 1986年10月10日,星期三,中國正在醞釀一場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明年或後年的今天,蘇聯是否會來一次政權更替?天安門廣場是否會變成一座鐵血兵營?「尼采宣告上帝死了,」老威喃喃道,「可支配一切的,依舊是不叫上帝的上帝。」
末日場景歷歷在目,老威反而什麼歌也唱不了,難道聲音也同文字一般不可靠?
卷一 獄中手稿
痲瘋病想念毛主席
歷史是什麼?按照學院派學者的觀點,歷史就是書籍,記載正史和野史的書籍。在書籍之外,考古學家不斷發現、挖掘古蹟,尋找補充、論證、糾正書籍的實物。書籍給人一種永恆的幻覺,所以歷朝歷代的統治者治國的頭等大事就是把文化置於權力的籠罩下,歷史上為寫書而殺頭坐牢的人太多了,僅僅被掐掉卵蛋的《史記》作者司馬遷應該感到幸福。老威在短暫的人生中,經常看到一本黨史,一本國史,一本教科書隨當權者的更替而不斷塗抹修改,作為詩人,他相信在書籍之外,有一種傳統悄悄持續著,藉助於人類的繁衍和...
推薦序
推薦序一
明鏡周刊:「好作家應該坐過牢」
作者:Maximilian Kalkhof ,中譯:王培根
2016年10月3日,星期一
他是中國歷史的記錄者:2011年流亡德國至今,在這裡非常出名。現在這位書業和平獎得主出版了第一部長篇小說。我們在柏林採訪了他。
問一個在德國公認的「異議詩人」覺得自己是不是「異議人士」—這問題太可笑?還是太愚蠢?
柏林夏洛特公主城堡附近,廖亦武坐在自家露臺上,他品著一杯四川花茶,九月的陽光刺得他直眨眼睛。他女兒不時在身邊出沒,她叫「小螞蟻」,還不滿兩歲,誕生在德國。
自2011年從故國出逃,廖亦武一直是德語文學界的明星。他是西方公認的中國當代底層歷史記錄者,他在1886年創立的漁夫出版社發表了六本紀實文學,還在另外的出版社發表過詩集、聲音書和文學檔案。2012年他獲得德國書業和平獎。現在他又推出了一部小說:《輪迴的螞蟻》。
廖亦武開門見山:這本書的源頭可追溯到1992年他在中國監獄開始的創作。1989年6月4日,北京天安門民主運動剛被血腥鎮壓,他就同步發表了長詩《大屠殺》,也因此遭受四年牢獄之災。在囚室中,他把螞蟻大小的字跡密密塗寫在紙片上,並利用各種渠道找機會偷送出去。
20多年後的今天,他終於在遙遠的柏林給自己第一本長篇小說畫上句號。值得注意的是, 此書首先面世的是德文—它還沒有中文或英文版本。
一部中國式公路電影和荒誕劇
《輪迴的螞蟻》講述了作者從前的自我。它把老威的虛構故事和中國的大歷史交織在一塊,發展 一部荒誕的、中國式公路電影似的小說,戲謔的筆法讓現實與過去、真實和超現實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不清。它充滿極其高超的幽默,而老威在當中扮演了一個妙不可言的反英雄。
老威有自己的政治倫理底線,也懂得靈活運用。出獄以後,他隨波逐流,混跡於江湖,缺錢時,就將盜版來中國的紐約低俗小說《教父》改頭換面,連夜編譔 《教母》和《教子》,讓中國民運昔日領袖在美國街頭與白人警察槍戰,不料竟成暢銷書。時過境遷,當年上街遊行示威的同志們,不少淪為一夜暴富的商人。可在另一面,老威又對老一套的說教不感興趣。當一喝醉的警察提醒,沒有共產黨中國人統統得餓死,他就使勁打哈欠說自己也他媽的醉了。
譯者白嘉琳花三年把這部小說變成德文,完成的一瞬間卻伏案哭泣,她愛上了書中折磨自己的諸多細節。其中難忘的一幕發生在殯儀館,老威朋友的妻子因抗拒拆遷而自焚身亡,老威陪同送葬到倒閉的國營企業改造的殯儀館,方得知那兒如同豪華酒店,喪事等級分普通、貴賓、特別貴賓、超級貴賓,并有對應的配套服務。在接下來滑稽透頂的討價還價中,殯儀館前臺小姐搖身一變為超級營銷怪獸,一波波推出一幕幕令人眼花繚亂卻出奇昂貴的離奇喪禮。對話尾聲是—
死者家屬:「死不起人啊。」
小姐: 「如果多來幾次, 成熟客了, 可以打八到七折。」
對中國特色的高臺跳水般的資本主義,再沒有比這更出彩的刻畫了。
德國的異議人士膜拜
關於廖亦武,有這樣的評價:長詩《大屠殺》使他成了反革命罪犯,西方的讀者們卻稱他為「異議詩人」。
這是實話實說?還是話中有話?批評「異議人士」的標籤化,或許也是批評德國常見的某種異議人士膜拜?從艾未未的例子,大家可看出,被簡化到「除了異議人士之外……」對一個藝術家意味著什麼。艾未未被狂熱追捧了相當長的時間,直到他說了一些對媒體來說不那麽「異議」的話,就受到許多質疑和詬病。
我問廖亦武:您覺得自己是異議人士嗎?
他放下茶杯,不解地盯著我。他並不了解關於艾未未的種種爭論。「我當然是異議人士,」他說,「是監獄把我造就成這樣。」
「異議人士」標籤比「詩人」標籤更重要,還有比這更中肯的對」標籤化」的批評嗎?
廖亦武繼續說:「在中國,一個好作家應該坐過牢,離過婚,被國家單位開除過。」
「什麼?」
「沒經歷過這些,我們還有什麼可寫的?」
這話不同尋常,可廖亦武是認真的。對他來說,起碼在中國人跟前,明擺著截然相反的兩面,讓你做出抉擇。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在獲獎後不久,把中國互聯網審查比作必不可少的機場安檢,這種人在廖亦武眼中算不上作家。這關乎人格底線,也引發了一個永久的爭議:誰才是中國文學的真正代表?
《輪迴的螞蟻》最終成了一本色調陰沉的作品,可在書的結尾又浮現希望,好像作者執意突破自己的過往:老威老家發生大地震,阻斷河流的大壩轟然決堤,倖存者老威在爬山:「他願意就這樣爬一輩子。人活著就該有個盼頭。
「老威不知道,在一米之外有一隊螞蟻也在爬坡,大約幾萬隻?不,至少幾百萬隻吧。牽成彎曲的長線,由底處向高處搬家。感覺上,螞蟻比人爬得慢,可螞蟻多,就總能爬到人的前頭。甚至爬到天的盡頭。」
原文連結:
http://www.spiegel.de/kultur/literatur/liao-yiwu-romandebuet-diewiedergeburt-der-ameisen-des-chinesischen-autors-a-1114717.html
推薦序二
德意志電臺:壓迫感與畫面感的極致
作者:Oliver Pfohlmann,中譯:王培根
2016 年 12 月 12 日
《輪迴的螞蟻》—這是中國異議詩人廖亦武第一本長篇小說書名,他 2011 年逃到柏林,先後獲得了紹爾兄妹獎和德國書業和平獎。這本 500 多頁的鴻篇巨製始於 1992 年作者被監禁時,終於不久前的流亡中。
「流逝的並沒有死去,」威廉•福克納寫道,「甚至根本沒在流逝中死去。」當有人被夢魘般的回憶所壓迫,觸及到歷史深處的某些傷口,福克納這話就顯得很有道理。就如在中國,每個關於 1989 年天安門大屠殺的討論都被嚴禁一樣。在瘋狂鎮壓抗議者之際,獨裁政權還把整個中國變成一座「血腥刺鼻的大兵營」,廖亦武在他的小說裡這樣寫道。
這部堪稱偉大的作品以強烈的壓迫感和畫面感,講述了為什麼昨日中國延伸至今,暴政依舊有其「合理性」,儘管還有那麼多的勞改營和互聯網審查。作者借書中主角老威之口,表達出一個「異議人士」的美學心願:有一天他能回到曾經被數百萬要求民主改革的大學生們所佔領的天安門廣場,用在監獄中學會的洞簫,吹一曲自己創作的《帝國末日》:
冬日夜半,雪花紛飛,他手持長簫,信口鼓吹,直至樓角傾圯,雕梁畫棟褪色。雪在一隻古曲中堆積,上漲,如海潮一般卷沒了門樓,然後他將看見廣場越來越空闊,終與天邊的蒼海連成一片。他繼續吹著,月兒被凍成一塊冰,在歲月的漫卷下,所有的帝國建築都如魚嘴一般開合著,吐著鵝毛飄飄的氣泡。接著,人密密地長出來,曾經擠滿這個廣場的死人和睡著的活人,都象雜草,從斑斑剝剝的磚縫冒出來,這就是所有人類帝國的結局麽……
靈感全來自中國社會被踐踏的人們
與小說情節相似,廖亦武也用簫聲悼念那些亡靈,不過不是在天安門廣場,而是在他的另一個「故鄉」德國,在一場接一場的作品朗誦會上。這位發表《這個帝國必須分裂》的著名異議人士獲得了 2012 年德國書業和平獎,與此同時,他的名字成為祖國的禁忌—這樣詭異的現實令這部長篇小說處女作竟以德譯本向全世界首發。目前為止,廖亦武以刻畫中國社會 「沉默大多數」的紀實文學而聞名,那些被剝奪、被歧視、被踐踏的人們,在中國按獨裁指令向壟斷資本主義狂奔中掉了隊。而此前,那首寫於大屠殺之夜的預言性長詩《大屠殺》,讓他身陷囹圄 4 年。2011 年出版的記錄這段經歷的《為了一首歌和一百首歌》裡,他已充分展現作為故事敘述者的文字功力和才華。
獄中歲月依舊是這部小說的枝幹之一。小說的創作始於作者服刑中的 1992 年。今年 58 歲的他,在前言中描述怎樣偷偷把螞蟻大小的字跡填滿破爛不堪的紙片,以此在內心深處重建剝奪不去的尊嚴和自由—這讓他的靈肉挺過家常便飯似的虐待和酷刑,地獄之旅成為這部書的出發點—在身體不能走的時候,心也要不斷向前,只有心自由了,遙遠的風中回聲才將撲面而來,飛舞的亡靈也將撲面而來。
看似虛構的文學自傳
由於老犯人的幫助,手稿被偷運出獄,藏起來,直到在20 多年後的流亡中完成。一目了然的是:主角老威的人生軌跡,與作者經歷有諸多重合。例如故事中種種家國遭遇,以及老威因為一首詩而成「反革命」—粉墨登場的還有好些異議知識分子,作者爛熟於心的朋友們,包括被長期監禁的唯一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譯者白嘉琳因此稱這部書為「看似虛構的文學自傳」。
老威愣在突如其來的黑暗中,感覺到歲月暗河的喧嘩,眾多逝者如魚群一般,紛紛從腋下滑過。姐姐、爺爺、爺爺的死對頭三婆、國軍戰犯四舅、蔣介石、毛澤東,鄧小平,還有被蔣、毛、鄧弄死的許多叫不出名字的冤鬼。眼下蒲勇也忝居末位,腳步輕得跟魚尾巴似的。
如果把這部跌宕起伏又哲思深沉的傑作簡化成一個便於評論的文學標籤,就太可惜了。作者高超的敘事技巧讓人驚嘆不已,從毫無掩飾的直白到極其晦暗的嘲諷,在這部書裡你能見識各種迥異的講述風格,隨處橫溢的非凡想像讓人不得不折服。它往往漫不經心地將讀者帶上意料不到的旅程:奇幻的、荒誕的、甚至是惡作劇的,每一場景都充滿幽默、戲謔和極端放肆。又例如書中主角遭遇那些「真正的」鄉村巫婆和神漢,他的夢、幻覺、逼真的經歷都融為一爐;還有在傳統葬禮上爆發了農民起義,反對「計划生育」,老威爸爸抗議無效,被鄉民們擁戴為妄想從中國分裂出去的「大有國」皇帝,當然,共產國的戒嚴部隊不大工夫便掃平了這次「動亂」。
獨裁政權的廣大受害者
這部感人至深的追憶小說呈現的另一特點,是源遠流長的傳統中國和被共產黨一再強暴的現代中國的衝突。例如老威的四舅是國民黨戰犯,偷越國境未遂,含恨死去,於是鄉村親戚組成的送葬大隊夜以繼日趕到城裡,要搭臺唱忠良被謀害的大戲,不料撞上六四屠殺之後的風聲鶴唳。警察們執行公務來了,用警棍驅散了鄉巴佬的「非法集會」。而時隔多年的另一場葬禮,卻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討價還價:
「……乾脆神父、和尚、道士全部要,中西合璧最完美,投胎也來得飛快。」
「我們商量一下再說。」
「還有追悼會主持和出殯儀仗隊……所有服務項目及價格,牆上鏡框內都有,全包還是半包,請您老仔細比較,再談。」
「全包多少?」
「四萬人民幣。美元按人民銀行當日匯率折算。」
「死不起人啊。」
「如果多來幾次,成熟客了,可以打八到七折。」
對話背後「惡毒」噱頭是:死者是一個因抵抗拆遷家園而自焚的老太太—這部肯定經得起時間考驗的作品叫《輪迴的螞蟻》—它所指的不僅是寫在監獄破紙上的螞蟻般擁擠的漢字,更是共產獨裁下的千百萬逝去或正在逝去的受難亡靈。
原文連結:
http://www.deutschlandfunk.de/liao-yiwus-erster-romaneindringlich-und-bildgewaltig.700.de.html?dram:article_id=373748
推薦序一
明鏡周刊:「好作家應該坐過牢」
作者:Maximilian Kalkhof ,中譯:王培根
2016年10月3日,星期一
他是中國歷史的記錄者:2011年流亡德國至今,在這裡非常出名。現在這位書業和平獎得主出版了第一部長篇小說。我們在柏林採訪了他。
問一個在德國公認的「異議詩人」覺得自己是不是「異議人士」—這問題太可笑?還是太愚蠢?
柏林夏洛特公主城堡附近,廖亦武坐在自家露臺上,他品著一杯四川花茶,九月的陽光刺得他直眨眼睛。他女兒不時在身邊出沒,她叫「小螞蟻」,還不滿兩歲,誕生在德國。
自2011年從故國出逃,廖亦武一...
目錄
德語書評一 明鏡周刊:好作家應該蹲監獄
德語書評二 德意志電臺:壓迫感與畫面感的極致
德語書評三 法蘭克福匯報:坐牢獲自由
德語書評四 世界日報:自由就是他自己
德語書評五 蘇黎世提示報:小螞蟻的大目標
作者導讀
卷一 獄中手稿
囚徒占卦
痲瘋病想念毛主席
亂倫的大舅母
生離死別
冰雪覆蓋的愛情
更加絕望的愛情
祖傳四合院
起死回生的棺材
同歸於盡
壽星的葬禮
農民起義
灰飛煙滅
卷二 喪家之犬
烏江夜色
山高皇帝遠
瞎子算命
古老的法術
詩人之死
政治與性愛
回憶在柏林停頓
紅軍廟
人販子
春來茶館
皮肉買賣
情敵、詩歌和自殺
卷三 兩代人
老兵越境記
獄中學簫記
卷四 畫地為牢
警察老曹
革命同志
又一位革命同志
更多革命同志
活人徒掙扎
死人不說話
刀下留狗
雞足神山
滾回凡塵
生錯了時代
法輪功
故鄉夢
卷五 淪落江湖
天邊外
鬼子進村
藝術給了瘋狗
帝都孤兒
吶喊的冤魂
搭錯車
幸福牌烈酒
沙漠裡渴死的河
維吾爾歌手阿不都
獲獎惹麻煩
臺詞練習
遣送回鄉
尾聲
附錄:天問
德語書評一 明鏡周刊:好作家應該蹲監獄
德語書評二 德意志電臺:壓迫感與畫面感的極致
德語書評三 法蘭克福匯報:坐牢獲自由
德語書評四 世界日報:自由就是他自己
德語書評五 蘇黎世提示報:小螞蟻的大目標
作者導讀
卷一 獄中手稿
囚徒占卦
痲瘋病想念毛主席
亂倫的大舅母
生離死別
冰雪覆蓋的愛情
更加絕望的愛情
祖傳四合院
起死回生的棺材
同歸於盡
壽星的葬禮
農民起義
灰飛煙滅
卷二 喪家之犬
烏江夜色
山高皇帝遠
瞎子算命
古老的法術
詩人之死
政治與性愛
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