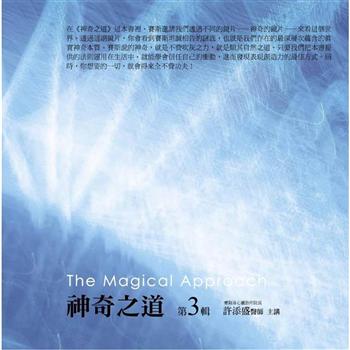鬼屋的設計有至少三層,介紹上說了全程大約四十分鐘,但這個四十分鐘應該不包括停在原地抱團尖叫的時間,反正蔣丞感覺他們一邊發出各種能嚇得死鬼的尖叫,一邊在忽暗忽滅的一個個房間裡轉了快二十分鐘,連一次樓梯都沒有走過。
「我們是不是應該找個地方上樓?」蔣丞問了一句。
「我在找呢。」潘智在最前頭回答,「這間屋子我們是不是進來過?」
「沒有。」顧飛說。
「那這個門我們應該也沒走過。」潘智指了指前面一個關著的門,「也許就是通……」
話還沒說話,一串小孩子的笑聲從他們身後飄過。
儘管蔣丞都聽出了這笑聲裡的電流聲可以確定就是從某個藏在角落裡的喇叭發出來的,但還是一陣毛骨悚然。
「後面有鬼?」李松問了一句。
「快走吧快走吧……」許萌扯著黎雨晴的衣服,低著頭都不敢往四周看了。
正說著,又一串笑聲響起。
「啊——」一幫人同時喊了起來,擠著潘智就往那個門撲了過去。
「別怕別怕別……」潘智被推得站都站不穩了,趕緊過去把門拉開,緊接著就是一聲暴吼,「啊——」
門外站著一個不知道是路過還是等半天了的鬼,潘智被一幫人直接推進了這個鬼懷裡。
嚎叫聲中這個鬼都被撞得靠到了後邊兒的牆上,不得不使勁把潘智給推開。
「啊——」一幫人轉身又跑。
身後還有個門,一幫人慌不擇路,世界已經毀滅了一般地衝了過去,拉開門就往裡衝。
明亮而耀眼的陽光在他們的嚎叫聲中灑滿了人間。
他們幾個人站在陽光裡還嚎了好幾聲才一臉茫然地停下了。
「我操?」潘智震驚地瞇縫著眼睛,「怎麼出來了?」
「連樓都沒上就出來了?」蔣丞回頭看了看那個小門,「這他媽是個緊急出口吧?」
顧飛站在最後,抱著胳膊清了清嗓子。
「嗯?」蔣丞回頭看著他。
顧飛往右邊遞了個眼神,一幫人順著看過去,頓時就想回頭再擠回鬼屋裡去。
右邊大約三十米的,就是入口排隊的地方,幾十個人排著隊一塊兒往他們這邊看著,臉上的表情都挺一言難盡的,還有幾個已經笑得不行了。
「我操這誰帶的路啊!」潘智悲痛欲絕地問。
「瘋瘋?」黎雨晴說。
「不是我。」胡楓馬上說,「我是跟在大李後頭出來的!」
「我?」李松一臉茫然地愣了好半天,還伸了個手比劃了半天,「我好像是有一個……開門的動作?」
「蠢貨!」潘智撲過去對著他連捶了好幾下,在他的帶領之下,一幫人全上去一人給了李松幾下。
已經出來了,就沒法再回去了,他們只好繃著臉,一臉「我們真的是只是走錯了路」的表情在排隊的人目送之下離開了鬼屋。
「去那個古塔看看吧?」許萌提議,「人文景觀嘛,也挺有意思的。」
「嗯。」顧飛拿了手機出來看了看時間,「古塔上去下來以後……差不多可以去吃點兒東西,公園裡頭應該有一家味道不錯的,我得先問問在哪兒。」
「也是個路癡嗎?」黎雨晴笑著說,「吃東西的地兒都不記得在哪裡了啊?」
「不是。」顧飛一邊撥號一邊說,「我上次來這兒都是小學春遊了。」
「啊?」黎雨晴愣了愣,「我看還有個遊樂園呢,還有動物園,要換了我可能一學期得來玩好幾次呢。」
「說明你心智不健全。」潘智說。
「你才不健全!」黎雨晴瞪了他一眼。
顧飛走到一邊估計是又給劉帆他哥打了個電話問吃飯的地方。
蔣丞看著他站在逆光中的背影。
無論是看電影,還是去遊樂園公園,顧飛的娛樂活動,似乎都停留在很久以前,雖然自己也不愛去公園,但跟同學朋友一塊兒去的次數也不算少,學校取消了春秋遊之後他們還老自己出去。
顧飛的生活就在鋼廠,除了曠課出去玩過幾次,他似乎就一直在鋼廠那片。
蔣丞這幾個月以來的生活也一樣,如果沒有顧飛,他的四周就像凝固了一樣,所有的人,就沿著腳下的那幾條街,困在這小小的一片空間裡。
活得沉悶而無力。
這樣的生活一天兩天可以,一個月兩個月咬牙,一年兩年可能就會爆發,蔣丞走到旁邊的垃圾桶邊,點了根菸叼著,時間長了呢,也許就會習慣了,無奈也好,不甘也罷,最後就沉下去了。
******
古塔在公園裡的一個湖邊,湖水不怎麼乾淨,但塔很漂亮。
塔挺高,站在塔頂上能看到公園外面的街道,來來往往的車,不過也更能看清這個陽光下都帶著些灰撲撲落寞的城市。
「我記一下內容。」潘智一邊拿了手機拍著牆上的介紹一邊說,「字數還不少,回去一抄,週記就齊活了。」
「這個不錯。」李松也開始拍照。
「我跟你們說……」潘智看了一眼都拿出手機對著牆開始拍的幾個人,「別都跟我抄一樣的。」
「沒事兒,寫清是引用就行了,引用都一樣嘛。」胡楓說。
「想想也是悲涼。」潘智嘆了口氣,「幾百字的週記,大概就最後一行是咱們自己寫的,以上引用自古塔旅遊圖。」
幾個人頓時笑成一團。
「我好久沒寫週記了。」蔣丞靠在欄杆上伸了個懶腰,「老徐也沒這個要求。」
「要求了也沒人寫。」顧飛說,「要讓我一週寫一篇這玩意兒,我肯定寫不出來。」
「也不會,你肯定寫得出。」蔣丞笑笑,「你可以寫詩。」
顧飛笑了起來:「對哦。」
「哎我跟你說。」蔣丞轉身撐著欄杆,看了一眼潘智,又轉回頭小聲說,「潘孫子應該是……看出來了。」
「嗯,我看出來他看出來了。」顧飛也放低聲音,「會有什麼問題嗎?」
「沒有。」蔣丞說,「我本來也沒想好該怎麼跟他說,他自己看出來了也好,省得我找詞兒了。」
「他以前就知道你的事兒是吧。」顧飛問。
「嗯。」蔣丞點點頭,「只有他知道……當然,現在你也知道。」
顧飛笑了:「我有你把柄哦。」
「我也有你把柄哦。」蔣丞斜了他一眼。
顧飛笑著沒說話。
「其實。」蔣丞沉默了一會兒,「這個其實對於你來說,算不上什麼把柄吧?」
「對你算嗎?」顧飛反問。
「我不知道,算吧。」蔣丞皺了皺眉,「我說不清,我不喜歡被人盯著,被人議論,我很討厭被人……指責。」
顧飛看著他,他停了一會兒:「你這樣是不可以的,你那樣是不對的,這裡你需要改正,那裡你需要提高。我討厭被人說你這樣是錯的,那樣是錯的,從小到大我聽得太多了,我就是真的……實在是……」
「我知道。」顧飛說,「我知道你的意思。」
「我本來不想說這個。」蔣丞輕輕嘆了口氣,趴到欄杆上,「我不想讓你覺得我……慫。」
「這個跟慫不慫沒什麼關係吧。」顧飛也趴到欄杆上,「不慫也不表示需要把這些事昭告天下,就像我不介意別人知道我內褲是什麼樣的,但也並不表示我會穿著內褲到處走。」
蔣丞偏過頭看著他,憋了一會兒之後笑了起來:「這什麼破比喻。」
「我已經用盡全力了。」顧飛說。
潘智從鬼屋之後一直沒有跟蔣丞討論過顧飛的事兒,一直到假期結束他們要回去了。潘智下午吃完飯回到出租屋,收拾完晚上要搭車的行李時,才說了一句:「你跟那個顧飛……」
「嗯?」蔣丞坐在沙發裡靠著。
「什麼時候開始的啊?」潘智問。
「沒多久。」蔣丞說,「你有什麼建議嗎?」
「沒有。」潘智笑了笑,「這有什麼可建議的,天要下雨,爺爺要談戀愛,多正常的事兒,我還能攔著嘛。」
蔣丞笑著沒說話。
「不過說實話啊,我挺吃驚的。」潘智說,「我壓根兒就沒想過你在這兒還能談上戀愛了。」
「為什麼?」蔣丞看著他。
「有什麼為什麼的。」潘智坐到他旁邊,「就覺得這種情況下你不會有這個心情唄。」
「嗯。」蔣丞倒在沙發扶手上枕著胳膊,「我自己也沒想過。」
「但也不是不能理解。」潘智想了想,「之前我還挺擔心你的,後來看你也沒崩潰……總好過一個人悶著吧。」
蔣丞沒吭聲,瞪著天花板出了很久的神,然後看了看潘智:「潘潘。」
「換個稱呼。」潘智搓了搓胳膊。
「孫子。」蔣丞說。
「什麼事兒爺爺。」潘智轉頭。
「談戀愛,談個戀愛。」蔣丞說,「你覺得有什麼區別?」
「腦筋急轉彎嗎?」潘智問。
「轉你大爺。」蔣丞說。
「這個你都要問我?」潘智看著他,「這不是你的風格啊。」
「我就想聽聽智商低點兒的人是怎麼想的。」蔣丞摸了根菸出來叼著,「我們高智商的人容易想得太多。」
「想得多和沒頭腦的區別唄,我想談個戀愛了。」潘智說,「比如我,我就想談個戀愛,黃慧,要不就……」
「不。」蔣丞打斷他,「那換個說法,想跟我談戀愛和,想跟我談個戀愛呢?」
「我操。」潘智擰著眉,「這麼麻煩,那就是只對你唄,無論談戀愛還是談個戀愛,都得是跟你。」
蔣丞衝他豎了豎拇指。
蔣丞感覺顧飛的細膩有些讓他吃驚,談戀愛和談個戀愛,這前面都有個「他」,無論是哪個答案,都是他。
蔣丞勾了勾嘴角,至少在這一點上,顧飛知道他的想法。
他並不是有多寂寞,有多孤單,需要在這裡隨便找個什麼人開始一段感情,只因為對方是顧飛,無論是什麼樣的感情,前提都得是顧飛。
這兩天他都在琢磨這句話,其實翻過來倒過去,他早就已經想得很明白這句話的意思。
也知道了顧飛那句「我會一直喜歡到你不再需要我喜歡你為止」真正的意思。
他不得不承認,顧飛的確比自己想得多太多,自己並不能說有多衝動,但畢竟這麼主動的原因就是我喜歡你,我想跟你在一起。
我想跟你談戀愛,不是談個戀愛,是你,不是別人。
這是顧飛最後會到樓下等他的原因。
但如果有一天,沒有路可走了,顧飛的選擇大概就是「到此為止」,而自己的選擇呢?
這是顧飛那個問題需要他回答的。
顧飛應該是習慣了把所有的事都想到,他的成長環境,他的家人,他的經歷,讓他習慣了把所有的可能性都想到,找到每一種可能性的應對方法。
而他不一樣。
他沒有需要他這樣去思考去確定每一件事的環境,哪怕是突然被扔到了這樣的地方,他也沒有去想太多,眼前碰到了什麼,就解決什麼。
我不是親生的,我的親生父母是這樣的,我換了個從天到地的環境……每一件事,他都沒有往縱深裡思考過,他所有的行動都是看著腳下,這裡有塊石頭,我怎麼過去,這裡有條溝,我怎麼過去。
在這一點上,他跟顧飛有著完全不一樣的卻又習慣了的思維方式。
「這個是他問你的嗎?」潘智在旁邊問了一句。
「是我問他的。」蔣丞拿過茶几上的菸灰缸放到沙發旁邊的地板上,往裡彈了彈菸灰。
「不可能。」潘智看著他,「我太瞭解你了。」
「那你要小心有一天會被我滅口。」蔣丞說。
「他給我的感覺吧。」潘智從茶几上的菸盒裡也摸了根菸點上了,「就是……怎麼說,我看到他就想叫聲哥。」
「他比你小。」蔣丞說。
「……我就是這麼個意思。」潘智嘖了一聲,「你也比我小,我還叫你爺爺呢,我的意思就是,他一看就是那種……扛過特別多事兒的人。」
「是嗎。」蔣丞輕輕嘆了口氣,這個判斷倒是相當準確。
「有些人你一接觸就能知道,就氣場這東西,還是能感覺得到的。」潘智說,「雖然他在鬼屋裡……但是我還是一看他就想叫聲飛哥,你懂我意思吧。」
「懂。」蔣丞說。
「不過我叫你爺爺不是這個原因。」潘智又說。
「這個就不用專門補充說明了。」蔣丞說。
「丞兒。」潘智抽了口菸,一臉深沉狀地思考了好半天,「于昕跟你不算談戀愛,連談個戀愛都算不上。」
「啊。」蔣丞應了一聲,也一臉深沉地凝視著他。
「所以。」潘智又沉默了好半天,「顧飛是你的初戀啊。」
「操。」蔣丞樂了,「憋這半天,我以為你要說什麼呢,屁都沒個響點兒的。」
「我沒說完呢,沒說完呢!」潘智很不爽地看著他,「你能不能把嘲笑我的步子從狂奔改成散步啊,慢點兒能死嗎!」
「散步,散步。」蔣丞點點頭,「您說完的。」
「按說吧,初戀多半……要受點兒傷,畢竟我們……還小。」潘智夾著菸,努力地措著詞,很艱難地磕巴著,「我就是想說,別讓自己傷勢太重,你懂我意思吧?就……爺爺啊,我看您那位……我奶……我姥爺吧,他應該是那種已經很清楚該怎麼自我保護了的人……我沒別的意思。」
「啊。」蔣丞半天才從潘智這混亂的稱呼裡整理出來他想表達的意思。
「別覺得我說話那什麼,不合適。」潘智說。
「謝謝。」蔣丞把菸頭按滅,起身在他肩上拍了拍,「我知道了。」
「嗯。」潘智點頭。
「菸灰彈這裡頭。」蔣丞把菸灰缸放到他面前,「再彈茶几上我讓你用舌頭給我把茶几舔一遍。」
「我操!」潘智愣了愣,「我他媽拿紙墊著的好嗎!」
「所以我現在沒讓你舔啊。」蔣丞笑著倒回沙發裡。
送潘智他們去火車站的行程,顧飛就沒再參加了,這幾天雖然他並沒有全程參加所有的活動,但在顧淼看來,他在家的時間還是少了,所以晚上顧飛帶著她去王旭家吃餡餅。
蔣丞把潘智他們送到了車站:「行了,都別說什麼臨別感言啊,太肉麻承受不住。」
「不說。」胡楓說,「暑假了回來看看我們啊,有來有往嘛,怎麼樣?」
「……這個真不好說。」蔣丞這幾個月以來還真沒想過回去的事兒,無論是回去幹什麼,都完全沒有想過。
「或者約個地方一塊兒去旅遊也行啊。」李松說。
「到時詳細約。」潘智說。
「對了,顧飛這幾天一直給當導遊,也沒跟人說聲謝謝。」黎雨晴把手裡的一個袋子遞給了蔣丞,「那天不是說他有個妹妹嗎,直接買東西給他好像不合適,我們就買了個娃娃……」
蔣丞笑了笑接過來:「哪用這麼客氣。」
如果這幫人見過這個妹妹,估計誰也不會再想著給她買個娃娃。
一幫人都進站之後,蔣丞轉身去了公車站,非常節省賢慧地坐了公車回了出租房。
進屋之後他給那個娃娃拍了個照,發給了顧飛。
—我同學送給顧淼的。
顧飛很快地回了一條訊息過來。
—送走了?
—嗯,你們還在九日家嗎?
—還在,你過來嗎?
—不了,我有點兒累,躺會兒鬆鬆老腰
—捏腰.jpg
蔣丞笑了半天,在屋裡又轉了兩圈,看看潘智有沒有什麼東西遺漏了的,然後進了臥室,時間還算早,夠……做一套卷子的。
蔣丞站在書桌前,對自己的決定表示了深深膜拜。
這,就是一個學霸的素質。
跪。
手機又響了一聲,顧飛發了張顧淼的照片過來。
照片上顧淼抓著一個餡餅,一臉茫然。
—我給她看了娃娃的照片,她是這個表情
—你這哥當的真好,一個小姑娘看到娃娃居然是這種樣子。
蔣丞把床上亂七八糟的被子扯起來抖了抖,雖然是要做卷子,但是環境也還是很有影響的,要整齊一些……他看到了枕頭下面露出了一個黑色的盒子。
他拿起來看了一眼,打開了盒子,雖然看到盒子的時候他已經猜到了這是什麼東西。
但打開看到裡面真的放著一支騷紅色的鋼筆的時候,他還是有些震驚,潘智居然會送支筆給他。
裡面還有張小紙條,上面有一行字。
「當面給你肯定被嘲笑,所以放在這裡了,給你支筆是讓你時刻記著自己是個學霸。」
蔣丞拿著筆坐到書桌前,笑了好一會兒。
想想又嘆了口氣,潘智這朋友沒白交,享受著孫子的待遇,操著爺爺的心。
他拿過一張紙,在上面隨便寫了幾個字,就是這字吧,用什麼筆,都顯不出筆好來。
他盯著紙看了一會兒,慢慢運著氣,寫下了一行字。
希望我們都能像對方一樣勇敢。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撒野(3)(限)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78 |
二手中文書 |
$ 261 |
華文戀愛輕小說 |
$ 290 |
中文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撒野(3)(限)
蔣丞的生父病重,在無盡的爭吵中李保國用他的方式離開了這個世界,蔣丞腦中始終縈繞著生父墜落的那一幕,還好的是他至少有顧飛一直在他身邊。
蔣丞在學校表演中用顧飛創作的《撒野》驚豔了所有人,確讓顧飛的內心充滿了矛盾,他雀躍於蔣丞的歌聲,卻焦躁於「夢醒」的慌張。
作者簡介:
巫哲
暱稱:球球、狗蛋兒
生日:4月28日
星座:金牛座
職業:小說作家
代表作品:撒野
資深網路原創小說人氣作家。
一個堅持寫溫暖故事的作者,日常愛好種花、養狗、懟金魚。
TOP
章節試閱
鬼屋的設計有至少三層,介紹上說了全程大約四十分鐘,但這個四十分鐘應該不包括停在原地抱團尖叫的時間,反正蔣丞感覺他們一邊發出各種能嚇得死鬼的尖叫,一邊在忽暗忽滅的一個個房間裡轉了快二十分鐘,連一次樓梯都沒有走過。
「我們是不是應該找個地方上樓?」蔣丞問了一句。
「我在找呢。」潘智在最前頭回答,「這間屋子我們是不是進來過?」
「沒有。」顧飛說。
「那這個門我們應該也沒走過。」潘智指了指前面一個關著的門,「也許就是通……」
話還沒說話,一串小孩子的笑聲從他們身後飄過。
儘管蔣丞都聽出了這笑聲裡的電流聲可以確...
「我們是不是應該找個地方上樓?」蔣丞問了一句。
「我在找呢。」潘智在最前頭回答,「這間屋子我們是不是進來過?」
「沒有。」顧飛說。
「那這個門我們應該也沒走過。」潘智指了指前面一個關著的門,「也許就是通……」
話還沒說話,一串小孩子的笑聲從他們身後飄過。
儘管蔣丞都聽出了這笑聲裡的電流聲可以確...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巫哲 繪者: 長樂
- 出版社: 葭霏文創 出版日期:2018-07-06 ISBN/ISSN:9789869622875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88頁 開數:25
- 類別: 中文書> 漫畫/輕小說> B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