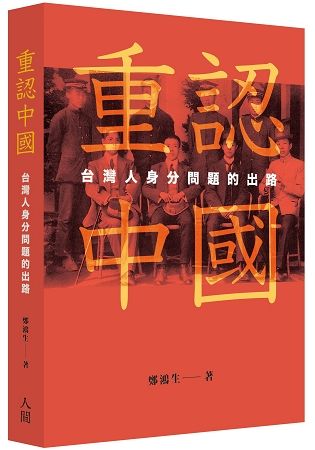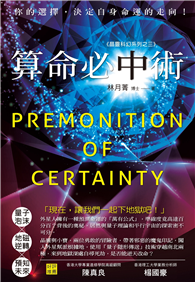「台灣問題」或「香港問題」基於其不同殖民宗主國與歷史過程等因素,有其相對特殊性,但畢竟都是由傳統中國社會被殖民與現代化之後產生的問題,所以還是傳統中國社會現代化問題的一環,就是說最終還是屬於中國的問題,一個在台灣或香港的具體歷史情境下呈現出來的中國現代化過程的問題。
中國的主體大陸地區雖然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有其相對自主性,而且為了取得這個自主性曾經歷經血跡斑斑的奮鬥,犧牲遠遠超乎台灣。但大陸的現代化也曾帶著「自我殖民」創傷。這種創傷的一個具體例證就表現在它曾經比日本更強烈地厭惡自己的過去,露出更昭彰的羞恥感與自卑感。
因此台灣、香港與大陸這三地如今所顯現的各種問題,就不應只被看作不同歷史經驗的個別問題,而應是傳統中國社會在現代化過程中的共同問題。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重認中國:台灣人身分問題的出路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332 |
二手中文書 |
$ 363 |
兩岸關係 |
$ 391 |
社會人文 |
$ 414 |
兩岸關係 |
$ 414 |
中文書 |
$ 414 |
社會人文 |
$ 414 |
台灣研究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重認中國:台灣人身分問題的出路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鄭鴻生
台灣台南人,1951年生。台大哲學系畢業,留美電腦碩士,曾任職美國的電腦網路公司、台灣的資訊工業策進會,現從事自由寫作。
主要著作有:
《揚帆吧!雪梨》(聯經,1999年)
《青春之歌──追憶一九七○年代台灣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華》(聯經,2001年)
《踏著李奧帕德的足跡──海外觀鳥行旅》(允晨,2002年)
《荒島遺事──一個左翼青年在綠島的自我追尋》(印刻,2005年)
《百年離亂──兩岸斷裂歷史中的一些摸索》(台社,2006年)
《母親的六十年洋裁歲月》(印刻,2010年)
《尋找大範男孩》(印刻,2012年)
其他文字散見《印刻文學》、《台灣社會研究》、《思想》、《人間思想》等刊物。
鄭鴻生
台灣台南人,1951年生。台大哲學系畢業,留美電腦碩士,曾任職美國的電腦網路公司、台灣的資訊工業策進會,現從事自由寫作。
主要著作有:
《揚帆吧!雪梨》(聯經,1999年)
《青春之歌──追憶一九七○年代台灣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華》(聯經,2001年)
《踏著李奧帕德的足跡──海外觀鳥行旅》(允晨,2002年)
《荒島遺事──一個左翼青年在綠島的自我追尋》(印刻,2005年)
《百年離亂──兩岸斷裂歷史中的一些摸索》(台社,2006年)
《母親的六十年洋裁歲月》(印刻,2010年)
《尋找大範男孩》(印刻,2012年)
其他文字散見《印刻文學》、《台灣社會研究》、《思想》、《人間思想》等刊物。
目錄
序 呂正惠
緒論:台灣人的身分問題及其出路
第一部 日本殖民後遺症
關於東亞被殖民經驗的一些思考
——台港韓三地被殖民歷史的比較
「二二八事件」可以避免嗎?
——重看台灣光復的歷史複雜性
水龍頭的普世象徵
——國民黨是如何失去「現代」光環的?
台灣民族想像的可能及其障礙
——回應安德森教授《想像的共同體》
第二部 分離與回歸的辯證發展
誰需要大和解?
——省籍問題中的災難與希望
台灣的大陸想像
台灣的文藝復興年代
——試論台灣六十年代的思想狀況
陳映真與台灣的「六十年代」
——試論台灣戰後新生代的自我實現
台灣的認同問題與世代差異
第三部 台灣話與國語的糾結
台灣話.省籍與霸權
「台灣話」與「中文/華語」的對立迷思
台灣人的國語經驗
——尋回失去的論述能力
第四部 重新認識中國
葉榮鐘為我們留下的香火傳承
重新認識中國的豐富與多樣
——從台灣人的認識局限談起
代跋:我的中國反思與書寫之路
緒論:台灣人的身分問題及其出路
第一部 日本殖民後遺症
關於東亞被殖民經驗的一些思考
——台港韓三地被殖民歷史的比較
「二二八事件」可以避免嗎?
——重看台灣光復的歷史複雜性
水龍頭的普世象徵
——國民黨是如何失去「現代」光環的?
台灣民族想像的可能及其障礙
——回應安德森教授《想像的共同體》
第二部 分離與回歸的辯證發展
誰需要大和解?
——省籍問題中的災難與希望
台灣的大陸想像
台灣的文藝復興年代
——試論台灣六十年代的思想狀況
陳映真與台灣的「六十年代」
——試論台灣戰後新生代的自我實現
台灣的認同問題與世代差異
第三部 台灣話與國語的糾結
台灣話.省籍與霸權
「台灣話」與「中文/華語」的對立迷思
台灣人的國語經驗
——尋回失去的論述能力
第四部 重新認識中國
葉榮鐘為我們留下的香火傳承
重新認識中國的豐富與多樣
——從台灣人的認識局限談起
代跋:我的中國反思與書寫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