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四十歲從頭學起
一
一九七○、八○年代之交是令人振奮的歷史轉折點。台灣黨外政治運動和鄉土文學運動同步發展,國民黨的政治高壓和思想鉗制越來越失去效力。七七、七八年間,國民黨發動它所能掌控的一切媒體,對鄉土文學進行總攻擊,但迫於輿論壓力,終於不敢逮捕鄉土文學的領導人陳映真等。七九年,黨外在高雄舉辦遊行時,由於糾察工作組織不力,讓混進遊行隊伍的不良分子有機會進行暴力破壞,國民黨藉此誣蔑黨外人士蓄謀叛亂,把重要黨外領導人幾乎全數逮捕,並對主要人物進行軍事審判。但在審判結束不久之後所舉行的選舉中,受刑人的家屬凡參與選舉的,無不高票當選。所以,當時我們心情非常暢快,以為台灣即將進入大有所為的民主時代。
沒想到,十年之後的局勢卻讓我大為沮喪。我那時候涉世未深,不知道整個七○年代潛伏著的台獨勢力正在蓄勢待發。所以等到八○、九○年代之交,情勢逐漸明朗時,我從困惑轉為憤怒,完全不知道要怎麼辦才好。
一九八六年,黨外主要力量在美國暗中嗾使下,宣布組織「民主進步黨」。按照當時尚屬有效的戒嚴令,蔣經國可以依法逮捕組黨人士。但是,這樣必然導致台灣社會嚴重對立,因此,蔣經國只好在第二年宣布取消戒嚴令。後來民進黨在訂定黨綱的最後階段,突然有人提議加入「台灣前途由台灣人民自決」的條款,而且通過了。有一批五○年代的左派政治犯,在民進黨宣布建黨時,立刻申請入黨。等到黨綱一通過,他們又立刻宣布退黨,並且登報申明反對民進黨的黨綱。這一事件的發展,可以看出一九八○年代末台灣政治情勢之詭譎。
另一方面,原本有台獨傾向的文化人也開始他們的密謀運作。他們攻擊鄉土文學領導人陳映真的大中國情結,並且一再申說,「鄉土文學」的「鄉土」只能指台灣,跟中國毫無關係,所以「鄉土文學」應該正名為「台灣文學」,還一再「論證」台灣現代文學和中國現代文學扯不上任何連繫。這是八○年代中期開始形成、到八○年代末已盛行於世的「台灣文學論」。
我原本研究唐詩,但受到鄉土文學運動影響,八六年開始寫台灣現代文學評論,並於八八年出版第一本評論集《小說與社會》,我的位置很清楚,我屬於「鄉土文學派」。但當我的評論集出版後,我卻發現,「鄉土文學」已經不成陣營了,新的陣營現在叫做「台灣文學」。
那個時候國民黨暗中支持日漸興起的「後現代派」,後現代派和台灣文學論者成為兩大勢力,左翼鄉土文學極端式微。大約在九五年左右,雖然我又出版了兩本評論集,但我新寫的評論已經很難刊登在報紙和雜誌上,我的論文大都只能在學術會議上發表。更糟的是,我的文章寫再多,已經沒有人想看了。我在中文系講授的是中國古典文學,但很明顯,學生對古典文學越來越缺乏興趣,大家都想讀台灣文學,而且必須是「有台灣主體性」的台灣文學。就這樣,我漸漸覺得,在台灣我好像是一個「沒有用」的人,如果不存在了,別人也許更高興。
更大的麻煩是,台獨派宣稱,他們不是中國人,而不認同台獨派的人,也不敢說自己是中國人。我曾經問過幾個外省學生,「你們認為你們是中國人嗎?」他們大都拒絕回答。我跟他們講,你們可以反對共產黨,可以不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但你們無論如何還是中國人啊!但他們對此無動於衷,事實上,這種人是另外一種台獨派,我們可以叫做「中華民國」的台獨派。因為他們如果承認自己是中國人,他們知道將來就要跟大陸統一,所以他們不願意承認,也就是說,他們選擇「中華民國」這一塊招牌,拒絕思考統一問題,這當然是另外一種形式的台獨了。
我在學院裡越來越感到孤獨,非常痛苦。後來有一個朋友跟我說,你何不加入中國統一聯盟,至少那裡還有陳映真等人,你就不會完全孤立。我終於聽從了他的勸告,在1992年4月正式加入中國統一聯盟。在此之前,我跟陳映真只見過兩、三次面,很不熟悉,加入中國統一聯盟以後,我們才變成「同志」與同事。
二
一九八七年蔣經國宣布開放兩岸探親以後,很多外省人回去過大陸。當時台灣的媒體最喜歡報導這些外省人對於大陸的批評:大陸非常落後,比台灣差太多了;上海還是四十年前的老樣子,一點變化也沒有;大陸廁所連門都沒有,如此等等。當時大陸規定,回大陸的人可以在香港購買電視、電冰箱、洗衣機(所謂三大件),領取憑證,再把憑證交給大陸親友去領取實物。這件事在台灣非常轟動,台灣人都知道,大陸連這三樣最基本的電器用品都買不起。
以當時兩岸生活條件之差距,台灣人不想跟大陸統一是必然的。當時兩岸的政治對抗還很強烈,所以,國民黨當然會跟台灣老百姓宣揚:你看,共產黨多糟糕,四十年來大陸人民的生活完全沒有改善,你們不應該再批評國民黨了。台獨派的推論就更「深」了:只有中國那種落後的國家才會產生永遠一黨專政的政府(這一批評同時也暗指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中國是沒有救了。當時台獨派什麼蔑視中國、蔑視中國文化的言論都出籠了。我記得最刺激我的一句話就是:「中國人」就像蟑螂一樣,死也死不完。台灣人在日本統治時代受夠了日本人的歧視,日本人動不動就罵台灣人是「清國奴」,現在台獨派把日本人罵他們父親那一代的話,倒搬過來罵「中國人」。台灣人現在發達了,闊氣了,所以也就有資格罵「中國人」了,那副嘴臉,我至今難以忘懷。
八十年代大陸的激進派知識分子也對台獨派的氣燄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大陸激進派說,美國簡直就是天堂,連台灣都比我們好太多,可見以前共產黨的路走錯了,以後一切要跟著美國。我看了他們製作的《河殤》以後,簡直目瞪口呆。他們說,中國是大陸型文明,是黃色文明;西方是海洋型文明、藍色文明。中國應該拋棄保守的、靜態的黃色文明,走向進步的、躍動的藍色文明。台獨派也看到《河殤》,他們欣喜莫名。他們說,台灣面臨海洋,是藍色文明,跟中國的黃色文明沒有任何關係。
大陸的改革開放,和台灣的解嚴及開放兩岸探親幾乎是同步的,其效果類似戰略上的「分進合擊」,它們聯合打擊的對象就是: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大陸經濟的落後,以及中國文化的保守與僵化。
我讀高中的時候(1964-7),李敖的「全盤西化論」盛行一時,我因讀李敖的書而開始關心五四新文化運動。我原來就喜歡中國的歷史與文學,我還沒有能力判斷李敖對胡適思想的繼承與發揮是否站得住腳,但閱讀相關書籍卻加深了我對中國歷史、文化的興趣。那時候我就下定決心考大學要選讀文科,放棄人人都以為將來更有前途的理工科(我的數學成績還不錯,讀得起理工科)。一九六七年考上台灣大學中文系以後,我接著讀碩士,然後到東吳大學讀博士,一九八三年拿到學位。在長達十六年(其中兩年服兵役)的時間我一心撲向「故紙堆」中,很少考慮李敖掀起的中、西文化論戰,以及中、西文明孰優孰劣的問題。
八○年代末兩岸同時興起、並且還意外形成「唱和」之勢的中國文化否定論,以及到處瀰漫、此起彼落的「我不是中國人」的吆喝聲,讓我感受到了類似「震撼教育」的效果。從內心湧現的兩種最重要的情緒是:「屈辱」——居然這麼瞧不起我們中國人與中國文化,和「憤怒」——發出這種聲音的竟然還都是中國人,是自己的「同胞」。此仇不報非君子,而且,君子報仇,十年不晚。我的報仇方法很簡單,把中西歷史、文學從頭讀起,一定要反駁那些無恥之徒的無根之談。
一九八九年我升了正教授,隨即接任清華大學中文系系主任,我在唐詩和台灣現代文學這兩個領域的研究成績是大家都看得到的。一九九二年,我加入中國統一聯盟,九五年我即將接任統盟主席的時候,也有機會競選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在院務會議投票過程中,我發現我的朋友全部聯合起來抵制我。即使如此,在院務會議中距離半數同意我仍然只差一票。那時候我了解到,我在台灣學術界的「功名」之路已經完全斷絕。從此以後,我日漸脫離所謂的「學術研究」,開始全心全意的搞起我的「雜學」。我已經四十多歲了,但我決心從頭學起,為了替中國和中國文化爭一口氣。
三
所謂雜學,並不是隨意找書來看。我先設定了三個大問題,再找相關的書籍來閱讀。首先是中國文化的評價問題。五四新文化運動最大的特點就是,全面批判中國傳統文化,虛心的向西方學習,這是矯枉過正,因為中國文化絕對不可能像新文化運動所批評的那樣全無是處。但毛澤東說過:「矯枉必須過正」,民國初年,保守勢力還非常強大,為了革新,不得不如此。這種反傳統的傾向,一直持續到一九八○年代,最後變成是對中國文化價值的全面否定,這就發展過頭了。也就是說,新文化運動的反傳統,已經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從現在開始,必須重新肯定中國文化的價值,這是台獨派和河殤派對我的啟示。
跟這個大問題相關的,就是對於西方文明的態度,以前為了學習西方,太過於強調西方文化的正面性。事實上,近代西方文明帶給全人類非常大的苦難,譬如,兩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死亡人數,是以往任何歷史都無法比擬的。只看西方的長處,不看西方文明所造成的災難,就會毫無限制的崇拜西方,就像台獨派和河殤派一樣。
第三個大問題是,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經過百年的摸索和嘗試,為什麼會走上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道路?革命成功以後,重建中國的道路為什麼會那麼艱難?為什麼需要進行改革開放?這難道是因為走錯路而要從頭開始嗎?真的能夠在社會主義體制下引進市場機制嗎?這樣會不會最終還是走向資本主義?
無論是對我來講,還是對台灣的統左派講,第三個問題都是最為迫切的。我跟一般人最大的不同是,雖然我憂心忡忡,但我對改革開放有信心(也許是盲目的信心吧),因此除了大量的閱讀相關書籍和文章外,我還同時閱讀跟前兩個大問題有關的其他書籍。我不急著尋找明確的答案,我希望在努力學習的過程中,我的體會逐漸深入,最後答案會自動出現。反正,我對台灣的形勢不可能有任何影響,我就沉潛下來安心學習,活到老學到老,這樣我的日子才不會白過。
我的讀書範圍之廣,絕對會讓人大感意外。譬如,為了理解中華文明經久不絕的綿延性,我異想天開的想要了解新中國的考古成果,最後我發現了蘇秉琦的《中國文明起源新探》。這本書告訴我,在新石器時代,中國各處都有新石器文明,用蘇秉琦的話說,就是「滿天星斗」。到了新石器時代的中晚期,黃河中游地區,因為處在中心點,終於能夠吸收各處新石器時代文明的精華,形成了華夏文明區,然後再由此輻射出去,帶動各處文明的發展。所以,在有文字之前,中華文明的特質就已形成:它海納百川,包容性極大,因此形成的凝聚力也就非常強大。我把這種想法,應用到我最熟悉的唐宋時代,同時寫出兩篇文章,〈中國文化的第二次經典時代〉和〈難以理解的「中國的存在感」〉。如果沒有讀過蘇秉琦的這本書,我不可能寫出這樣的文章。
(未完……)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走向現代中國之路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60 |
中國文學總論 |
$ 408 |
小說/文學 |
$ 432 |
華文文學研究 |
$ 432 |
中文書 |
$ 432 |
文學 |
$ 432 |
政治 |
$ 432 |
Literature & Fiction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走向現代中國之路
本書特色
《走向現代中國之路》為作者呂正惠用二十多年的時間,透過有系統的大量閱讀,並且儘可能走遍中國的每一個角落,沉潛思索與印證後的讀書心得,述說著他如何從書本中所知道的中國走向現在實際上的中國。本書就其主要目的來講就是要「重認中國」——重新認識中國文化的價值、重新認識中國革命的道路。
作者簡介:
呂正惠,1948年生,台灣嘉義人。台灣大學中文系學士、碩士,東吳大學中文系博士。
台灣清華大學、淡江大學榮譽教授,重慶大學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著有《抒情傳統與政治現實》、《詩聖杜甫》、《小說與社會》、《戰後台灣文學經驗》、《殖民地的傷痕》、《台灣文學研究自省錄》、《CD流浪記》。
TOP
章節試閱
代序:四十歲從頭學起
一
一九七○、八○年代之交是令人振奮的歷史轉折點。台灣黨外政治運動和鄉土文學運動同步發展,國民黨的政治高壓和思想鉗制越來越失去效力。七七、七八年間,國民黨發動它所能掌控的一切媒體,對鄉土文學進行總攻擊,但迫於輿論壓力,終於不敢逮捕鄉土文學的領導人陳映真等。七九年,黨外在高雄舉辦遊行時,由於糾察工作組織不力,讓混進遊行隊伍的不良分子有機會進行暴力破壞,國民黨藉此誣蔑黨外人士蓄謀叛亂,把重要黨外領導人幾乎全數逮捕,並對主要人物進行軍事審判。但在審判結束不久之後所舉行的選舉中,受...
一
一九七○、八○年代之交是令人振奮的歷史轉折點。台灣黨外政治運動和鄉土文學運動同步發展,國民黨的政治高壓和思想鉗制越來越失去效力。七七、七八年間,國民黨發動它所能掌控的一切媒體,對鄉土文學進行總攻擊,但迫於輿論壓力,終於不敢逮捕鄉土文學的領導人陳映真等。七九年,黨外在高雄舉辦遊行時,由於糾察工作組織不力,讓混進遊行隊伍的不良分子有機會進行暴力破壞,國民黨藉此誣蔑黨外人士蓄謀叛亂,把重要黨外領導人幾乎全數逮捕,並對主要人物進行軍事審判。但在審判結束不久之後所舉行的選舉中,受...
»看全部
TOP
目錄
代序:四十歲從頭學起
第一輯 反思現代中國的艱難歷程
我的「接近中國」之路——三十年後反思鄉土文學運動
陳明忠回憶錄《無悔》序
新中國統治下的尋常老百姓
中國社會主義的危機?還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鄭鴻生《重認中國》序
關於評價鄧小平的一些思考
第二輯 重新認識傳統中國
中華文化的再生與全球化
中國文化的第二次經典時代
難以理解的「中國的存在感」——杉山正明的困惑
西方的太陽花,東方的紅太陽
從反傳統到反思傳統
中國文化是我的精神家園
第三輯 陳映真問題
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台灣
一九...
第一輯 反思現代中國的艱難歷程
我的「接近中國」之路——三十年後反思鄉土文學運動
陳明忠回憶錄《無悔》序
新中國統治下的尋常老百姓
中國社會主義的危機?還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鄭鴻生《重認中國》序
關於評價鄧小平的一些思考
第二輯 重新認識傳統中國
中華文化的再生與全球化
中國文化的第二次經典時代
難以理解的「中國的存在感」——杉山正明的困惑
西方的太陽花,東方的紅太陽
從反傳統到反思傳統
中國文化是我的精神家園
第三輯 陳映真問題
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台灣
一九...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呂正惠
- 出版社: 人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11-08 ISBN/ISSN:9789869630221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462頁
- 商品尺寸:長:210mm \ 寬:148mm
- 類別: 中文書> 社會科學> 政治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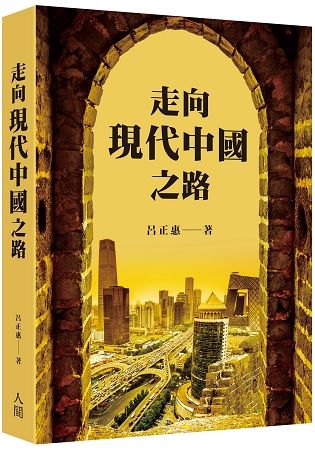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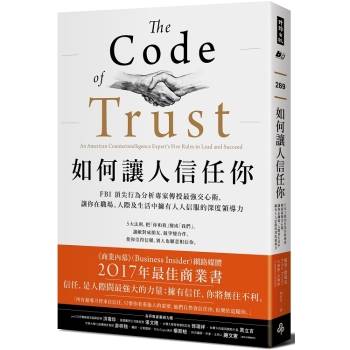









 2025【精選作文範例】國文(作文)[快速上手+歷年試題](記帳士)](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41001205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