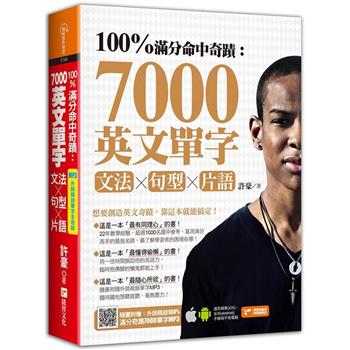【Chapter 01】
人都是這樣的,需要藉由他人的答案來壯膽。
「早安,流蘇。」徐澈特有的慵懶嗓音爬入耳裡。「妳有寫昨天的作業嗎?」
握在手中的筆頓了一下,我頭也沒抬的「嗯」了聲,繼續演算化學習題。
「噯,大家都是同學一場,別這麼冷漠,虧我還覺得妳今天特別美麗,彷彿窗外的太陽閃耀無比……」
我不自覺抬頭瞄他一眼,不過就那麼一瞬間,捕捉到他望向天空的同時,微微皺起的眉心。徐澈將早餐放在桌上,原本緊繃的塑膠袋一碰到桌面,像是洩了氣的熱氣球,發出沙沙聲響。
「其實你只是想抄作業吧……」我無奈地扯了扯唇角,「在你抽屜。」
徐澈高聲歡呼,早自修寧靜的空氣被劃破,同學們紛紛起了騷動。
都是這樣的。只要有人帶頭,姑且不論有意無意,大多會引起周遭人群仿效。例如有人在一片綠地丟了垃圾,經過的人看見了,自然而然拋去道德,將手中垃圾隨手一扔,久而久之那一小塊地方便會堆滿骯髒惡臭的垃圾。
「流蘇,妳不能總是這樣放縱他。」鄧雨莐側過半身說。
「我只是借他抄寫作業的人,他以後會怎樣,跟我無關。」而我只是淡淡的回。
徐澈這個人怎麼樣,和我一點關係都沒有。他坐在我後面,我們的關係就只是抄作業跟借作業給人抄的關係,就像房東跟旅客,等他結束住宿,自然會離開,除此之外我們不會有其他交集。
鄧雨莐聳聳肩,對於我的回應不予置評。
午飯時間,我和鄧雨莐拿著各自的便當到後花園的樹蔭下吃飯。
後花園是明和高中學生最愛聚集的地方。一大片嫩綠柔軟的草地像絨毛毯子一樣,許多學生會在這裡吃午餐、聊天,有人就連午睡時光都會在後花園度過。晚上的時候,這裡看得到星星,於是自然成為了觀星社研究星星、紀錄與拍照的地點。
看到這,你可能覺得很無聊。那我再補充一點,後花園還是個告白聖地。
「今天太陽會不會太大了……」鄧雨莐半瞇著眼睛,打開鐵製餐盒,夾起一塊紅燒肉送入口中。
「天氣預報是說今天最高溫到三十二度。」我咬了一口飯糰。
「真的假的?那會有午後雷陣雨嗎?」鄧雨莐一面吃一面問。「下午的體育課我不想上,今天忘了帶防曬乳,要是曬黑就糟了。」
「應該是不會下雨。」我想了想又說:「妳還是聽聽就好,氣象局預測雨天跟颱風天的發生機率妳不是不知道。」
她點點頭,隨口應了聲。「對了,妳這句話最好別讓徐澈聽見,他媽媽在氣象局工作,若是知道妳這麼評論氣象局預測天氣的準確度肯定會大發雷霆。」
氣象局……
「嗯。」
記得有次英文老師上課拿氣象局預測颱風失誤的新聞開玩笑,徐澈忽然猛地拍桌,要求英文老師道歉,還大聲喝斥她不該拿別人的專業大做文章。結果最後徐澈什麼也沒得到,還吃上一支警告,實在是得不償失。
「其實他這樣也沒錯,不同職業的人也是得互相體諒,更何況英文老師是個外行人。再說了,天氣這種東西原本就很難預料,說變就變,也不是氣象局的人能掌控的。」
我吸了一大口紅茶,說:「他自己也是控制不住脾氣,畢竟對方是老師,就算她說了什麼不中聽的話,該有的禮貌還是要有。況且那不過是上課提振同學精神的玩笑話,聽聽就過了,何必放在心上。」
忽然鄧雨莐沒說話了,周遭倏地只剩下其他學生聊天的嘈雜聲音。我納悶地抬起頭,發現鄧雨莐正盯著我瞧。
「怎樣?」我忍不住問。
「流蘇,這是妳說過最長的一段話了。」她認真的眼神倒是讓我很無言。
陽光穿過葉隙,點點金光灑在鄧雨莐肩頭上,讓她看起來像是被呵護至極的天使。
最後我別過眼,說:「吃完就快點回去吧,快要午休了。」
*
放學後,鄧雨莐要留學校晚自習,我便自個兒揹著書包走出教室。
突然身後一道慵懶的聲音喚住我。
「裴流蘇,流蘇花是在春天開花的嗎?」徐澈問。
我心頭沒來由一熱,隨後整理好情緒,淡淡的應了聲:「嗯。」聲音還有些沙啞。
「我知道了。」他打了一個呵欠,拉了拉肩上的背帶,轉身跨著大步離開。
徐澈的背帶調得極短,側背包是反過來背著的,深藍色布料十分乾淨,像是全新的一樣。我發現他居然沒有在上頭做任何塗鴉。
印象中,像他這樣的學生不是應該要做很多幼稚又無意義的事情嗎?
每天不寫功課、不交作業、上學遲到、上課時間翹課、愛穿便服褲、便服上衣、夾腳拖來學校,自以為和教官作對很偉大、很了不起,卻只是彰顯自己的行為多麼不成熟、多像長不大的孩子,叛逆、驕傲,一副跟全世界過不去的樣子,因為別人的一個眼神就與對方大打出手……
然而,徐澈卻是那種不打架、不鬧事的人。
但是會翹課。
並不是認為他的行為可以被原諒,而是比起明和高中裡那些整天無所事事只愛鬧事的不良少年少女,他已經算是在師長能夠容忍的範圍內了。
……呃,大概吧。
「裴流蘇,妳站在這裡幹嘛?不回家嗎?」鄧雨莐收完書包走了出來,往我面向的方向望了幾眼。徐澈早就在轉彎處消失。
「嗯,要走了,再見。」我說著,並催促她快去晚自習中心報到,千萬別被記遲到。
踏出校門,碰上正在牽腳踏車的李佟恩。
橙紅色的夕暉籠罩住大地,李佟恩淺褐色的頭髮被染上血紅色的光,刺眼得讓我眼球脹痛。
「今天沒和妳那個朋友一起走?」他將腳踏車牽至人行道最裡面的位置,身體靠在紅磚圍牆上,雙手環胸。
我搖搖頭。「她今天留晚自習。」
「春天要過了呢,接下來是夏天了。」
「嗯。」
「就快要進入四月了,學校那棵流蘇樹的花應該也謝得差不多了吧。」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突然提起這個,如同我不能理解徐澈剛才問我的問題
──流蘇花是春天開的花嗎?
是呀,是春天開的花,花期是三至四月。我想起高一經常看到徐澈躺在流蘇樹下睡覺、翹課,忍俊不住,笑了出來。
「笑什麼?」李佟恩似笑非笑的問。
「沒事。走吧。」我說。
理所當然地坐上李佟恩腳踏車後座,迎著微涼的風,回家。
*
當年爸爸外遇,和媽媽每天在家中吵得不可開交。那陣子兩人總是說不上三句話便吵起來,吵到各自火氣足了、找不到稱得上尖酸刻薄的話語質疑對方在這些年婚姻當中的付出了,難聽字眼便自然而然地衝口而出。大抵爸爸媽媽就是要將彼此羞辱得一文不值,大不了離婚。
可是,媽媽忘了。
離了婚,爸爸若運氣好,大可以和他們之間的第三者共度下半輩子。但媽媽就不一樣了,自從與爸爸結婚之後,家中大小事皆由她一手扛起,一整天下來的家事量讓她無暇與朋友相聚,除了一星期一次出門買菜之外,她幾乎沒有什麼戶外活動,久而久之,變成了完完全全的「家庭主婦」。
和外面的接觸愈來愈少,媽媽哪有什麼機會另尋依靠?
「我眼裡啊,就妳爸爸人最好、最值得託付終身。這樣子沒什麼不好呀,反正我這輩子就是跟定妳爸爸了,一直待在家沒關係,因為我等的人是他。」
那時候的媽媽說這句話時,眼裡是滿滿的笑意。
可是她不知道,命運終究是捉弄了她。
在我升上國二的那年春天,有次媽媽到爸爸的公司替他送早上忘記帶出門的便當,進公司時,被公司內的幾位員工調侃了幾句,馬腳就這麼露出來了──
「現在的社會啊,真的很少遇到像妳這麼忠心的老婆囉。」
「但若要比較,還真有點難度啊……」
「裴太太,妳趁早發現還好,瞧妳這發現的時間卡在中間,要早不早,要晚不晚的,想挽回還得多花些功夫喔。」
我不會忘記,媽媽那天晚上是怎麼哭著睡著的。
她問我能不能和我一起睡?我連回答都來不及,眼淚就先從她的眼角滾落。
接下來是一連串的爭吵。媽媽從原先默默地掉淚,到最後與爸爸相互咆哮爭執,有時甚至會摔壞家中易碎物品。而地上的碎片,彷彿是他們的婚姻,不能重來,更無從拼湊。
雖然當時的我已經接近成熟的階段,但看見這樣的畫面,不免有些害怕。
──他們接下來要離婚了嗎?
──這個家分崩離析了嗎?
──我要變成單親家庭的小孩?
──還是我會被爸媽拋棄?
裴流蘇……妳以後會是什麼樣子?
最後我崩潰大哭,奔出早已沒了溫度的房子,甩上門的同時,我再一次聽見玻璃碎裂的聲音在地板上炸開。
「妳在這裡做什麼?」
我是在那時遇見李佟恩的。在我最徬徨、感到最無助的時候。
我並不認識他,他卻來和我搭話,也許是因為當時情緒關係,我壓根兒沒想過問他為什麼要前來關心一個陌生人──哭得很醜,很狼狽的女孩。後來我們成為好朋友,我也沒想過要問起這件事。畢竟過去都過去了,重新提起似乎也沒什麼意義,反而像是炫耀,又或者把別人的關心當作是搭訕女孩子的招數,誤了重點。他是真的關心我。
李佟恩在我生命最低潮的時候出現,也陪伴我走過那段無味時光。
「你覺得,我要跟誰?」我淡淡地問。
說真的,我並不奢望他給我什麼篤定的答案,他不是我,也沒經歷過像我一樣痛苦的事,怎麼能交出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我只是希望有人可以告訴我該怎麼做,或者該做些什麼──講白些,此刻我最需要的就是有個人假裝什麼都懂、什麼都明白都知道,然後陪我說說話,回答那些好像自己也歷經過的答案。
人都是這樣的,需要藉由他人的答案來壯膽。
「妳想跟誰就跟誰吧。」李佟恩聳聳肩,似乎覺得這問題一點也不困難。
也是,對他來說,何其輕鬆?
對我而言,又是何其困難?
「兩邊都是我最親也最愛的家人,怎麼可能說跟誰就跟誰?」
「那麼妳跟爸爸吧,至少以後的日子不會過得那麼苦。」他想了想後說。
「可是媽媽怎麼辦?離婚後她就要一個人生活了嗎?」我皺起眉心,眼眶一熱,鼻尖也忍不住酸澀起來。
「說不定妳媽媽她會回到鄉下和妳外公外婆一起住。」
「那我見她豈不就更難了?我怕我會想她。」
李佟恩挑了挑眉型好看的眉毛,又改口道:「既然如此,跟媽媽一起生活吧。」
「嗯,還是跟媽媽吧。」
忽然我覺得,這似乎就是我想要聽到的回答。
答案早就在心裡面了,只需要有個誰再推我一把。
而李佟恩,就是那個願意朝我伸手的人。
*
「早安,流蘇。」
「嗯,早。」
徐澈的雙腳頓時停在我桌旁。
「怎樣?」我抬頭對上徐澈的眼睛。
他面無表情,淡漠的挑了挑眉,走到我後面的位子坐下。
我聽見他翻找抽屜裡書本的聲音,然後把其中一本抽出來,放在桌上。那本一定是我借給他的數學習作。接著他拉開書包拉鍊,從裡面拿出鉛筆袋,將原子筆筆蓋拔開,在自己的習作上抄寫下我的演算過程及答案。
「裴、流、蘇。」鄧雨莐的氣音吐在我臉上,飄散出火腿蛋餅的味道。「妳的藍筆要暈開了啦。」她用力抽走我握在手中的藍筆。
國文練習卷上一點突兀的藍色墨水由中心向外擴散,像是朵不規則的水花。
「是在恍神什麼啊?」鄧雨莐將藍筆輕輕放回我的桌上,眼睛卻沒離開過我。
「我沒有恍神。」
她「嗤」了一聲,不以為然的點點頭,意思大概是「隨便妳」。
「妳今天為什麼突然跟徐澈說早安啊?」鄧雨莐以極輕的音量問我。
我愣了下,隨即道:「他跟我說早安,我回他,不是合情合理嗎?」
「是啊,可是妳以前都不會,還一副不想理他的樣子。」鄧雨莐嘟起粉嫩嘴唇。
「我有嗎?」我漫不經心地問,重新提起筆。
餘光掃到她正用力點頭。
於是我將筆放下,身體靠在椅背上,雙手環胸,說:「那就是我沒注意到。可以停止這個沒有意義的話題了嗎?」
「流蘇,妳好兇喔……」
我再也忍不住的翻了記白眼。
心煩氣躁。
這是我唯一能夠用來形容今早心情的詞彙了。
下午第一堂課下課,國文老師吩咐我去油印室替他拿下一次段考範圍的練習試題卷。
由於地球暖化的關係,近年來的天氣總是特別極端,尤其是夏天,比以往還早報到,才剛剛踏入五月初沒有多久,太陽一出來簡直炙熱無比,我覺得自己像是要蒸發一樣。
我瞇起眼睛,經過後花園時,看見熟悉的身影躺在流蘇樹下。
徐澈又翹課了。
從油印室回來時,手上多了不少重量。當我再次經過後花園,徐澈還在那裡。但這回他的身畔坐著一個女孩子,汗水從額尖滑落,凝在睫毛上,我看不清那女孩的臉。
「噯,國文老師老愛叫妳做事呢。」
話剛落,我手上的重量瞬間少了一大半。
「我可以拿。」我將剩下的卷子安置在左手臂彎處,騰出右手要拿回李佟恩抱在懷中的練習卷。
而他一個輕閃,彷彿要躲避我根本不費他吹灰之力。「不用。」他說。
「這是我們班的東西,不能麻煩你。」我再次伸出手,而他再一次閃過。
「我當然知道這是你們班的東西。」李佟恩率先邁開步伐,而我追了上去。「如果今天是別人,我就會當作沒看到;但今天是妳,我沒辦法假裝沒看見一個女生在大熱天搬這麼重的練習卷。」他笑得溫溫的,輕輕的,柔柔的。
而我卻不自覺的露出慍色。並不能完全算是生氣,比任何情緒都還要多的是害怕。
於是我停下腳步,皺眉道:「我們是朋友。」
其實,我最害怕的,並不是李佟恩喜歡上我。
我比誰都還要明白維持一段感情有多困難,爸爸媽媽當初也是愛得轟轟烈烈,但最後誰也沒有好過,不是嗎?
早知如此,又何必當初?
我害怕的,是走在一起的兩個人,終有一天會分開。
李佟恩也止了步,過了幾秒鐘後,轉過身,說:「我知道。」然後,他的笑容又深了些。
可是那笑容太刺眼,刺眼到我根本無心注視。
刺眼到,我忽略了太多太多,他有多好。
| FindBook |
有 9 項符合
你擁抱了我的青春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10 |
二手中文書 |
電子書 |
$ 189 |
愛情小說 |
$ 213 |
大眾文學 |
$ 213 |
網路愛情小說 |
$ 237 |
中文書 |
$ 238 |
大眾文學 |
$ 243 |
華文愛情小說 |
$ 243 |
愛情小說 |
$ 243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你擁抱了我的青春
♥ POPO人氣作家馬蘇蘇.暖心淚推──
「看著他們會想起很多年少輕狂,正因為能讓人想起某個誰,才更能感動人。」
/// 我們學會逃避、學會隱藏,在錯的時間橫衝直撞,撞得滿身是傷。
誓言要扭轉命運,可是卻忘了其實我們都只是個十六、七歲的高中生。///
高中階段,正是青春正盛的時候,於是有了這個故事。
我們將青春都留給了對方,回首翻來,處處都找得到彼此的影子。
「裴流蘇,流蘇花是在春天開花的嗎?」徐澈問。
我心頭沒來由一熱,淡淡的應了聲:「嗯。」聲音還有些沙啞。
可惜的是,每個人都有自己應該待著的位置,並非我們想要就一定能夠得到。
「我把我的青春給你/不是因為想換取和你的婚禮/
而是單純在最美好的年華/遇見了你 必需愛你」
這是一場沒有未來的愛情。
原來從我遇見徐澈的那一刻起,這首歌便這麼預言著。
「妳就像流蘇花一樣。」徐澈緩緩說,一字一字說得很輕。
就像開在樹上的流蘇花一樣,勇敢,美麗。
青春跌跌撞撞,而卻在笑淚之中,明白了最簡單的道理──
當我們都把青春留給了對方,就是最可貴的愛了。
你的眼裡始終下著雨,若不是勇敢的人很難闖入。
如果我習慣等你,那麼,是否就要習慣等待你的落寞?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倪倪
紮紮實實的吃貨,只要有吃的一切好說。
此生熱愛抹茶,終其不變。
TOP
章節試閱
【Chapter 01】
人都是這樣的,需要藉由他人的答案來壯膽。
「早安,流蘇。」徐澈特有的慵懶嗓音爬入耳裡。「妳有寫昨天的作業嗎?」
握在手中的筆頓了一下,我頭也沒抬的「嗯」了聲,繼續演算化學習題。
「噯,大家都是同學一場,別這麼冷漠,虧我還覺得妳今天特別美麗,彷彿窗外的太陽閃耀無比……」
我不自覺抬頭瞄他一眼,不過就那麼一瞬間,捕捉到他望向天空的同時,微微皺起的眉心。徐澈將早餐放在桌上,原本緊繃的塑膠袋一碰到桌面,像是洩了氣的熱氣球,發出沙沙聲響。
「其實你只是想抄作業吧……」我無奈地扯了扯唇角,「...
人都是這樣的,需要藉由他人的答案來壯膽。
「早安,流蘇。」徐澈特有的慵懶嗓音爬入耳裡。「妳有寫昨天的作業嗎?」
握在手中的筆頓了一下,我頭也沒抬的「嗯」了聲,繼續演算化學習題。
「噯,大家都是同學一場,別這麼冷漠,虧我還覺得妳今天特別美麗,彷彿窗外的太陽閃耀無比……」
我不自覺抬頭瞄他一眼,不過就那麼一瞬間,捕捉到他望向天空的同時,微微皺起的眉心。徐澈將早餐放在桌上,原本緊繃的塑膠袋一碰到桌面,像是洩了氣的熱氣球,發出沙沙聲響。
「其實你只是想抄作業吧……」我無奈地扯了扯唇角,「...
»看全部
TOP
推薦序
【推薦序】/人氣作家 馬蘇蘇
一開始看的時候,我想像中的故事是這樣的──獨自面對一切的少女,遇見了不羈的少年,那少年是純粹的黑白,隨心所欲地過活,他必會吸引那個彷彿跟他來自不同世界的少女,諸如此類的猜測,最後逐一的被打破。
明明也是看過很多青春戀愛故事的,我卻在看到結局的時候,有些意外,這個意外並不是覺得「怎麼會這樣」,相反的,整個故事的元素和事件都是可能發生在你我周遭,合理而熟悉的事件,加上這些鮮明的角色,就能理解作者安排的用意了。
我把我的青春給你,這是少女對少年說的話,亦是一首動人歌曲最清...
一開始看的時候,我想像中的故事是這樣的──獨自面對一切的少女,遇見了不羈的少年,那少年是純粹的黑白,隨心所欲地過活,他必會吸引那個彷彿跟他來自不同世界的少女,諸如此類的猜測,最後逐一的被打破。
明明也是看過很多青春戀愛故事的,我卻在看到結局的時候,有些意外,這個意外並不是覺得「怎麼會這樣」,相反的,整個故事的元素和事件都是可能發生在你我周遭,合理而熟悉的事件,加上這些鮮明的角色,就能理解作者安排的用意了。
我把我的青春給你,這是少女對少年說的話,亦是一首動人歌曲最清...
»看全部
TOP
作者序
【後 記:跌跌撞撞的青春】
Hello大家好,我是倪倪。
《你擁抱了我的青春》差不多是在我高一的時候完稿的,從簽約到真正出版,不知不覺過了一年多,在這期間,我從期待、興奮,一直到後來開始擔心這個故事會不會其實並沒有那麼好?是不是還有哪些部分需要再多做描述?
於是前前後後又經歷了不下百次的修稿。
是的,連結局也不一樣了。
在這邊跟大家透露一下好了,最初的設定,是要讓流蘇和徐澈有情人終成眷屬的,但沒想到我愈寫愈歪,不知道是不是我本身是個寫不出happy ending的體質,所以整個故事的走向愈來愈虐……
所以說大綱都...
Hello大家好,我是倪倪。
《你擁抱了我的青春》差不多是在我高一的時候完稿的,從簽約到真正出版,不知不覺過了一年多,在這期間,我從期待、興奮,一直到後來開始擔心這個故事會不會其實並沒有那麼好?是不是還有哪些部分需要再多做描述?
於是前前後後又經歷了不下百次的修稿。
是的,連結局也不一樣了。
在這邊跟大家透露一下好了,最初的設定,是要讓流蘇和徐澈有情人終成眷屬的,但沒想到我愈寫愈歪,不知道是不是我本身是個寫不出happy ending的體質,所以整個故事的走向愈來愈虐……
所以說大綱都...
»看全部
TOP
目錄
推薦序
楔 子
Chapter 01
Chapter 02
Chapter 03
Chapter 04
Chapter 05
Chapter 06
Chapter 07
Chapter 08
番外一:候鳥未歸
番外二:輕輕地記得
後 記:跌跌撞撞的青春
楔 子
Chapter 01
Chapter 02
Chapter 03
Chapter 04
Chapter 05
Chapter 06
Chapter 07
Chapter 08
番外一:候鳥未歸
番外二:輕輕地記得
後 記:跌跌撞撞的青春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倪倪
- 出版社: 要有光 出版日期:2018-07-19 ISBN/ISSN:9789869632164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22頁 開數:14.8*21 公分
- 類別: 中文書> 類型文學> 大眾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