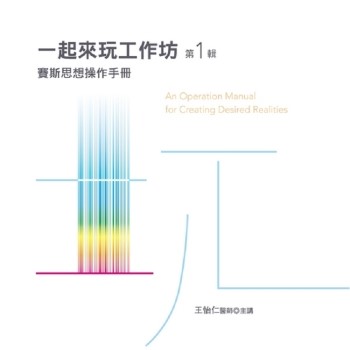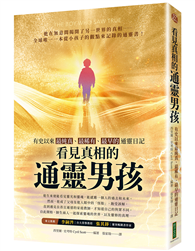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10 項符合
花給樹梢染上絢爛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10 |
二手中文書 |
電子書 |
$ 196 |
愛情小說 |
$ 221 |
大眾文學 |
$ 221 |
現代小說 |
$ 246 |
中文書 |
$ 246 |
大眾文學 |
$ 252 |
現代小說 |
$ 252 |
愛情小說 |
$ 252 |
文學作品 |
電子書 |
$ 280 |
現代言情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Readmoo 評分:
圖書名稱:花給樹梢染上絢爛
罪惡感是一棵大樹,黑色的大樹。
最後,整棵樹,包括樹葉,全成了黑濁一片。
「大叔──大叔──從今以後我就要住在這裡了,請大叔多多指教啦。」
十九歲少女趙一冬,在滂沱大雨的夜晚闖進大叔俞斯南家中,藉故成了房客。
她一點也沒變,俞斯南忍不住想著。她仍是那個稚氣未脫的小女孩,閃著清澈的目光。
隨著日子過去,她逐漸挖掘出大叔不為人知的一面,
趙一冬就像絢爛的煙花,在大叔終年被陰霾籠罩的心中,點亮閃爍般的希望。
趙一冬不知道的是,大叔的心裡就像她一樣,也有著一棵樹。
一棵被黑暗緊緊纏繞的樹。
比起趙一冬心中的樹,俞斯南的更顯黑暗可怖。
「那是收據,證明我把靈魂賣給她了──我的人生,我的所有一切,都是她的了。」
無論俞斯南再怎麼努力忽視,
卻還是不自覺被那棵樹牽引著,最後傷害自己、也傷害他人──
趙一冬只能在心中默默期許著:
願到了最後,所有人的心都能被煙花染上絢爛的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