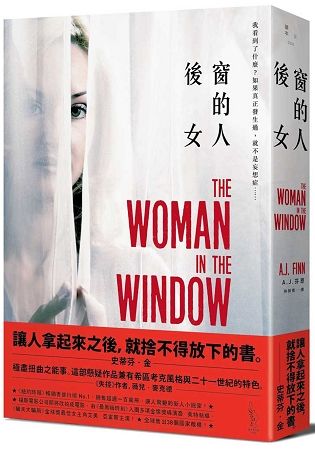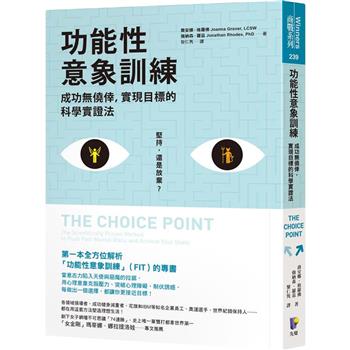我看到了什麼?
如果真正發生過,就不是妄想症……
如果真正發生過,就不是妄想症……
安娜.福克斯,恐曠症患者,獨自定居紐約市,無法踏出家門。她白天開始喝酒(可能喝太多)、 看黑白驚悚老片、和相隔兩地的老公和女兒講電話,另外就是:偷窺鄰居!?
後來對面搬來羅素一家:這家人有父親、母親和一個青春期的兒子,就像所謂的完美家庭,彷彿安娜一家的倒影。有一天晚上,安娜跟每天一樣,用相機窺視窗外的世界,卻看到不該看的景象!從那時起,她的世界開始崩壞,所有的祕密傾巢而出。
什麼是真的?什麼是她的想像?究竟誰有危險?到底誰才握有掌控權?在這本小說中,沒有一個人、沒有一件事是表裡如一。
隱晦曲折又震撼人心,獨樹一格又動人心弦,《後窗的女人》是鋪陳巧妙、精緻複雜的驚悚懸疑小說,只要一翻開,就無法停止閱讀,直到最後。
令人聯想到希區考克最精采的作品《後窗》!
本書特色
★《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No.1,銷售超過一百萬冊,讓人驚艷的新人小說家!
★福斯電影公司即將改拍成電影,由《最黑暗時刻》入圍多項金像獎導演喬.萊特執導,《瞞天大騙局》金球獎最佳女主角艾美.亞當斯主演!
★全球售出38個國家版權!
★鋪陳巧妙、曲折離奇,具有強烈希區考克風格!
文壇名家熱烈推薦
《後窗的女人》是少數讓人拿起來之後就捨不得放下的書。文字流暢,獨樹一格。芬恩以黑色電影為背景,創作這個獨特故事的手法既吸引人又教人不寒而慄。──史蒂芬.金
令人吃驚。充滿刺激。有意思又不可思議。我還可以再穿插更多形容詞,但是諸君應該已經了解我的意思。芬恩為新千禧年創造了一個懸疑故事,故事中有迷人的角色、出乎意料的轉折、優雅的文體,我也想和敘述故事的主人翁共飲一瓶梅洛紅酒,也許兩瓶吧,因為我有好多問題想問她。──《控制》作者,吉莉安.弗琳
極盡扭曲之能事。這部懸疑作品兼有希區考克風格與廿一世紀的特色。──《失控》作者,薇兒.麥克德米
了不起,令人著迷,實在太棒了!──懸疑天后泰絲.葛里森
不同凡響的處女作。故事緊湊,引人入勝。鋪陳聰明、情節揪心,而且非常可怕。──《重返人間》作者,妮基.法蘭齊
《後窗的女人》就像是經典希區考克電影的小說版,我幾乎想看看有哪些卡司。故事懸疑,字裡行間危機四伏,文字優雅。這本書充滿刺激,而且每個鋪陳都別具意義。──《Sanctus三部曲》作者,西蒙.托恩
了不起,好一本文筆優美的驚悚小說。我打從一開始就喜歡福克斯醫生,故事的轉折完美精緻。很難看到這麼引人入勝、文采洋溢的故事──每一頁都透露出希區考克的氛圍和品味。這麼說實在老套,但我真的是在家無論走到哪裡、或應門、或用餐,都捨不得放下這本書。──《鄰居家的上帝》作者,喬安娜.坎儂
緊湊、精采,令人難忘;下筆精準,涵蓋層面寬廣。──《夢幻婚禮》作者,珍妮.寇根
芬恩將我徹底拉進《後窗的女人》的世界,我闔上最後一頁之前,幾乎大氣都不敢喘。脆弱的主角安娜沒有朋友、家人,自外於鄰里、真實世界。這本動人心弦、引人入勝又令人回味無窮的小說,絕對會在二○一八年緊緊抓住讀者心弦。──暢銷書《Lying in Wait》作者,莉茲.紐根特
自從二十五年前史考特.史密司的《絕地計畫》之後,再也沒有這麼精采的驚悚處女作。《後窗的女人》引人入勝、揪心,更刺激得教人頻頻屏息──讓我驚嘆不已。──紐約時報暢銷書作者,喬.希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