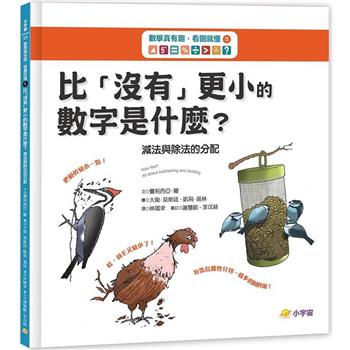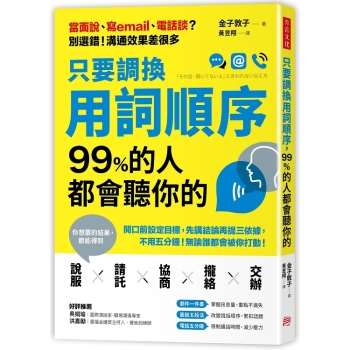春禧殿裡光線幽濛,冷宮不比正主子們待遇,大暑天不得冰塊,悶燥使人呼吸難受。楚鄒叫小榛子把官帽兒八仙椅搬到廊簷下,看對面殿頂上幾隻角獸遙遙,瞇著眼睛,手上刻刀不停。
小劉子背著楚恪在台階前放下,一襲垮腰小袍子壓得皺巴巴的。楚鄒看也不看他,輕叱道:「爹都不領回去的孩子,總來我這兒礙眼做甚?」
楚恪最怕人提爹娘,便囁嚅著小嘴討好他,「我給你帶糖吃來了。」把腰上別的小荷包打開,裡頭是三枚方塊小梨花糖。米白色晶瑩剔透的,還可看見細碎的梨花瓣。楚鄒不屑地看一眼又收回眼神,楚恪只好自己先掏出一塊舔了舔,作一臉繾綣地說:「是她給的,那個小宮女。」
這陣子他總來找他的四叔,他的四叔早前不搭理他,後來發現只要提起那個小宮女,他的四叔就會默默不說話地買他面子。楚恪於是就總叫小劉子把自己背去衍祺門裡頭找陸梨。當然,陸梨問他的那些話,他一古腦告訴他的四叔了。
果然楚鄒頓了頓,便不說話。
楚恪試探地掏出一塊梨花糖,一塞,便塞進了他四叔兩排潔白整齊的牙齒裡。
午時的光景,日頭當空,御花園那頭正在辦慶功宴,到了這會兒膳房卻沒把吃的送過來。
片塊的梨花糖在口中化開,清潤中夾雜著蜜桃的甜香。把梨花與桃汁混合,宮裡頭的太監可沒這心思。那香甜向五感滲透,楚鄒不自覺吮了一吮。男子硬朗的喉結跟著動了一下,把兩歲的楚恪看得滿目崇拜。
楚恪比劃著小手說:「她又問起你了。」
奶聲奶氣的,天生早慧的小孩,這是他一貫的開場白。其實陸梨可沒問過他幾回,一是不好太多問,二則尚服局活兒可忙,可沒什麼時間陪他瞎閒聊。
問一句:「世子爺有幾個皇叔吶?」
楚恪自動把話一傳,就成了:「她問,你是第幾個皇叔。」
隔兩天再問一句:「世子爺怎不去和你小四叔玩吶?」
到楚恪嘴裡又成了:「她問我,你在和誰玩。」
好麼,一個才進宮的小宮女,卻對一個素未謀面的冷宮廢太子心心念念。話聽進楚鄒的耳中,一次兩次,便生出了奇妙。楚鄒時常浮想那日看到的陸梨身影,似曾相識的長開的眉間眼角,那看向自己的眸瞳裡帶著寧靜而飄遠的光芒,叫他實在無法解釋得清。
楚鄒抿了口梨花糖,閒淡地仰靠在椅背上,「哦,今兒又問了我什麼?」
楚恪舔著嘴角,「她叫我說你……不吃飯,臭毛病多。」
呵,楚鄒諷蔑地扯了扯嘴角,清瘦的肩膀被幾聲咳嗽震顫,「那她又在做些什麼?」
楚恪答:「她撚花汁,偷花兒,藏袖子裡。」跟著學了動作,他的四叔每回總會問這一句,他就把看見陸梨做的事都告訴他。比如她寫幾個字就換作左手,她還愛給人塗嘴唇。
撚花汁,藏花瓣……楚鄒聽了便不說話,腦海裡又浮過母后宮中踮腳偷花的小太監,默了默,只問道:「你可知她叫什麼嗎?」
「怒泥,她問你的小阿嬌了。」楚恪把小臉蛋貼著楚鄒的手肘,父王總不來接自己,他想有那種像爹爹的感覺。
什麼破名字,這樣難聽,楚鄒皺了皺眉頭。正說著,牆外傳來幾聲嗚努嗚努的狗吠,隱約聽見少女的低聲輕喚。楚恪便虎了臉,轉向他四叔,「瞧,她又偷看你來了。」
楚鄒聽得動作一滯,那僵硬多年的心忽然便有些緊張。
咸安門外青灰色磚石浮塵,胖狗麟子叼著陸梨的裙裾滿地撒潑打滾。
「欸……」陸梨走不得,搡著牆根,就這麼毫無準備地跌進了咸安門。
第三章 昔日嬌影
院子裡烈日灼曬,耳畔能聽見蒼蠅嚶嗡叫響,她有些茫然地站在台階下,便看到那荒草深處一座孤立的春禧殿,楚鄒著一襲墨藍團領袍,正橫坐在殿匾下的靠椅裡,長條條的像一張畫。
陸梨便躊躇著不知進退。守門的老太監過來,見她懷裡抱著木盤,只當是浣衣局打發過來的新宮女,便吭哧道:「甭掙扎了,這狗護主子,必是看妳們兩天不來收拾,這便著急上了。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再不濟總歸是個主子,不興這麼把人怠慢。」說著自己在前頭引了幾步。
竟然是楚鄒養的狗,他那樣不耐煩的性子幾時也有了這興致。陸梨有些意外,只好躬了躬身子,硬著頭皮往裡隨。
藍綠漆花的廊簷下偶有細碎小風,兩歲的楚恪早不知藏到哪兒去了。她抬腳邁上台階,看楚鄒一個人背對而坐,便悄悄屏住呼吸。楚鄒只是旁若無人地雕刻著,十八歲的臉龐甚俊美,留給她一道肩展脊瘦的背影。陸梨暗暗鬆了口氣,連忙快步走進去。
那風帶走一抹柔香,楚鄒這才不自覺地用眼角睨了睨。
殿內光線幽暗,烈日在這個沒有遮擋的西北角顯得尤其地曬。正中央是他的櫥櫃,上面擺放著許多木雕,小的拳頭大,大的也不過手掌高,卻都雕刻得栩栩如生。東端間是他的書桌,往日主子們的月牙下必垂著刺繡簾子,鏤空處也被擦得油光發亮,他這裡卻都是晦舊沾著灰。桌面上堆著一叢筆墨字畫,給人的感覺怎麼都是清苦。
陸梨打量著,心裡便湧起酸楚。骨子裡帶出來的心疼,見不得他過得這樣不好,臉上卻不動聲色,只是轉而去西端間收拾他的衣物。
一道轉門邁進去就是他的床榻,榻前是拖鞋的青磚,對面是洗臉的架子。床後有衣帽架,他對規矩甚講究,脫下的鞋襪放在最底層,衣服掛上頭,褲子掛中間。不像二皇子楚鄺,一古腦兒地堆在一塊,由著下人們去拾掇。
陸梨把衣物疊好放在盤子裡,看見床上被子也沒疊,忍不住就想過去瞅兩眼。卻只有一個樸素的枕頭,枕邊有他的中衣,並無任何女子的物件。她悄悄往床底下看,那床底下也塞不了人,更沒有女人的鞋拖,心裡不由納悶,又假意給他把被子掖了掖。
楚鄒一直打量陸梨的動作,看著她習慣性的把右邊袖子先折,習慣性地把中衣疊放在中間,似乎又要去整理他的枕頭了,他忽然想起那枕下的小衣,連忙出聲道:「這些不用妳,待小榛子暑氣一退,自有他歸整。」
少年變化了的嗓音,帶著皇室特有的貴氣。陸梨手一抖,這才曉得楚鄒一直在關注自己,忙轉過身來一福,「是,殿下。」
忍不住看了眼楚鄒。這年他十八了,都是青春正好的年歲。許久不曾再見,幾許陌生摻雜。
都有些局促。後來楚鄒就說:「我這裡晦氣,衣裳拿了,妳就可以走了。」忍著胸腔裡的咳嗽,把老舊的宮梁、器物一瞥,沒了昔日那可威風的榮耀。他的眼神黯淡下來。
「好。」陸梨聽了心裡可痛,到底狠下心來叫自己離開。
只這掠身而過,卻看到楚鄒腰帶上掛著的荷包,那藍綠線刺繡的小麒麟與黃柿子太醒目,不由意外地頓了頓。楚鄒眼目銳利,自然注意到她的視線,低頭看了一眼,只是沒說話。
黃毛胖狗見陸梨要走,很是不甘地追著跑。楚鄒盯著她聘婷的背影,忍不住蠕了蠕嘴角,在她身後輕輕叫了一聲:「麟子。」
陸梨腳下不經意一頓。狗搖著尾巴過去,楚鄒收入眼底,只默然地伸出手蹲下來,「銀子掉在我宮裡也不要嗎?」
陽光下光芒刺眼,陸梨狐疑地回過頭,看到他手中攤開的一枚小鐲。
楚鄒盯著她絕色的臉,「牠方才蹭掉了妳的手鐲,待我修好了,妳自己來取。」
陸梨這才發現腕上的鑲玉銀鐲不見了。那聲「麟子」叫得太輕,她也不曉得是不是「銀子」。
她便溢出笑臉道:「那鐲子廉價,怎好勞動殿下修補,交給奴婢自己串就好了。」
聲音那樣靈動,聽得楚鄒目中忽然一酸,陸梨話音未落,他人已經起身往殿內走了。
俊瘦的背影孤獨一長條,陸梨叫他「殿下」、「殿下」,他也好像頑固沒聽見。
沈嬤嬤端著熬好的米粥從後頭過來,乍看見庭院中間朴玉兒一張俏生生的臉,嚇得兩手一哆嗦,那瓷碗便連帶著整碗的粥碎了地。陸梨不知所以,連忙迎過去幫著收拾,「嬤嬤可是看見了什麼,為何這樣緊張?」
越問沈嬤嬤越勾著頭抖顫不止,她便只好鞠個躬,三步兩步地跑出了咸安門。
去到浣衣局,大中午的局子裡沒什麼人,倒好,把楚鄒衣物往水盆裡一擱,便轉身溜走了。
日子如白駒過隙,十七那天慶功宴後,皇帝又寵幸了孫凡真,自此今歲身家相貌最出挑的兩個淑女便都得了幸。緊接著兩廣那邊的仗也開打了,倭寇狡黠,不大規模同大奕水軍打,很是費神與精力,所幸東北面捷戰告停,勉強維持了拮据的朝政開支。謖真王有意要入京求和,聽說高麗內朝也在爭執,一半主張繼續投靠謖真,一半主張繳納貢品與貢女歸附大奕。楚昂對此沒有表態,他要的是齊王,無論是謖真還是高麗,結果只是把人交出來。
然而山西那邊的邪黨卻不容樂觀,西南面的乾旱使得他們擴張迅猛,並起了個「白蓮教」的名頭。教民們臂上紋白蓮戴白巾,在各地建立庵堂傳道起義,風波鬧到京城裡來,一些大臣甚至宮裡的太監都被洗了腦。這段時間,司禮監大總管戚世忠都在忙這事,聽說東廠的番子在各地到處捉拿人,但凡看見戴白巾的都抓起來,嚇得民間辦喪事都改成戴黃麻了。人人如驚弓之鳥,談白蓮教色變。
大奕王朝在天欽十四這年經歷著一個艱巨的考驗,皇帝楚昂時常一個人坐在坤寧宮裡,久久地靜坐不語。除了必要的召幸,夜裡幾乎都只宿在康妃的承乾宮,皇后去世這些年,後宮唯康妃一個久持著這樣的隆寵。
但宮女和奴才的日子還是照舊過。五月二十那天,尚宮局貼出了告示,六局要考試,二十歲前的都可以參加。陸梨叫喜娟陪著去看的,告示貼在西六宮那頭,不僅六局,樂工局、舞坊都招考,熙熙攘攘圍著一群人。尚食局是個吃香的衙門,統共招的就十六個,報名的得有五十多,陸梨也報了名。
張貴妃罰她給楚鄺拾掇衣裳,雖是得臉的差事,到底是個辛苦的力氣活兒。每日整好的舊衣,得和粗使宮女一塊扛去白虎殿前的儲衣庫。皇子公主們的舊衣裳都送到這裡,由尚衣監的太監們歸整後安置。
通常幹完當日的活,送過去差不多就是傍晚夕陽西下了。那當口各門裡都在忙碌,陸梨趁粗使宮女和太監清點件數的時候,曾悄悄去看過從前住的破院子。
一堵矮破的老紅牆,清清幽幽的,牆下紅門上了把舊銅鎖,裡頭似乎有綠枝探出來。風一吹,樹葉搖一搖,打哪兒冒出來的新鮮綠枝呢?後來有一回似被人看見了,在背後吼了聲「唏,見鬼了」,她就再也沒敢去瞧過。
半夜裡似乎落過幾滴雨,乾涸了多少天的地板終於溢出點濕氣。清早的衍祺門內,三五個宮女分作一堆,用石臼搗著花瓣。搗出的花汁原漿用細紗布過濾,再拿去給上料的太監們處理。待陽光下曬出了雛形,便還用細紗布一層層覆上去。那紗布是事先裁剪好的,宮女們拿在手裡,用開水燙軟了晾到半乾,這時候覆上去才容易吸粉。
陸梨一邊用水燙著,燙完了又用熨斗輕輕軋一回,再放回去過一遍水。她做這些事總是很認真,功夫入到細微之處,心裡卻在矛盾該不該去楚鄒那兒把鐲子拿回來。
大約受了陸安海的從小教化,她過日子總是省算。吳爸爸給她的銀票她分文未動,全給他帶了回來,自己攢下的三百兩銀子用來買了死口,南下逃荒時恰與一戶姓陸的人家同行,那家夫婦在路上病死了閨女,和自己一般大年紀,半路上死了沒法銷戶籍,她就跪下來求續了身分。
一路作伴,那夫婦看她乖巧伶俐,又聽老朱師傅說是個撿來的可憐娃兒,便欣然答應下來。原本是想許配給自個兒兒子的,後來老朱師傅病逝,陸梨執意要入宮,遂便作罷。如今去查,查到底,她也是那戶陸姓人家的閨女。
餘下的錢她便省著花了,老朱師傅一輩子在灶膛上捏麵,得的打賞可不及她壓歲錢多,那恁大的肚子裡原來裝的是一顆瘤,先頭在宮裡沒心思在意,出宮後安逸下來,那病就颼颼地犯了。陸安海的許多積蓄都被用來看了病,後來又買了兩塊好墓,便所剩無幾。女孩兒家家也愛美麗,她去首飾攤上買來碎玉、碎珠子自己串著戴。想要什麼式的便編什麼式,倒不比那攤上叫賣的差多少。那鑲玉銀鐲可是她最喜歡的一條,可偏被他楚鄒拿去了。
她想他那天同自己說話的一顰一言,應該也不像認出自己,就是自己怕去多了,慢慢又放不下他。
古華軒下,掌事嬤嬤便看著陸梨忽而把紗布浸潤水裡,忽而又挑出來熨熨,眉眼飄忽甚遠。最近這批胭脂唇紅裡頭出了一撥蹊蹺,往年的成品沒得比較倒也覺不出什麼,這批次裡卻有一撥出挑的,紗布汲顏色甚好,亦更柔軟貼合肌膚,頭批送去給幾宮主位用了,連張貴妃、康妃那倆挑剔的角兒也都不住嘉讚。從來都是西六宮那三局得的賞賜多,掌事嬤嬤這回竟也稀罕的得了賞賜,心裡不自禁納悶,這兩天便杵院子裡觀察,觀察來觀察去便在陸梨這裡看出了古怪。
見她似乎魂不守舍,末了便叫奴才去把她喊過來。
「梨子,叫妳了。」太監踅到石臼跟前擺了下手臂。
陸梨這才恍然回神,見那邊嬤嬤在看自己,連忙擦擦手走過去,「嬤嬤找陸梨何事?」
搭腕間一禮,把宮廷規矩做得恰到好處。
掌事嬤嬤板著臉,盯著她的手問:「那紗布是怎麼回事,為何過水了又熨一回繼續浸水裡?須知咱們尚服局的忙碌,存心閒磨功夫的婢子該送去尚正處嚴罰的。我見妳素日乖巧勤快,也不似這樣的混子,妳便給我說說理由。」
陸梨回頭看了看,愣了一剎才明白嬤嬤在說什麼。她做胭脂膏兒的技巧盡是李嬤嬤教的,那紗布上沾毛,便用開水燙了也除不盡,有礙胭脂的附著,但若燙後在熨斗下一過,再浸一回水就變得綿柔貼合了,聞此,連忙把理由一說,末了謙聲道:「是陸梨自作主張了,請嬤嬤責罰。」
掌事嬤嬤不動聲色地聽著,瞧她身段生得一等一,臉也長得美妙,叫人過目不忘。
在宮裡頭熬久的人眼睛都毒辣,現下既被貴妃調去當差了,她猜著這丫頭早晚怕是留不住,便慢聲道:「費了心的自該落得表揚,不怪貴妃、康妃娘娘誇著好。我見妳近日精神頭不濟,聽說是報了尚食局的名兒。妳自進宮來便事事上進,既是有心從這裡出去,我也不好留妳。今後要練那膳食上的功夫,便去後頭的茶水屋吧,裡頭有個爐子歸妳使,但不許弄出煙霧來,影響了其餘的局子,我也不好交代。」說著便站起身往台階上走。
陸梨詫異抬起頭,還以為必然要被責罰,不想竟是給自己騰了空間,連忙叩頭謝了恩典。
這之後除去當差,她便有了鼓搗的空間。不讓弄出煙霧,那煎炸一類便免了。夏日的天,切一掊冬瓜丁下鍋一煮,加幾顆冰糖晾涼了往嬤嬤跟前一端,還能駁她兩回笑臉。再把麵粉裡和了香芋,隔水一蒸,便成了粉紫甜糯的芋糕。
一塊當差的姐妹有口福了,好嘛,沒幾天那咸安宮裡的狗也嗅著鼻子跟過來。陸梨起先不管牠,看牠老實巴交杵在門下看,鼻子眼睛烏泱泱的,她心一軟,就給牠扔下去了兩塊。牠嚐著好吃就賴著不肯走了,瞅見陸梨把剩下的打包在矮几上,兩爪子蹭上來,叼了就往咸安宮那頭跑。追也追不上,沒命了似的。
盛夏的天,荒草叢裡蚊蠅多。給的驅蚊香不頂用,蚊帳裡整夜整夜地鬧大戲,楚鄒夜裡睡不著,漫長的白天便容易入了魘。
那夢中氤氳,似又看見四歲那年的母后,笑盈盈用牙籤挑開自己的嘴,又看見乾清宮裡父皇夾到碗裡的荷葉肉,還有那個小太監軟乎乎蹭在臉上的腳丫子,連他也陶醉。忽然手背就被濕濕地一碰,他猛然從夢中驚醒,那狗嘴裡叼的食物就成了他在這個夏天的慰藉。
那小點小點捏成的食兒,送得不頻繁,不夠打牙祭。時而是三兩塊水晶蘿蔔糕,時而是幾個冬瓜盒子,她像把食物也當作如他母后手下的瓷瓶,變作了一種陶醉的藝術,做得精緻又爽口。院子裡一顆野生的番茄結果了,沈嬤嬤用果子給楚鄒煮了清湯,那略帶酸甜的湯汁就著點心吃下去,味道便入了楚鄒的心。
陸梨也不再是從前的小麟子了,她在宮外頭又新學了許多本事,也學會了藏小心眼與防人,並不把從前陸爸爸和李嬤嬤教會的廚藝那麼輕易地露出來。楚鄒吃著依稀有幾分熟悉的味道,卻又不全然一樣,他便猜不出她到底是不是。
只在夜深人靜時,再回想那日她匍在床沿替疊衣裳的一幕,他在少年時死寂了的心,便又開始有了一種對於暖的奢望。
掉下的手鐲成色簡單,在宮廷御俸中長大的皇子爺眼裡,是入不得眼的,可他那天也不曉得怎麼了,就是不想還給她。街邊的碎玉石間隔著銀珠子串成,用細棕繩編了花樣,鬆緊環應是被那蠢狗蹭掉了。楚鄒便叫小順子給自己弄了條同色的繩子,又用香楠木給她在尾端磨了兩個木珠子,這般綴上去就不怕再掉了,還顯得更好看。
他練字疲累時將那珠子撚在手心,淡淡的冰柔,這感覺像什麼?就好像從前在聖濟殿裡寫字,那小太監滿目崇拜地貼著他的手背站,臉蛋軟乎乎、呼出的氣也柔乎乎,生怕他一個錯神不把字寫歪了似的。
熬了一個通宵才磨好,滿心期盼又惴惴地等待陸梨來拿,但陸梨卻是真的不來了。
他等了她數日不見,心中便又升起那股隱匿的自我卑棄,越發渴望能再一次見到她,不管是與不是,總要把答案弄清楚。
老三在五月二十三那天回了王府,進宮來抱孩子,順道過了咸安宮一趟。在京郊別苑照顧王妃一個多月,看起來瘦了許多。兩歲的楚恪趴在他肩頭上抹眼淚,他就輕輕地拍了拍兒子的小脊背,臉上都是憐愛與奔波的倦憊。
見了楚鄺一面,兄弟兩個也沒什麼話,孩子哭累睡著了,楚鄺迷迷糊糊逗弄兩下。楚恪也不識得楚鄺,楚鄴便照常問了幾句傷勢就走了。
等他到楚鄒這裡時,楚鄒正在練箭,修頎的身軀顯得沒精打采,楚鄴看一眼便曉得他有心事,告訴楚鄒說父皇又瘦了,聽說整夜裡咳嗽,一直是錦秀在身邊照顧。今歲北京城天氣熱得詭異,反倒南京那邊時有下雨,便是父皇真的有心移駕南都,這京城裡莫非叫老二與貴妃坐鎮嗎?你倒是真想償還你小九弟。
楚鄒沒應,想起回憶裡的那麼多,心下湧起痛苦與酸澀。只問了一句「那天你說的那個宮女呢」,楚鄴才見兒子,這會兒可不曉得他心裡惦記了啥。還以為他寧可找個宮女下台階,也不肯把「小麟子」送走,末了無奈道一句「被貴妃要去了,怕暫時不好弄過來,要麼再換一個」。
楚鄒想起陸梨那討人疼的模樣,臉就陰下來沒說話,也沒叫老三把狗領走。
後來他便養成了個習慣,只要那扇掉漆的宮門有動靜,便抬眼望那邊看。
幾日下來,下頜上便長了青茬。月底刮臉的老劉師傅拎著箱子晃悠悠進來,身後跟著被調到剃頭差事上的小太監王根生。老劉叫王根生拿廢太子爺的臉兒試刀子,小半時辰工夫,便見楚鄒眼睛往門那邊看了三四回。也怪,這位爺從十四歲起就像個死人樣,宮牆塌了也沒見他抬眼皮,如今倒是回了魂,一隻壁虎都能叫他分神。
給主子爺刮臉可是件人命關天的大事,王根生頭一回操刀子,一個差事下來就濕了半身汗,轉頭去找劉廣慶一說,劉廣慶最近在延春閣裡給七皇子當差,七皇子不得寵,住的院子邊上全是一幫太監。話一傳出去,廢太子爺精神怕是愈恍惚了,神神鬼鬼哩,鎮日個魂不守舍陰晴不定,刮個臉都坐不穩。
聽到皇帝的耳中,那批閱奏摺的筆墨便在中途頓住。康妃錦秀瞅見了憂心,忙叫給傳個御醫過去看看,不說還好,說了楚昂的臉色便愈加陰慍。那小子的秉性他又豈會不懂,順者昌,逆者亡,眼睛深處斂著常人沒有的堅毅……怪只怪自小對他太放縱。
楚昂是為什麼把楚鄒圈禁的,他最清楚,楚鄒叛逆不知悔改,楚昂便叫他把苦參透。那是楚昂答應孫皇后的約定,是為大奕王朝的後儲之力,斷不能如他這般性子繼續胡為。
但這麼多年幽禁,卻似對他並無改益,傳來的反倒都是不好的消息。
入夜已深,楚昂眉宇凝重地走去龍榻邊,錦秀便過來替他寬衣解帶。她在他眼中始終是除卻自己便一無所有的婢女,他在她這裡容易得著放鬆。後來錦秀便建議說給楚鄒施針安神。
乾清宮裡當差站班的都是三頭六臂,話一傳開,隔天送往咸安宮的飯菜就又酸了。
那飯菜任它變作什麼味,楚鄒早已都是麻木。聽說後來施針的太醫被他一棒子扔過去給趕了。
大晚上打雷烏壓壓的,老太醫帶著徒弟穿過兩排荒草而來。楚鄒本正在寫字,待一抬頭看到老太醫手中的銀針,頓地鳳目一凜。那老太醫還沒把針燙完,手一抖,腦門上就正正地砸過來一塊雪松木。
繼而楚鄒便掃了桌案上的紙墨,臉龐隱在昏濛的光線下,磨著唇齒說:「叫她莫要再費那番周折,真要叫本皇子死,但求父皇賜下一杯鴆酒罷!」
太醫回頭把話一傳,皇帝在乾清宮裡氣得又是當場一陣咳嗽。錦秀便連忙換上一襲素衣裹身,戰戰兢兢地長跪在宮門外不敢起。正在擷芳殿上課的九皇子聞知消息,匆匆地趕過來也一同在漢白玉台階前跪下,求請父皇莫要因為四哥而牽責康妃的好意。那八歲的孩子,當真叫人看了心生憐恤,前朝關於廢太子的爭議便又不好了。
消息傳到景仁宮,張貴妃便都是冷笑,呵呵,笑她錦秀做得一手苦肉好戲。然而她雖冷眼看著錦秀做戲,到底卻是樂見楚鄒這般鬧劇的。
張貴妃便也跟著賣乖做了好人。這陣子宮裡頭生出鬧鬼的傳聞,只道在從前那個小太監院外看見閃過一道綠影,怕不是那幽魂死不瞑目,隔了幾年又滲回來攪擾廢太子的安寧。
張貴妃便想起了楚鄒四歲那年的一場法事,求請皇帝在宮中又重新做了一場。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太子妃花事記(卷三):似是故人來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67 |
二手中文書 |
$ 213 |
華文羅曼史 |
$ 213 |
言情小說 |
$ 213 |
古代小說 |
$ 237 |
中文書 |
$ 243 |
古代小說 |
$ 243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太子妃花事記(卷三):似是故人來
假死逃離皇宮的小麟子回來了!回復女兒身,藉著秀女選拔再次回到了有楚鄒在的深深皇宮。她回來的原因除了報仇,還有為了多年未見的故人們……
晉江名家[玉胡蘆]細細述說紫禁城內的宮闈秘事,文辭細膩,讀來令人如歷其境、如聞其人。
當年的點膳小太監如今成了皇帝的窈窕秀女,
她的真實身分,他知、他也知,卻是這宮牆內──最不能說的秘密。
陸梨回來了,帶著不甘與找尋真相的意念回到會吃人的深宮。沒想再與楚鄒有所牽扯,卻總是情不自禁地追尋他的身影,捨不得這人再受冷落欺凌。
是註定糾纏不清的命呢。被半迫著、也是不捨他孤苦多年,她便隱晦地認了陪伴他多年的小太監正是自己。
楚鄒便痴了、纏了、黏了,原以為早已死去的心又漸漸活絡了過來,為著疼他的早逝娘親,為著身邊親仇待報的人兒,他如潛龍方醒,又逐漸升為東邊閃耀的一顆星。
可擋在前頭的不只皇子兄弟,還有佔據父皇身邊的妃子與暗處掌著大權的小人,如何不打草驚蛇地復甦壯大,他需得隱忍、更隱忍……直至復得那個位子的那一日!
作者簡介:
玉胡蘆
作者玉胡蘆,久居福建東南隅,射手座,喜好隨性,思緒天馬行空。私認為寫文是一種修煉,同時亦希望筆下故事得到你的喜愛,看完若能留於心中,則為榮幸。本篇《太子妃花事記》源於一次故宮之行,在完結後又動筆了現言《非正式戀愛》,不同風格,期待閱讀。
繪者
殼中蠍
微博:殼中蠍
twitter/tumblr:sasorainster
暱稱是蠍子~喜歡畫畫、看劇和玩遊戲的認證宅女,每天最幸福的事就是能夠睡到自然醒。做為一個半路出家插畫師,喜歡各種畫風並樂於嘗試,目前古風作品比較多。如果你喜歡我的畫,我會感到很榮幸,你也可以通過上述社交網站找到我的更多作品( =?ω?= )。
TOP
章節試閱
春禧殿裡光線幽濛,冷宮不比正主子們待遇,大暑天不得冰塊,悶燥使人呼吸難受。楚鄒叫小榛子把官帽兒八仙椅搬到廊簷下,看對面殿頂上幾隻角獸遙遙,瞇著眼睛,手上刻刀不停。
小劉子背著楚恪在台階前放下,一襲垮腰小袍子壓得皺巴巴的。楚鄒看也不看他,輕叱道:「爹都不領回去的孩子,總來我這兒礙眼做甚?」
楚恪最怕人提爹娘,便囁嚅著小嘴討好他,「我給你帶糖吃來了。」把腰上別的小荷包打開,裡頭是三枚方塊小梨花糖。米白色晶瑩剔透的,還可看見細碎的梨花瓣。楚鄒不屑地看一眼又收回眼神,楚恪只好自己先掏出一塊舔了舔,作一臉...
小劉子背著楚恪在台階前放下,一襲垮腰小袍子壓得皺巴巴的。楚鄒看也不看他,輕叱道:「爹都不領回去的孩子,總來我這兒礙眼做甚?」
楚恪最怕人提爹娘,便囁嚅著小嘴討好他,「我給你帶糖吃來了。」把腰上別的小荷包打開,裡頭是三枚方塊小梨花糖。米白色晶瑩剔透的,還可看見細碎的梨花瓣。楚鄒不屑地看一眼又收回眼神,楚恪只好自己先掏出一塊舔了舔,作一臉...
»看全部
TOP
目錄
第一章 重回宮闈
第二章 舊人今事
第三章 昔日嬌影
第四章 泰慶王爺
第五章 柳暗花明
第六章 情難自禁
第七章 旖旎纏綣
第八章 如履薄冰
第九章 手足之情
第十章 十全十美
第二章 舊人今事
第三章 昔日嬌影
第四章 泰慶王爺
第五章 柳暗花明
第六章 情難自禁
第七章 旖旎纏綣
第八章 如履薄冰
第九章 手足之情
第十章 十全十美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玉胡蘆 繪者: 殼中蠍
- 出版社: 可橙文化工坊 出版日期:2018-06-20 ISBN/ISSN:9789869635103
- 語言:繁體中文 適讀年齡:18歲以上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52頁 開數:25開
- 類別: 中文書> 漫畫/輕小說> 羅曼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