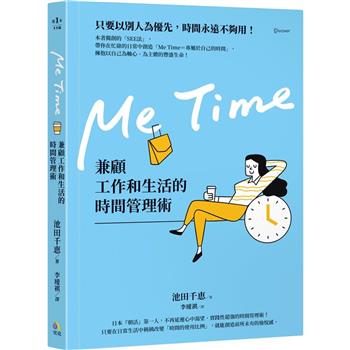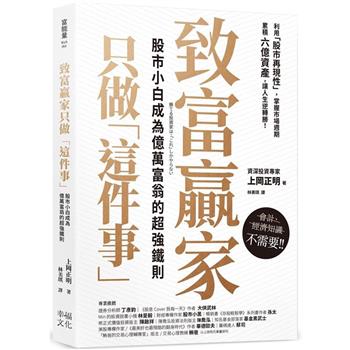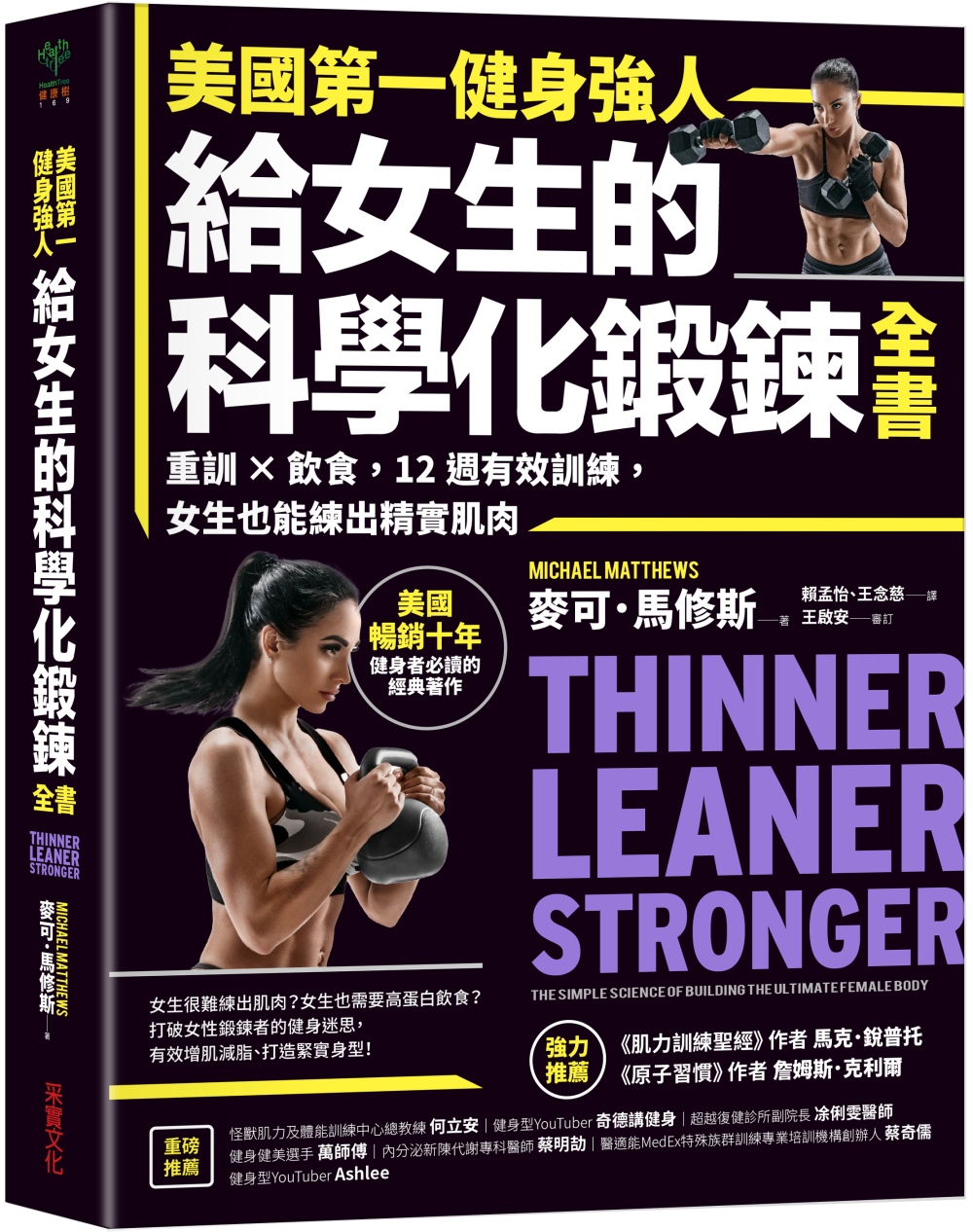琴家繡坊,花廳。
「楚小姐,先喝點兒熱茶,壓壓驚。」一名年約四十餘歲的中年女子含笑給楚瑜遞了一杯香茗,她看著楚瑜臉上的細傷,輕聲細語問道:「您臉上的傷可要處理?」
楚瑜接過茶,禮貌的道:「多謝年大管事,我這點兒擦傷不打緊,您可查出殺手的來歷了?」
這中年女子正是雲州琴家繡坊的管事娘子,人稱年大管事,是金姑姑手下的得力幹將,也是曜司中人。
年大管事看了眼坐在一邊的金曜,見他只垂眸喝茶並無反對的樣子,便點頭道:「查出來了,這些人是骷髏堂的殺手,江湖上專門做殺人買賣,但是抓住的這些人都是下層殺手,他們並不曉得為何要對姑娘動手。」
年大管事的話讓楚瑜眼底閃過若有所思:「買兇殺人?」
「我知道楚姑娘這些日子都在風煙山上住著,您在山上可得罪了什麼人?」年大管事品了一口茶,微笑道:「您且說一說,敢在咱們曜司頭上動土的,從未有人能全身而退。」
楚瑜想了想,總覺得自己得罪的人無非就是琴學裡頭的那幾個人,再不然,她也就只能想到……目前結仇的宮少宸?
聽了楚瑜說的情況,年大管事沉吟片刻,便道:「楚姑娘且寬心住下,繡坊裡總是安全無虞的,您有什麼需要只管著人與我說就是了。」
這小姑娘能得七曜星君裡的金曜星君與水曜星君親自護送,必定是要緊人物,出不得差錯。
楚瑜也知道殺手這事一時間查不出個所以然,便含笑道:「年大管事,我想請您安排我現在就去繡坊看看,不知道方便與否?」
年大管事一愣:「現在嗎?自然是可以的。」
年大管事便起身親自領著她往繡坊內而去。
繞過曲折精緻的長廊,楚瑜見著內院裡一溜幾十間極大的房間,每間房裡都整整齊齊的擱置著大大小小的繡棚,大則十數張,小則數十張。繡娘、繡工正認真的持針繡著手上的活計。
還有各種小工、小婢負責打下手,包括幫著繡娘、繡工們劈線、選線、配色、剪線頭、上棚、裱繡……等等雜活。
楚瑜一一看過,又細細的向年大管事請教了她不了解之處和各種工序。她甚至掏出本子,將許多細節之處和各種工序記錄下來。
「每個繡娘、繡工配之一、二個小工共同勞作……繡棚高幾尺幾寸,寬幾尺幾寸,剪刀大小約幾寸;每人每針繡時,胳膊抬起幾寸……」
金曜見她那仔細認真的模樣,桃花眼底閃過一絲異樣,雖然心中不屑,但還是耐心的等著。他和其餘人一樣好奇,這個不學無術的丫頭又要折騰什麼?
記錄這些,就能贏宮家?
一轉眼便到了傍晚。
一日舟車勞頓,又被人襲擊,再馬不停蹄的進繡坊轉了一圈下來,楚瑜隨意扒拉了幾口飯,匆匆沐浴一番,直接爬上床倒頭就睡。
疲倦之極,按理說該是一夜無夢,好眠到天亮,她卻是怪夢連連。
到了最後,她夢見自己變成一個毛茸茸的線球,被一隻皮毛漂亮的琉璃眼貓兒又是叼著玩,又是拿爪子戳啊戳、拍啊拍……戳得她滾來滾去,渾身發軟,頭暈腦脹,呼吸不順,甚至胸口……發疼。
胸口發疼?她勉力的睜開眼,天色未明,卻見一張陡然放大的俊美臉孔正居高臨下的睨著她。
「白白,你怎麼來了?」楚瑜揉著眼,迷迷糊糊的嘀咕,剛想起身,卻發現自己動彈不得——美人正毫不客氣的騎在她身上。
難怪她覺得呼吸困難,這麼個大仙兒一屁股坐她腰上,她能呼吸順暢才怪!
「醒了。」琴笙輕哼一聲,惜字如金,目光卻沒看她,定格在她頸下三寸處,一臉冰霜,卻難掩一雙沉月眸裡的那一點兒興味盎然的幽光。
她心中忽然生出熟悉的不妙感,立刻順著琴笙的目光向下一看,瞬間嬌軀一震,瞪大眼,漲紅了臉,咬牙切齒的怒道:「你在幹什麼呢!」
楚瑜胸口的衣襟不知何時完全大敞,騎在她身上的琴笙一臉專注的盯著她胸口,一隻手指勾著她的肚兜帶子,正慢條斯理的解著上邊的結。
「賞玩。」琴笙漫不經心的回了她一句,指尖順勢又在她胸口戳了兩下。
肚兜下的小桃被他戳得晃了晃,引得他眼底幽光一閃,竟似透出覺得新鮮有趣的笑意。
「此物竟會滾動,有意思。」
楚瑜剛睡醒,又讓坐在自己身上的琴笙弄得還有點回不過神來,下意識的點點頭:「嗯,當然會動,假的才不會動呢。」
「哦?此物還有假的?」琴笙來了興趣,挑眉問道。
他似有些不耐煩那肚兜上的繩結半天沒有解開,乾脆直接挑了指尖,就要扯斷繫帶。
「當然有假……哎呀,你給我把爪子拿開!」楚瑜脖子上的繫帶被他這麼一扯,磨得肉疼,方才一個激靈清醒過來,彈起身子,下意識一巴掌拍開琴笙的手,另一隻手死死抓住已經被扯斷帶子的肚兜,朝著琴笙怒目而視。
清脆的巴掌聲和手上傳來的微痛感讓琴笙眼底的那點兒笑意瞬間散了去,他瞇起眸子,反手挑起她的下巴,冷冷的道:「魚,妳敢打我?」
楚瑜被吵醒後有些起床氣,加上又被平白「輕薄」加「驚嚇」了一回,惡向膽邊生,怒笑:「呵呵,你信不信再不從我身上滾下去,我還敢咬得你這隻臭貓兒喵喵叫!」
說著,她朝他擱在自己嘴邊的手指狠狠咬去。
琴笙哪怕失憶了都記得戴手套出門,最是寶貝自己一雙漂亮的玉骨手,她就不信他不滾下去。
卻不想,她啃上他玉一般的指尖,他卻只是微微顰眉,沒有鬆開手,只冷冷的睨著她。
被他這麼一看,楚瑜莫名其妙的有點兒心虛,竟狠不下心咬傷嘴裡那漂亮細緻的手指,只虛咬著他的手指,大眼睛不服輸的瞪著他。
兩人就這麼大眼瞪小眼,誰也不動。
瞪著瞪著,她就發現琴笙的目光有點兒不對,他一向清冷如雪的眸光竟有點兒飄忽,這個角度看上去,還能看見他漂亮的喉結滾了滾。
而她嘴裡咬著的手指,竟摩挲了下她的小舌頭……
楚瑜一僵,忽覺得坐在自己身上的那尊大仙兒,似乎比自己還要僵硬。
楚瑜心中一動,瞇起大眼,似笑非笑的睨著他。
半明半暗的空間裡,氣氛變得有些古怪起來。
「哼。」琴笙冷嗤一聲,瞬間抽回自己的手,旋身一個折腰,就從她身上俐落優雅的落下地,負手背對著她。
楚瑜慢吞吞的爬起來,一邊整理自己的衣衫,一邊道:「白白,以後你再不經過我同意,隨意賞玩我身上任何地方,我會不客氣的把你扒光了賞玩回去。」
琴笙身形一頓,冷笑一聲:「妳有這個能耐嗎,魚?」
楚瑜整理好衣衫,爬下床,特意繞到他面前,微笑:「你可以試試,也許我不一定有這個能耐,但是我不理你的能耐總是有的。」
「妳在威脅我?」琴笙冷冷的瞇起琥珀眸,不知為何,天色越是昏暗,他的眸子顏色便顯得越淺,此刻已經變成淡金色,看起來像會在暗處發出幽幽冷光,看得讓人毛骨悚然。
楚瑜卻不閃不避,定定的抱胸看著他,也不說話。
兩人就這麼僵持著。
他的眸光越冷,楚瑜越是氣定神閒。
琴笙忽然垂下眸,轉身拂袖而去,冷冷的留下一聲:「哼,吝嗇!」
「砰!」門被甩上,發出一聲巨響,虛靠在門框上,搖搖欲墜。
房間裡,楚瑜慢慢的吐出一口氣。那隻驕傲又嬌氣的大貓兒又惱了,但她卻知道他妥協了。
她隨後往自己隨身戴著的小錦囊裡摸了摸,摸出一隻精緻的小魚來。
那細長的梅花色小魚躺在她的手心裡,細細的鱗片微張,魚身光潔粉嫩,上面還有一層細膩的水光,她的手微微一動,小魚便似在她掌心裡活潑的跳躍著,抖落一身透明的水珠。
只有細細去看,才能看見那並非一條真魚,而是一隻繡工精細的小魚,也不知道用了什麼手法,那魚並非躺在繡面上,而是一條栩栩如生、立體非常,似躺於她掌心的活物。
這是立體繡的小魚,手法不知比雙面全異繡高明多少。
楚瑜握住那條精緻的小魚,唇角慢慢揚起一點兒得意的笑來。
自她從火曜那裡拿到這條小魚之後,便知道那隻口是心非的傲嬌大寶貝已經接納了她,至少已經將她劃入了他的勢力範圍或者所有物裡。
像貓兒那樣防備心極強的生物,一旦將某種東西或者人劃歸為自己的所有物後,占有欲會暴增,也絕不會輕易捨棄所有物。她沒有知會他一聲,就逕自下山來,也是想看看那隻貓的反應。
他果然追來了。
正因為如此,她今兒才敢和他叫板,試探他的底線在哪裡。
而之前差點被他扒了扔水裡的事,加上今日的突發事件提醒了她,小貓兒好奇、不懂事,她得慢慢的調教和立規矩。否則,這隻貓遲早會肆無忌憚的將她當玩物搓圓搓扁。
那可不是她想要的。
她想要的……
楚瑜看著手裡栩栩如生的精美小魚,原本亮得有些犀利的眼神柔和了不少。
她想要的是夜幕低垂時,有少年乖乖枕在她的膝頭,溫柔喚她一聲:「小姑姑,笙兒想妳了。」
不管是出於為自己在曜司裡的安全處境考量,還是出於心底捨不得的那一份牽掛與溫柔。
楚瑜悵然若失的輕嘆一聲,眼神有些迷離,唇角浮現出一點兒自嘲的笑意來。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執念,那個不管不顧捨命護她,總是要枕在她身上才能一夜安眠無夢的少年,不知何時已經化作了她心底的一抹執念。
「砰!」又一聲巨響,門瞬間落了下來。
楚瑜被嚇得所有的小情緒全飛了,轉頭一看,就見水曜正一臉受驚的看著倒地碎裂的大門,又看向她:「夭壽哦,妳這條鹹魚半夜夢遊拆門嗎?」
楚瑜摸了摸脖子,一臉無辜:「哦……」
那隻漂亮的貓兒,還真是一如既往的暴力,一爪子就拍散了一扇門。
若是這一爪子拍她身上……楚瑜沉默了一下,忽然覺得自己的馴貓大計不會進展得太順利。
待楚瑜洗漱完畢,年大管事便親自過來請她用早膳。
早膳極為豐富,紅木鑲螺鈿花的方桌上,一碟四喜小卷、一碟椰奶四方小糕、一碟牛乳糯米丸、一碟燕窩酥皮卷,一碟蒸餃並四碟小醬菜、幾碗碧梗米粥擺得桌上滿滿當當,散發著誘人的香氣。
楚瑜摸摸肚子,眼神卻略過金曜、水曜、年大管事,飄向門口,「這麼豐盛,只有咱們吃嗎?」
年大管事看著她,笑了笑:「楚小姐如是想問您那兩位西域保鏢,她們一大早就出門了。」
楚瑜本是想問琴笙的事,此時卻聽霍家姐妹不在,不由得一愣:「出門?」
「正是,她們說她們腹中飢餓,要去打點兒野食。」年大管事的笑容裡有著疑惑:「是咱們繡坊裡提供的餐食不好?」
她話音剛落,水曜就擱下手裡的小鏡,豔麗的面容上閃過一絲獰色:「哼,那瘋女人就是狗改不了吃屎!」
水曜突然罵人,不但招來金曜和楚瑜詭異的目光,也讓年大管事嚇了一跳。
「這是……」年大管事有些茫然,她怎麼覺得氣氛有點兒古怪,卻又說不上來哪裡古怪。
楚瑜擺擺手:「無事,無事,我其實是想問問年大管事,今兒看見我的姪兒了沒有?」
金曜端著碧梗米粥優雅的喝了一口,才冷冰冰的哼了一聲:「妳還以為那位會像以前一樣被妳蠱惑,天天跟著妳嗎?」
楚瑜懶得一大清早就和人吵架,只笑咪咪的看著一臉疑惑的年大管事:「是這樣的,我那姪兒知道我下山,便吵著鬧著與金姑姑說了他要過來,我以為他已經到了。」
看樣子,金曜等人已經知道琴笙下山的消息,年大管事卻不知道,這說明琴笙不想暴露身分。
年大管事一愣:「您姪兒已經到繡坊了嗎?在下並沒有得到消息。」
楚瑜聞言,大眼珠一轉,做出有些不好意思的模樣:「沒錯,那孩子早年發燒,燒壞了腦子,是跟著我一起長大的,若是大管事見著了,還要請您多關照。」
年大管事笑咪咪的點頭:「那是自然的。」
金曜又冷哼一聲,繼續吃東西,卻沒有說話。楚瑜也不理會他,逕自坐下用早膳。
年大管事抬眼看了下楚瑜,遲疑片刻,問道:「不知道楚小姐用完早膳之後要做什麼?」
楚瑜用帕子擦了擦嘴,笑咪咪的道:「還是要勞煩年大管事再帶我去繡坊裡轉一轉,我這三日都需要在繡坊打擾諸位。」
年大管事也沒有多想,只頷首笑道:「這自然沒有問題。」
她實在很好奇這個小姑娘進繡坊要做什麼。金姑姑臨時送了一封信來,她才知道昨日匆匆而來的小姑娘就是琴三爺的「小姨」,代表琴家迎戰湘南宮家之人。
一個什麼都不會的小姑娘,打算靠著這些時日待在繡坊裡練成刺繡高手,迎戰宮家少主?
◎
接下來整整三日,楚瑜都待在繡坊裡。
但是她卻沒有像年大管事和金曜等人想的一樣去研習繡技,而是繼續拿著尺子,把沒有量完的各個尺寸的繡棚全量了一遍,甚至去量繡房大小、繡凳高矮和繡花針長短,連繡娘和繡師們的身高、臂長都量了一遍。
然後她便蹲小牆角去勾勾畫畫一堆誰都看不懂的圖和符號。
剩下的時日,楚瑜則是待在倉庫裡看絲線如何儲存和領用,在繡坊裡來來回回的轉悠,也不知道在搗鼓什麼東西。
搗鼓完了,她又從早到晚的蹲在一個繡娘身邊,不知道記錄些什麼。
記錄完這個繡娘後,又跟在一個繡師身邊,盯著人家幹活寫寫畫畫。
最後,她甚至跑去跟在一個小工身後,盯著人家上了幾次茅房。
她這一番折騰下來,直將整個繡坊弄得雞飛狗跳。
琴家繡坊的繡娘和繡師們雖然不如琴學裡的大師地位尊崇,但能進繡坊的也都是繡中高手,自然有些脾氣。何況刺繡與作畫一般,講究的就是寧神靜心,哪裡能受得住這般叨擾?
一來二去的,眾人都對楚瑜有了怨言,卻又礙著對方的身分不敢明言,只是私下裡便不肯再如之前那般配合楚瑜了。
雖然年大管事已經再三安撫眾人,但她心裡也有些看輕了只會搗亂的楚瑜。
至於金曜和水曜,早就對楚瑜這般瞎折騰失去興趣,反正他們只要保證楚瑜不會死了或者跑了就成,便自顧自幹自己的事去了。
楚瑜也不是沒有察覺繡坊裡的氣氛不對,但她已經將要看的東西、要記錄的東西都記錄得差不多了,自然無所謂。
第四日,她便不再去繡坊,而是把自己關在房間裡,也不知道寫畫些什麼東西,搗鼓了一個通宵,天明才睡去。
搗亂之人不在,繡坊裡的眾人都齊齊鬆了一口氣。
到了第五日中午,楚瑜忽然從床上坐起來,揉了揉眼,想起一件事,那隻炸毛的貓去哪了?
炸毛炸了四五天,毛也該順了吧?
她去問金曜,對方冷笑一聲,一副「老子為什麼要告訴妳」的樣子,轉身就施施然的飄走。
水曜原本也想學金曜的模樣,但是不知是不是想到了楚瑜養的女狼兇猛,還是與她說了:「主上一直在妳房間裡,妳難不成沒見著嗎?」
楚瑜一呆,又一拍腦袋:「哎,好像是有這麼回事。」
時間太緊,她一忙起來就人事不理了。如今回憶起來,好像每天都有一抹白影悄無聲息的掛在房梁之上。只有她洗澡的時候,那抹白影……似乎才會消失。
是因為被她警告過,所以他雖然不爽,卻還是在她洗澡的時候乾脆離開,也沒有打擾她幹活?
這種行為模式,除了那隻愛炸毛又驕傲的貓兒,還會有誰?
但是,她忽略了他那麼多天,還跑出來到處問人他去哪裡了……
不好!貓是一種報復心很強的生物!
楚瑜頭皮一炸,心生不妙之感,瞬間拔腿就往自己的房間跑。
果不其然,她才走到房間前,就看見房門搖搖晃晃。
楚瑜沉默了一下,小心的推門:「白白,你在房間裡嗎?」
她手指才碰到門,那大門就「轟隆」一聲瞬間倒地,碎成數片……
楚瑜呆滯片刻,趕緊往房裡奔,果不其然,整個房間亂七八糟的,她的東西幾乎都被扔出後窗,枕頭上、被子上幾個漂亮的腳印鮮明異常。
「我的稿子!」楚瑜大驚失色的往桌前跑,果然看見自己的稿子……全被扔進了水缸裡!
楚瑜眼前一花,顫抖著從水缸裡撈出紙張,欲哭無淚。這就是——自作孽,不可活!
楚瑜又惱又無奈的抬頭四顧,卻發現房間裡空空如也。
她一咬牙,也顧不上別的,先趕緊抱著自己演算描畫的稿子直奔院子,小心翼翼的將稿子晾曬在院裡,同時對著半空吼了一嗓子:「二娘、三娘,在不在?在就給我找個爐子來!」
說實話,她還真不敢確定霍家姐妹是不是又像前幾日那樣,去小倌館裡打野食了。
當她看見霍家姐妹捧了兩個爐子,速度極快的跑出來的時候,還是鬆了一口氣。
她立刻生火,小心的烘烤被水浸溼的紙張。
好在她多是用炭筆勾稿,只有繪圖時會用到墨水,讓霍家姐妹一起幫著自己烘烤了一張張的稿子,總算救回來了大部分,楚瑜這才放下心。
「妳這是遭劫了嗎?」霍二娘將手裡的稿子遞給楚瑜,撓了撓頭,有些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
她們姐妹明明就住在小姐旁邊的房間裡,怎麼會小姐遭劫了,她們都不知道?
楚瑜小心翼翼的把稿子收好,嘆了一聲:「算是吧,屋子裡的貓被我弄炸毛了,遭他報復了。」
琴笙不想要別人知道他的存在,自然不會有人知道。
「妳屋子裡啥時養了那麼個小東西?」霍三娘皺了皺鼻子:「貓那種小東西最煩了,換季就掉毛,還嬌氣又矯情,只能牠不理妳,不能妳不理牠,一不如意就炸毛,快扔了吧!」
霍三娘話音剛落,忽然整個人臉朝下的向火爐子裡栽去!
楚瑜一驚,也顧不上會燒著自己的手,趕緊伸手去扶。
說來也怪,楚瑜一伸手,霍三娘原本往火栽倒的身子頓時以一個詭異的姿態穩在半空中。
她自己也算反應快,立時穩住身子,只險險的被火燎了頭髮,燙得她趕緊伸手拍。
楚瑜也跟著手忙腳亂的幫她滅火:「小心!」
「燙死了!燙死了!」霍三娘一陣尖叫。
霍二娘見狀,速度極快的抬了房間裡的水缸出來,把一缸子冰水潑過去。
「嘩啦!」霍三娘冷得一個激靈,瞬間從烤雞成了一隻落湯雞,涼風一吹,大冷天裡凍得瑟瑟發抖,一個大噴嚏打出了鼻涕泡:「哈啾!奶……奶……個……熊……哈啾……臉……我的臉!」
霍二娘掏出把小手鏡扔給她,嘲笑道:「妳瞅妳那慫樣,蹲著好好的,也能把臉送火爐子裡去。真毀了臉,以後妳要打野食,豈不是只能用強的了?」
「哎呀,真是見鬼了!」霍三娘接過鏡子細細的看自己的臉,擔心受怕了好一會兒。
雖然免了大面積的燙傷毀容,但頭髮燎了火,臉上、脖子上免不得被燙了幾處紅印,一戳就疼得她齜牙咧嘴:「疼!」
待確定沒有什麼大的傷處,她這才鬆了一口氣,心有餘悸的嘀咕:「還好是皮肉傷,也不知道怎麼了,剛才腳下忽然發軟,撐不住身子往火爐子裡栽,怪哉!」
楚瑜揉了揉被火星濺到、雖有些發疼卻並無大礙的手背,一雙大眼四處瞟,沒有看見那一道熟悉的修白身影。
不知道為何,她總覺得這事十有八九就是那隻報復心極強的「貓」幹的。
楚瑜看看霍三娘的臉,嘆了一聲:「妳先去找大夫看看吧,雖然只是一點兒紅印子,但到底是頭臉的地方,還是謹慎些好。」
霍三娘一邊看著自己的臉,一邊點頭:「也好。」
楚瑜想了想又道:「我想上街轉轉,看看有沒有什麼適合貓兒玩的,到底是我先惹了他。」
按理說,馴獸都是打一下鞭子,給一顆糖。她倒好,上次冒險小小「抽」了那隻傲嬌貓一鞭子,他難得沒翻臉,還乖了好幾日。
她卻沒記得順毛,直接忽視他的存在,這不等於又抽了他一鞭子?那隻貓不炸毛才怪。
這時候,琴貓貓肯定不知隱在哪裡,但此時定然是在氣頭上,否則不會出手就要毀了三娘的臉。她琢磨著最好還是先把他引出去,消磨點兒火氣,說點兒軟話,順順他的毛。
別讓那隻貓發作起來,把她身邊的人都折騰得半死不活。
霍三娘臉上正疼著,聽著楚瑜要出門,便有些不耐的嘀咕:「別去了,一隻臭脾氣的貓兒,理牠做甚,扔了……」
話音未落,她忽然一個踉蹌,這一次是直接腿軟向爐子裡跪下去。
好在楚瑜一直防備著,趕緊伸手一把抓住她的衣領,大力向後一扯,才免了她跪火爐的命運。
「小心!」
霍三娘頓時出了一身冷汗,她四下看了看,並沒有發現任何異常,也沒有探查到有人潛伏在周圍暗算她,只嘀咕:「哎呀,今兒莫不是撞邪了?不行不行,去醫館前得摸個小哥去去晦氣。」
楚瑜無言捂臉:「妳……真是夠了。」
這色中魔女實在讓她有種撓牆的衝動。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繡色可餐(卷二)名響江南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50 |
二手中文書 |
$ 246 |
中文書 |
$ 252 |
古代小說 |
$ 252 |
華文羅曼史 |
$ 252 |
文學作品 |
$ 252 |
言情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繡色可餐(卷二)名響江南
蟬聯瀟湘書院金榜第一,[青青的悠然]繼《宦妃》後最眾所期待的作品!
最強男女主角的相愛相殺,你攻我防之間碰出最燦爛的火花!
一張有著驚天之秘的藏寶圖,讓她背負了天下的陰謀,她要如何在一群殺人如麻的追逐者中,保住自己得來不易的珍貴小命?
⊙收錄網路版刪減片段和實體版特別番外,絕對精彩絕倫,鐵粉一定要補完!
與宮家的大比來到了最後一局,這回不靠精美繡圖,也不依賴琴家的龐大勢力,楚瑜會用什麼奇技淫巧來贏得宮少宸那號人物?
大比結束,楚瑜的名聲亦響徹江南,更被推舉為織繡商會的會長?幸好逐漸在琴家混得如魚得水的楚瑜有著金姑姑與曜司們的支持,做起事來雖不算得心應手,也還順遂過得去。
可當一切漸上軌道之際,竟出現了自稱琴笙未婚妻的南風少主要來商談聯姻之事!此女來勢洶洶,不懷好意,楚瑜又會遇上什麼難題?
依舊不復記憶的琴笙非但幫不了忙,更是變本加厲的纏著她鬧出事端,讓楚瑜又愛又恨又苦惱──孩子大了佔有慾強了,當小姑姑的也是有點看不懂琴笙那偶爾閃著不明意味的目光是幾個意思了……
作者簡介:
青青的悠然
暢銷新銳作家。瀟湘書院金榜寫手,人氣常年居高不下,代表作《宦妃》、《九天傾凰》系列頗受讀者追捧,曾多次上實體銷售熱榜,前作《宦妃》多次斷銷並加印。
▌繪者
沉沉狐眠
95後典型雙魚座患者,喜歡紙片人,喜歡摸魚,想擁有一隻自己的小狐狸,想做一個神秘的靈魂畫師,做自己喜歡的事,畫自己喜歡的圖。
新浪微博:https://weibo.com/p/1005052816647813
TOP
章節試閱
琴家繡坊,花廳。
「楚小姐,先喝點兒熱茶,壓壓驚。」一名年約四十餘歲的中年女子含笑給楚瑜遞了一杯香茗,她看著楚瑜臉上的細傷,輕聲細語問道:「您臉上的傷可要處理?」
楚瑜接過茶,禮貌的道:「多謝年大管事,我這點兒擦傷不打緊,您可查出殺手的來歷了?」
這中年女子正是雲州琴家繡坊的管事娘子,人稱年大管事,是金姑姑手下的得力幹將,也是曜司中人。
年大管事看了眼坐在一邊的金曜,見他只垂眸喝茶並無反對的樣子,便點頭道:「查出來了,這些人是骷髏堂的殺手,江湖上專門做殺人買賣,但是抓住的這些人都是下層殺手,他們...
「楚小姐,先喝點兒熱茶,壓壓驚。」一名年約四十餘歲的中年女子含笑給楚瑜遞了一杯香茗,她看著楚瑜臉上的細傷,輕聲細語問道:「您臉上的傷可要處理?」
楚瑜接過茶,禮貌的道:「多謝年大管事,我這點兒擦傷不打緊,您可查出殺手的來歷了?」
這中年女子正是雲州琴家繡坊的管事娘子,人稱年大管事,是金姑姑手下的得力幹將,也是曜司中人。
年大管事看了眼坐在一邊的金曜,見他只垂眸喝茶並無反對的樣子,便點頭道:「查出來了,這些人是骷髏堂的殺手,江湖上專門做殺人買賣,但是抓住的這些人都是下層殺手,他們...
»看全部
TOP
目錄
第一章 天工繡坊
第二章 出奇制勝
第三章 大開眼界
第四章 織繡商會
第五章 索取獎勵
第六章 南風織造
第七章 禁養野貓
第八章 遭人算計
第九章 明月女史
第十章 攜貓出走
第二章 出奇制勝
第三章 大開眼界
第四章 織繡商會
第五章 索取獎勵
第六章 南風織造
第七章 禁養野貓
第八章 遭人算計
第九章 明月女史
第十章 攜貓出走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青青的悠然 繪者: 沉沉狐眠
- 出版社: 可橙文化工坊 出版日期:2018-10-03 ISBN/ISSN:9789869635141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84頁 開數:25
- 商品尺寸:長:210mm \ 寬:148mm
- 類別: 中文書> 漫畫/輕小說> 羅曼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