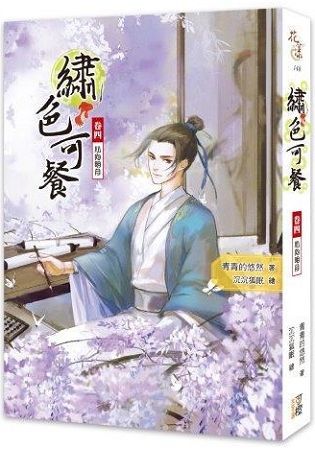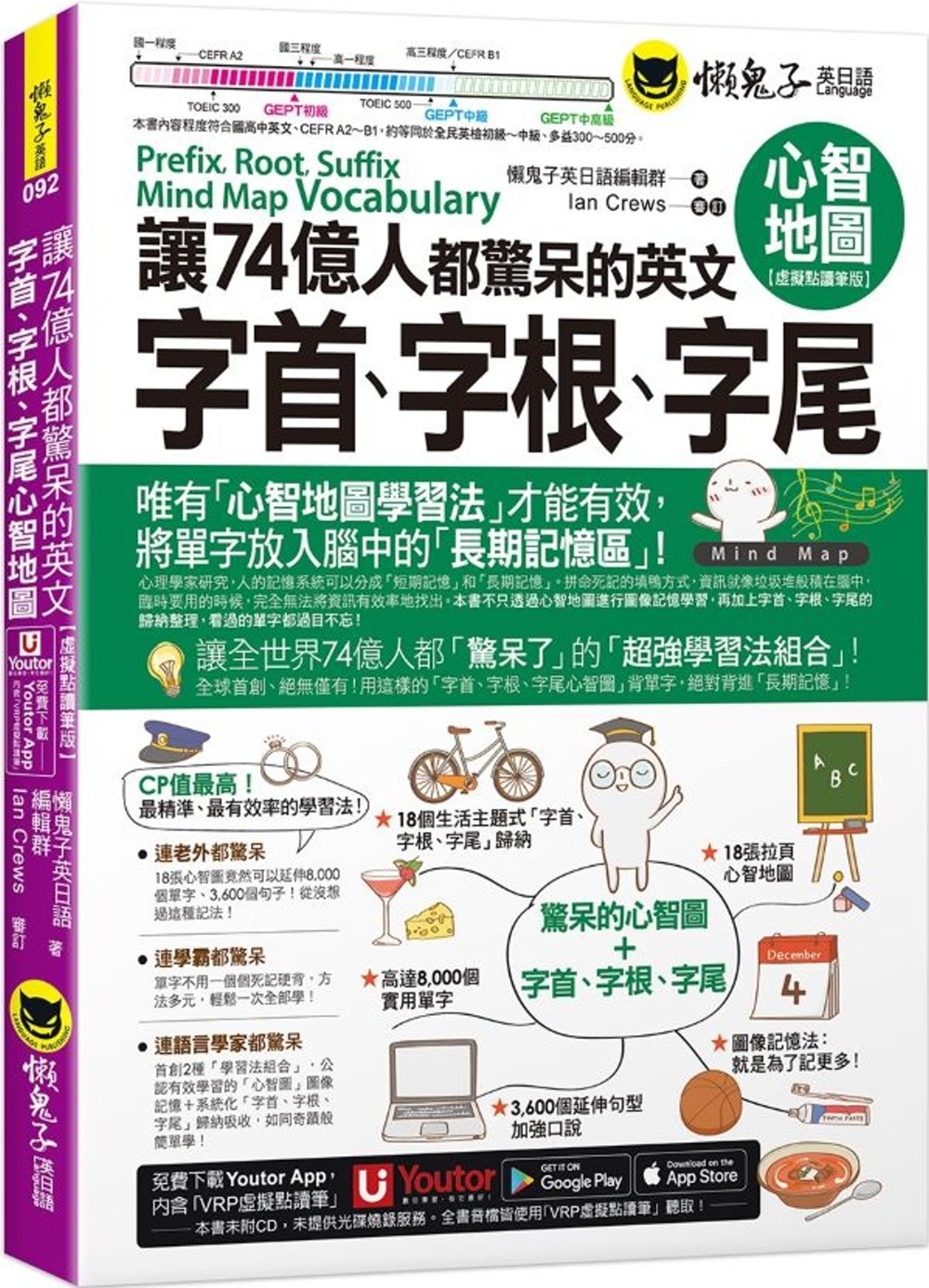紅袖早早的領著人待在耳房,看著日頭稍傾斜了一些,已經是平日琴笙起身的時辰,這才領著婢女們去敲門。
房間裡有溫泉,不需要她們準備熱水,但是昨晚主上和小姐一直都沒有出來,金曜也擋了她們,不讓她們進去送吃食。
不知道為什麼,紅袖就是直覺的感覺裡面應該是出事了,但是出了什麼事,她也不清楚,只是有些不安。
金姑姑聽了也覺得有些異樣,但沒有多言,只讓她候著守夜。
就這麼一夜過去了,她一大早就數著時辰準備進去伺候。
可她才準備敲門,手指還沒有碰到門,門便「吱呀」一聲打開來了。
琴笙照舊一身繡飛雲紋的白衣站在門前,領口的琵琶袖盤釦扣到最上面的一顆,烏髮一絲不苟的梳在腦後,以玉扣扣住,無雙容顏清冷淡然,氣息更是不染纖塵。
彷彿昨晚他根本沒有洞房花燭,而是打坐修仙了整夜。
但是房間裡,那似殘紅凌亂碾碎,開到荼蘼的靡靡氣息……
紅袖一呆,看著面前的琴笙,卻在對上彷彿永遠籠著幽深冷霧、睨望凡塵的精緻妙目時,忽然打了一個寒顫。
原先那種因為主上性情改變,而褪去了一些的敬畏忽地爬了上來,讓她迅速的低下頭,聲音有些發顫的道:「主上,屬下來伺候……伺候小姐……不,夫人。」
她是習慣了,改不了口。
主上馭下極嚴,曜司眾人受他細緻縝密、靜水深流的行事風格影響,一貫也是嚴苛的。
雖然自主上……腦子不好以後,就已經沒有再如從前那般對屬下要求嚴謹,他甚至根本懶得理會他們。但不知為什麼在這一刻,紅袖卻覺得她必須恢復到以前的方式。
琴笙看了她一眼,只聲音淡柔的道:「中午再過來,她凌晨才睡,至於稱呼,她大概不會喜歡夫人這個稱呼,改不改並不重要。」
紅袖有些不太明白。為什麼小魚會不喜歡?她一直盼著這場婚禮不是嗎?
但是她的本能已經讓她伏下身子,恭敬的道:「是。主上現在要去何處?」
琴笙道:「去東樓書房,讓七曜與在琴家繡坊的金字輩都來見我。」
紅袖看著琴笙直挺的背影,忽然心頭一跳,睜大了眸子:「主……主……」
她立刻又再次抱拳,強行壓抑著激動:「是!」
紅袖交代了一下跟著自己一同來的婢女後,立刻運功飛身離開。
一刻鐘後,東樓書房。
窗外山巒起伏如墨氳,藍天碧水,雲悠悠,有風徐來。
夏日的風吹起正負手看著書房牆壁上一幅大漠殘陽圖的修白人影的如墨長髮,但見他如雪氣息壓得窗外烈日的暑氣都散了。
只一眼,金姑姑和老金都忍不住心頭狂跳。他們已經大概聽紅袖和金曜說了。但是如今親眼所見,竟有近鄉情怯之感,他們已經失望過很多次了,怕這一次再失望。
尤其是老金,幾乎有些不抱希望自家主上能恢復了。
還是金姑姑先有些發顫的開了口,試探著道:「主上?」
白衣人慢慢的轉過身來,神色淡然的看著他們,唇角彎起溫柔而涼薄的弧度:「金姑姑,老金,這些日子可是辛苦了,嗯?」
金姑姑和老金忍不住老淚縱橫,齊齊喚道:「三爺!」
他們神祇一般的主上、曜司眾人的信仰終於回來了。
連著七曜等人都齊齊單膝下跪,神色之間是掩藏不住的激動。
一番簡單的交流之後,金姑姑抱著之前堆積的許多奏事冊過來,見琴笙正抬手由著金曜伺候他換上手套,她忽然想起什麼,不動聲色的道:「三爺,小魚她……」
琴笙戴手套的動作一頓,妙目淡淡的看著她。
金姑姑忽然打了個寒顫。
那一瞬間,房裡原本歡喜的氣氛都凍結,所有人的呼吸都窒了窒。
雖然琴笙臉上沒有任何表示不悅的表情,他的唇角甚至是上翹的,但是房間裡的空氣彷彿都稀薄了許多。
琴笙示意金曜繼續替他戴上手套,他單手支著臉頰,平靜的道:「她很好。」
老金見狀,便一邊為琴笙診脈,一邊不動聲色的換了個話題:「主上,您如今可有頭疼,又或者哪裡不適?之前的事情,您記得多少?」
琴笙道:「尚且還好,之前的事……」他頓了頓,唇角彎起意味不明的弧度:「都記得清楚。」
眾人互看一眼,臉色一瞬間都變得有點古怪。主上這是什麼意思?都記得……
他們不約而同的想起自家主上抱著一個少女叫娘,後來堅持叫人家小姑姑,被對方一碟烤梅花魚誘得從房頂上跳下來,坐在她懷裡,然後跟雛鳥認母似的一直只讓她近身……等等。
主上此時,是何等心情呢?
曜司諸人全看不出來。此刻的琴笙,是九天琴神,永遠沒有人看得透他溫潤含笑眸子裡那一片深邃幽暗的海,也沒有人活得不耐煩的探問。
只金曜有些忍不住開口:「您失去記憶前,曾經召集金字輩在乾坤院等候消息,那夜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可是與您召集我們有關?」
他實在不明白,到底是什麼人能將主上傷成那樣。他一直懷疑是楚瑜下的手,卻又沒有證據,更不明白她一介弱女子怎麼能動自家主上一根汗毛?
琴笙單手輕敲著椅子的扶手,妙目幽沉,卻沒有多言:「一點意外罷了,也是本尊大意了。」
他輕勾了下唇角,神情莫測,話鋒一轉:「至於召集你們,一來是追緝多年,我得到了黑海老魔手上的那一幅最關鍵的藏寶圖,需諸位看一看;二來是關於湘南宮家之事,他們與黑海老魔有所牽扯,很可能是他在中原的內應或者合作者。」
琴笙此言一出,立刻讓老金等人臉色微沉。
「黑海老魔背景複雜,黑海幫一貫混跡海上,大吃四方,與西洋海盜、琉島人、東洋倭盜都有密切的牽扯,咱們船隊曾經和這些人都打過交道,若是他們中有人覬覦藏寶圖,怕也是棘手之事,可能牽扯到國政。」金姑姑沉聲道。
老金輕哼一聲:「牽扯國政,與咱們有什麼關係?」
琴笙垂著鴉翅似的睫羽,讓人看不出他在想什麼,只是優雅的輕支著臉,另外一隻手的玉白指尖輕劃過自己面前的一幅羊皮海陸圖,最後定在圖上一處名為琉島的地方:「第四幅藏寶圖在琉島島主的手上。」
金曜的桃花眼裡閃過一絲冷色:「主上,這琉島的島主一向神秘,因這琉島是那處海域上最龐大的島嶼,島主占地為寇,卻自封國主,前兩年朝廷曾派海軍去征討過,但是敗北而歸。」
大元的海軍一貫強悍,但是那次卻敗得極慘,後來因為琉島附近礁石極多,暗流也多,乃是暴風雨頻繁之處,琉島上也沒有朝廷需要的資源,朝廷便索性封了去琉島的海路,打算直接困死他們。
但是身居海島,又怎麼可能會真的被困死?雖然封了海路,但貿易發達的地方,走私難絕禁。只是朝廷懶得理會,便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朝廷那些廢物,哼,豈能和主上一手帶出來的琴家戰船隊相媲美,自然用這種綏靖之策。」老金輕蔑的冷笑。
「當初咱們也不是沒有撞上過琉島人,只是他們遠遠看見琴家的大旗便不來招惹,而是迅速離開,是有些眼力,是以咱們也沒有和他們號稱剽悍的船隊戰過一場。」金姑姑道。
琴笙的指尖在那島上的位置輕敲了敲:「當初藏寶圖分六份,咱們琴家一份,其中五份流落出去,一為廉親王所藏,一為黑海老魔所獲,一為老金藏於蜀中唐門,一為琉島島主所獲,一藏於漠北,如今唐門與黑海老魔的那份都已經到了咱們手上……」
他輕輕的彎起唇角:「做些準備吧,咱們也許要走一趟琉島。」
眾人一怔,竟都有些恍惚的感覺。因為主上受傷,曜司許多計畫都暫停了,如今他們才清晰的感覺到主上是真的回來了。曜司將再次成為曜司!
「是!」眾人都難免有些激動,抱拳行禮。
待眾人散去了以後,金姑姑卻停留在房間門口,並沒有離開的打算,神色也有些猶豫。
「姑姑還有什麼事嗎?」琴笙淡淡的看向金姑姑。
金姑姑沉默了一會兒,還是慢慢的道:「主上,我知道您原此生都沒有打算成婚,但是小魚她……是好姑娘,對受傷時候的您,一直都全心全意,照顧您一直都是極妥帖的。」
疼愛這個詞如今在深沉的主上面前說出來,充滿了怪異的違和感。所以她換了一種說法。
琴笙抬起琥珀眸,看著窗外遠處的山巒,神色幽幽的輕勾了下唇角:「這不是姑姑想說的吧,您想問我的是,我打算怎麼處置她?」
金姑姑呼吸有些微窒,意有所指的道:「小魚很是聰明,也是咱們琴家的恩人,何況對您也是一片真心,您在受傷時一直對小魚一往情……」
但話音未落,便被琴笙似笑非笑的打斷了:「若是我與姑姑說,兩次受傷,都拜她所賜,妳還會為她求嗎?」
金姑姑一愣,似有些沒有反應過來,好一會兒,她才神色極為複雜的苦笑:「小魚雖然心思慧黠,但若不是因為自己的安危受到威脅,是不會輕易與人動手,甚至取人性命。」
琴笙看著金姑姑,忽然輕笑了起來,聲音有些幽涼:「這丫頭確實很有些能耐,不過年餘時間,竟能讓本尊身邊的人一個個都向著她,嗯?」
金姑姑臉色微變,無奈的對著琴笙一福:「主上,您怎會不明白我們這些人的忠誠,我們所有的一切都是為了您考量,又何須試探屬下?」
她是看著他長大的,其他人不明白,她又怎麼能感受不到他此刻心緒並不如表面上看起來這般平靜清冷。
哪怕是驚瀾翻天,暴怒之中,他面上的微笑都不會淡去,清冷出塵似紅塵俗世不過眼,談笑間千百種手段就讓對手灰飛煙滅。如今話裡都帶了刺,分明已經是情緒極不佳。
琴笙沒有說話,只是依舊目光涼薄的看著窗外。
金姑姑靜靜的陪伴在他身邊,架起小爐子,如曾經做過千百遍一般,為他煮起香茶來。
房間裡一時間只能聽見咕嚕嚕的泉水在紫砂壺裡煮沸的聲音。
不一會兒,滿室飄蕩開雀舌茶的清香。
金姑姑將一杯泡好的碧綠雀舌擱在琴笙的桌面上。
那是琴笙失憶前最鍾情的一種昂貴的茶,每年只出產五六斤,極為難得,上貢也不過一斤,剩下的都是留著他用。
即使御書房裡沒有了供應,琴笙的書房裡依然飄散著純清的茶香。
琴笙忽然淡淡的問:「我如今,與兩次受傷之後區別很大?」
茶水的裊裊蒸氣輕輕舞動,有些模糊了琴笙美得驚心動魄的容顏,讓人看不清楚他的表情。
金姑姑輕嘆一聲,卻是很乾脆的道:「是,判若兩人。」
當初的「仙仙」和「白白」看似性子相差極大,但如今和三爺對比起來,才能感覺到那其實真真不過是純澈稚子長成了叛逆少年罷了,都是「笙兒」的不同年齡階段,是一眼能看得見底的單純,畢竟「笙兒」的性子再矜傲,再天生敏慧厲害,也沒有那十幾年陰鬱與沉重的記憶。
他不過是一個依賴楚瑜,又深愛著她的「少年」。
她和老金之所以覺得這般的主上也不錯,宛如拋卻了過去所有黑暗沉重血腥的負累,重獲新生的琴笙,人生可以重新來過。
楚瑜那小丫頭陪著他走過人生最初的純稚淳雅、少年時令人頭疼的叛逆,未來再一路陪著他一起重新走向更輕鬆的路,一路扶持,一路相伴,重新獲得幸福,白頭到老。
她知道那少女一定會緊緊的握住他的手不會放開,主上也算因禍得福,不好嗎……
但如今恢復了記憶的三爺,除了擁有做為「笙兒」時期那些並不複雜的經歷和被楚瑜陪伴的溫暖記憶外,那幾十年累積在他心中黑暗海域裡的記憶,才是塑造了如今深不可測的三爺性情的全部。
那是一個連她這個陪伴著三爺經歷前半生風雨的老人都不能揣摩出心思的存在。
小魚那姑娘給予的那些溫柔與溫暖,可能暖得他心中所有的冰冷水域?又或者是一點溫暖燈火也會被黑暗的海潮吞噬?
金姑姑輕垂著眸子,掩去眼底一點濕意。
不知為什麼,如今越想,她竟不希望琴笙恢復原來的那些記憶了。
琴笙看著金姑姑的模樣,似有些譏誚的閉上眼,淡淡的道:「去將本尊放在樓裡的那些刺青用的東西拿出來,色料……」
他沉吟:「先取來,本尊先調製。」
金姑姑一愣,有些跟不上琴笙的思路:「主上要這些是……」
不知為什麼,她有點不太妙的預感。
琴笙神色悠悠:「姑姑只管去拿就是了。」
金姑姑福了福身子:「是。」
又看著琴笙的表情,有些猶豫,有心想要勸一勸。
一邊背著醫藥包站在門外等著再給琴笙診脈的老金,見金姑姑的模樣,他到底忍不住了,提著醫藥包也不等召喚就進了門:「主上,小魚如今已經是咱們曜司的主母,您……」
琴笙指尖輕敲了敲桌面,緩緩睜開妙目,似有清冷霧氣籠在其間,笑容幽暗莫測:「你們這一個個的,難不成真以為本尊會把自己的小夫人怎麼了?」
老金和金姑姑都不敢再說話,後者沉默著退出去,前者老實的低頭繼續替琴笙診脈開藥幹活。
琴笙看著老金搗騰一番完畢之後,他慢條斯理的起身,看了看天色:「晌午了,也該是和我的小夫人用膳了,免得你們都以為她已經沒了。」
老金腦門上冒出一層細汗,他乾笑:「主上……」
新房裡,一片紅色,喜慶非凡。
楚瑜只靜靜的坐在溫泉池裡,身上披著一件輕薄的紅色紗袍,紅袖在一邊替她洗頭,看著池子裡安靜的少女,還有她露出的胸前、肩膀那青青紅紅的斑點痕跡,甚至連手臂、大腿、纖細的手腕、腳踝都有被纏繞的紅痕。
紅袖眼裡閃過一絲不忍和不安,她不遲鈍,在進房間的時候,楚瑜雖然安靜的窩在被子裡,她也能看出來有些不對勁。
直到楚瑜披上一件紅色紗袍,同意她伺候自己洗頭的時候,紅袖才覺得事情有點……棘手。
這姑娘從來不喜歡人伺候的,如今她像是一點都不想動彈,安靜得過分。
「小姐,午膳已經擺上了,妳想吃什麼?」她試圖找點話題。
楚瑜垂著眸子,平靜的道:「隨便。」
她沒有胃口。現在的她只想吃人肉。最好是琴三爺的。
紅袖也沒有多言,只替她將長髮擦乾,塗抹上薔薇香露,順便岔開話題:「這香氣真的很適合現在的小姐呢。」
這五月薔薇香露很好聞,用在楚瑜身上,會與她身上的味道混合成一種很清麗馥郁的香氣,很襯楚瑜現在那種介於少女和女子間清純慧黠又嫵麗的感覺。
只是楚瑜聞著那香味,心情卻有些不大好,冷淡的道:「下次還是換別的吧。」
昨晚那魔頭越是聞著她身上這味道,越是一下下的用盡手段,幾乎折騰得她要哭出來。
「為何要換?這薔薇是波斯進貢之物,宮裡也不過一年十瓶,小魚不喜歡?」一道溫柔幽淡的聲音忽然在溫泉室的門口響起。
聽著那聲音,幾乎讓楚瑜有一種錯覺,彷彿他們真是一對恩愛夫妻,他真的柔情如水。
楚瑜有一瞬間的恍惚,又有些自嘲的彎起唇角。
那個男人,本來就喜歡戴這種溫情脈脈的面具,掩蓋他冰冷殘酷的內心。
她冷冷的看著紅袖起身,有些尷尬的向門口的琴笙行禮。
「下去。」琴笙抬了下手。
紅袖面上露出一瞬間的擔憂和遲疑:「但是,小姐……」
話音最後終結在琴笙幽沉冰冷的目光裡,紅袖窒了窒,身子微微一抖,不敢隨便動彈,只恭謹的道:「是,主上。」
她便退出了溫泉室。
琴笙順手取過紅袖擱在紫檀雕花架上的大布巾,走向楚瑜,垂眸居高臨下的看著她,俊美出塵的容貌上表情溫柔到莫測:「小魚,妳比本尊想像的要有能耐很多,本尊身邊這些人,一個個都操心著,只怕本尊一個不小心將妳弄沒了。」
楚瑜被他那目光看得渾身不自在,她拉緊了身上的紅色紗袍,有些刻薄的輕嗤:「那可見三爺你平日做人有多失敗了,不過是我這般人物都能拉攏你的人,又或者你平日裡行事太過殘忍苛刻,讓你自己的屬下有那樣的疑慮。」
「疑慮?」琴笙眸光幽幽如波,恍若無奈的輕嘆:「我怎麼捨得將我的小夫人弄沒?」
楚瑜拉著衣襟的手,不小心碰到自己柔軟胸口上那些還有些發疼的紫紅痕跡,那上面甚至有一些齒痕,便陰沉著臉道:「你是沒有弄死我,不過也差不多了。」
琴笙挑眉,笑容清淺:「不是還沒有嗎?不過是取了點妳在琴園和風煙山上差點要了本尊性命的利息罷了,要知道,本尊一貫是一個睚眥必報之人。」
他說得那般自然,彷彿在說一件無比理所當然的事情。
楚瑜一呆,這是利息?那本金是什麼?
她一對上他看不清情緒的眼裡那一片深暗的濃霧,就忍不住打了個顫,暗自罵了聲:禽獸!
琴笙慢條斯理的將手裡的大布巾敞開:「上來。」
楚瑜警惕的瞇起大眼:「你出去,我自己來!」
琴笙仙氣飄飄的微笑:「妳上來,或者本尊下去,選。當然本尊下去,很有可能會變成妳說的那種……」
他沉吟了片刻:「嗯,禽獸。」
楚瑜:「……」這魔神會讀心術?
她沉默了一會兒,看在對方如此痛快承認他是禽獸的分上,還是攏了衣衫爬上去,一身濕漉漉的抱著胸口,陰沉的看著他。
禽獸,不,琴笙挑了挑眉:「紗袍濕了,不打算換?」
楚瑜冷哼一聲,轉過身去,利索而乾脆的將身上的袍子脫下一扔。
她穿著紗袍不過是為了不讓紅袖看見她背上的圖,如今既然這魔神在這裡,他也不是沒有看過自己的背後,她倒沒有什麼好矯情的。
楚瑜的乾脆讓琴笙的動作一頓,他的目光落在她凌亂的潮濕烏髮,然後順著她纖細的脖頸,到滑膩白皙的脊背上。
少女的光裸脊背上有一雙很精緻的蝴蝶骨,微微一動,便恍若兩片蝶翼。
蝴蝶骨之間的白皙皮膚上此刻是一大片線條華麗的山海圖,浪潮隨風而起,山巒精緻,花朵搖曳而華美,一看便是大家手筆。雖然沒有色彩,但是卻已經極為漂亮。
因著楚瑜才從溫泉裡上來,皮膚帶著淡淡的粉色,讓那圖呈現出一種近乎香豔的惑人來。
琴笙琥珀眸微深,指尖輕輕的挑開她垂落下來的髮絲,擱在她脊背細膩的肌膚上,慢慢的下滑,似在愛撫,又似在丈量。
那冰涼細膩的觸感讓楚瑜覺得脊背上莫名的酥麻。
靠近脊髓的附近,正是神經集中的敏感之地,她顫了顫,忍不住咬牙道:「你夠了沒有?」
就算他要描圖,能不能換個地方?她身上還一絲不掛呢!
琴笙輕勾了下唇角,抬手拿著布巾將她一包,打橫抱起她向溫泉室外走去。
楚瑜一驚,下意識的伸手去拉他的衣襟,穩住自己的身子。
之前,都是她的貓兒沐浴完畢,慵懶的喚她來抱他出去,若是她手上有事耽擱得久點,他便會不耐煩,有時候會使些小性子,在她抱起他的時候,趁機弄她半身的水。可但凡她抱著他的時候,他總是很安靜,安靜到乖巧,惹得她心中有點癢癢的,想要揉他的頭。
如今換了過來,卻已經沒有了那時的心境。
抱著自己的人,氣息還是熟悉的清冷水香,懷抱還是熟悉的微涼,熟悉到她身體都沒抗拒的靠進去。但這懷抱裡此刻彷彿多了一種危險又成熟的氣息。
楚瑜垂下眸子,神色複雜,而她並沒有看見自己頭頂上那雙熟悉的琥珀眸子也正睨著她,亦是一片複雜而莫測的幽光。甚至,有些迷離。
琴笙抱著她在床邊坐下,楚瑜立刻扯了被子把自己裹起來,冷眼瞪著他。
琴笙只挑了挑眉:「本尊的小夫人打算裹著被子用午膳,本尊自然也無所謂。」
楚瑜冷淡的道:「三爺,我不要求你非禮勿視,但既然你現在不打算殺了我,也不打算立刻描下藏寶圖,只打算用膳,那麼就請你背過身去,我自然會穿好衣衫,畢竟你我現在也沒有什麼關係。」
紅袖給她準備的衣衫就擱在床邊的凳子上,他走開之後,她伸手一撈即可。
楚瑜的話,讓琴笙唇角清淺的笑意漸漸散了不少,他垂下眸子,睨著她,道:「怎麼,昨晚洞房花燭夜一個晚上,妳都沒有想清楚嗎,小魚?」
他意有所指的話讓楚瑜臉色倏然漲紅,她冷笑:「你讓我怎麼想?」
她話鋒一轉,輕嗤:「哦,不,我想清楚了,經過昨夜,我更肯定你和笙兒根本就不同,他捨不得傷我分毫,對藏寶圖一點興趣都沒有,他不稀罕那玩意,自與三爺不一樣的!」
話音未落,只聽得「砰」一聲巨響。
她忽然就住了口,有些僵木的看著面前眨眼間壓低放大的俊美容顏。
他幾乎一瞬間逼到她眼前,抬手越過她臉頰,驀然捶在床後的牆壁上,壓低了臉,與她眼對著眼,鼻尖也幾乎壓迫到她的鼻尖上,她幾乎能聞見他唇間帶著淡涼微醇的潮潤氣息。
琴笙目光幽沉冰涼的睨著她,似譏、似誚,聲音卻依然溫柔如水:「捨不得傷妳分毫?地宮晶洞裡,妳若不主動吻上來、沒有第一時間否認妳對宮少宸有心,妳已經被情緒徹底魔怔的他,嗯,不,是被我穿透了心臟在晶柱上鎖魂了,魂魄和屍身一輩子都被鎖在我身邊。」
楚瑜一怔,不自覺的咬住了唇,幾乎將自己的唇咬出血來。
琴笙將指尖輕按在她的唇上,看似動作輕柔,卻毫不留情的強迫她鬆開嘴。
「怕嗎?」他輕笑,笑容卻很涼、很涼,涼到有些刺骨,聲音卻很慢:「妳所鍾情的人,從來都沒有改變過,是比起失去而寧願毀滅自己所愛之物、所愛之人,也不會容許背棄的殘忍又冷血的存在。所以,妳愛上的、鍾情的,從來都是一個溫情的幻象。」
他輕嘆一聲,指尖輕輕的撫摸過她唇角上的血,淡漠又憐憫的道:「後悔嗎?」
說話間,他抬起指尖,慢條斯理的輕嗅一下,將手指送進自己唇間。
楚瑜腦子裡一片混亂,此時卻忽然大驚,抬手就擒住他手腕,怒道:「你瘋了?有毒!」
唐墨天臨死前說換了她一身天下至毒的血,她原是不信的,直到後來在唐門地宮之外,她心神不寧的割破了自己的手指,滴落在草葉上。那上面有幾隻蟲,一觸到她的血便扭曲著身子,彷彿一剎那被腐蝕一般的死絕了。
她恍惚著匆匆離開,卻不想傍晚就聽說了有兩匹曜司的戰馬忽然無聲無息的七竅流血而死,卻查不出原因。
最後還是她想起那馬兒吃草的地方正是她滴了一滴血的草叢,待她趕過去之後,唐鼎天蹲在馬兒附近,正呵斥把死馬烤來吃的唐門弟子。
他們餓了太久,捨不得浪費馬肉,結果一吃,就立刻有人毒發。
唐鼎天是有見識的,猜測到一些原因,立刻又借了她的血來調製解藥,才解了毒。
「妳在擔心本尊?」琴笙看著她。
楚瑜一僵,她只是……習慣了。習慣了去照顧他,去操心他。卻忘了……
這個男人,再不是那個矜傲又懵懂的少年。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繡色可餐(卷四)心向明月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50 |
二手中文書 |
$ 221 |
言情小說 |
$ 246 |
中文書 |
$ 252 |
古代小說 |
$ 252 |
華文羅曼史 |
$ 252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繡色可餐(卷四)心向明月
大婚之夜,琴三爺回來了。與他鬥智鬥勇好些日子的楚瑜仍然無法脫離他的掌控,什麼心思都被他摸透,似乎就連情感,也漸漸不受控制……
她逐漸在他身上看到過去仙仙白白的面貌,卻不懂到底曾經經歷了什麼的他,才會長成如今冷血殘酷的琴三爺。
可即便是那樣的琴笙,楚瑜也無法克制自己不去愛他、包容他的一切,他身上藏著的無數秘密,她竟期待也許有一天,琴笙會向她一一吐露?
血肉與豔麗的圖紋交織,她竟然在煉獄中看到了他的一縷真心,也許,琴笙從來沒有變過,而是她必須跟上他的腳步──
「你好,很高興能認識你,琴三爺。」
▌本書特色
血與淚的成長,造就了如今冷血殘酷的琴三爺,每個人身上背負的過去,都是痛得無法再提起的回憶……
楚瑜和琴笙如何在不斷交手的過程中,從相互折磨的敵人成為相愛相生的伴侶?
⊙收錄網路版刪減片段和實體版特別番外,絕對精彩絕倫,鐵粉一定要補完!
作者簡介:
《作者》
青青的悠然
暢銷新銳作家。瀟湘書院金榜寫手,人氣常年居高不下,代表作《宦妃》、《九天傾凰》系列頗受讀者追捧,曾多次上實體銷售熱榜,前作《宦妃》多次斷銷並加印。
《繪者》
沉沉狐眠
95後典型雙魚座患者,喜歡紙片人,喜歡摸魚,想擁有一隻自己的小狐狸,想做一個神秘的靈魂畫師,做自己喜歡的事,畫自己喜歡的圖。
新浪微博:https://weibo.com/p/1005052816647813
TOP
章節試閱
紅袖早早的領著人待在耳房,看著日頭稍傾斜了一些,已經是平日琴笙起身的時辰,這才領著婢女們去敲門。
房間裡有溫泉,不需要她們準備熱水,但是昨晚主上和小姐一直都沒有出來,金曜也擋了她們,不讓她們進去送吃食。
不知道為什麼,紅袖就是直覺的感覺裡面應該是出事了,但是出了什麼事,她也不清楚,只是有些不安。
金姑姑聽了也覺得有些異樣,但沒有多言,只讓她候著守夜。
就這麼一夜過去了,她一大早就數著時辰準備進去伺候。
可她才準備敲門,手指還沒有碰到門,門便「吱呀」一聲打開來了。
琴笙照舊一身繡飛雲紋的白衣站在門...
房間裡有溫泉,不需要她們準備熱水,但是昨晚主上和小姐一直都沒有出來,金曜也擋了她們,不讓她們進去送吃食。
不知道為什麼,紅袖就是直覺的感覺裡面應該是出事了,但是出了什麼事,她也不清楚,只是有些不安。
金姑姑聽了也覺得有些異樣,但沒有多言,只讓她候著守夜。
就這麼一夜過去了,她一大早就數著時辰準備進去伺候。
可她才準備敲門,手指還沒有碰到門,門便「吱呀」一聲打開來了。
琴笙照舊一身繡飛雲紋的白衣站在門...
»看全部
TOP
目錄
第一章 心深似海
第二章 暗中較勁
第三章 牡丹御史
第四章 書樓之秘
第五章 情之一道
第六章 夜探鳳棲
第七章 身世之謎
第八章 吐露真心
第九章 琉島殺機
第十章 走入圈套
第二章 暗中較勁
第三章 牡丹御史
第四章 書樓之秘
第五章 情之一道
第六章 夜探鳳棲
第七章 身世之謎
第八章 吐露真心
第九章 琉島殺機
第十章 走入圈套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青青的悠然 繪者: 沉沉狐眠
- 出版社: 可橙文化工坊 出版日期:2018-10-09 ISBN/ISSN:9789869635165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84頁 開數:25
- 商品尺寸:長:210mm \ 寬:148mm
- 類別: 中文書> 漫畫/輕小說> 羅曼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