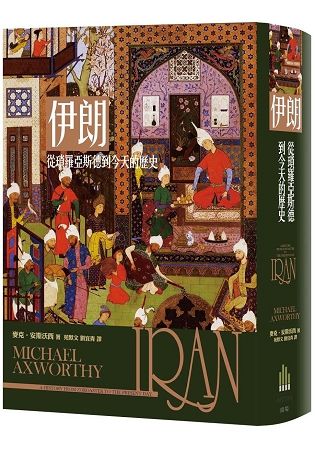關於伊朗(波斯)我們不僅知道的太少,而且大部份是誤解!
當人們提起「波斯」時,聯想的圖景是那個浪漫的國度:優雅花園中的玫瑰和夜鶯,矯健的駿馬,奇幻的故事,挑動情慾的美女,寒光四射的彎刀,像是嵌了寶石一樣發光的彩色地毯,詩歌和憂鬱的音樂 。然而在西方媒體營造出的「伊朗」則是另外的一番圖景:眉頭緊鎖的教長,黑色的石油,黑袍後面露出蒼白臉色的女子面無表情地凝視別處,兇殘的人群點燃旗幟,嘶嚎著「XX去死」的口號。這是同一國家與文明嗎?
伊朗充滿了各種悖論、矛盾和例外。大多數非伊朗人都覺得這是一個遍佈炎熱沙漠的國度,但伊朗是有高聳、寒冷的群山環繞的,它擁有富饒的農業省份,其它的地方則充滿了茂盛的亞熱帶森林,因為有各種氣候類型,這裡有多元又多彩的動植物分佈。伊朗位於伊拉克和阿富汗,俄羅斯和波斯灣之間,這裡的人在普遍說阿拉伯語的中東地區說著印歐語系的語言。伊朗一般被誤認為是一個具有強大民族文化的單一民族國家,但是例如亞塞拜然人、庫德人、吉拉克人、俾路支人、土庫曼人等等各種少數族裔人口構成了伊朗人口的一半。自1979年革命以來,伊朗的女性要遵守整個伊斯蘭世界中最為嚴格的著裝法規,然而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前所未有的大量伊朗家庭讓家裡的女孩外出讀書和工作,伊朗現有百分之六十的大學生是女性,很多女性(即便已婚)都擁有自己的工作。一個將神權與共和國結合的國家,一個高喊反美卻羨慕美式生活,1979年伊朗大學生攻佔美國大使館的同時,也沒關閉美國企業的可樂工廠。
波斯曾經打造過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包容多民族、尊重各民族傳統與信仰的大帝國。後來即使在阿拉伯人征服下,信了伊斯蘭,然而大部份時期是以什葉派為國教(其中有人為刻意的因素在裡頭),這不僅獨樹旗幟,讓它不同於其他伊斯蘭政權,而且做為少數是註定無法爭奪伊斯蘭世界的共主地位。
本書有一獨到的見解:波斯—伊朗是中東世界的晴雨計、風向雞,觀諸歷史上伊朗的動向,因為其地緣與文化魅力,後來常常成為周邊國家發展方向的預告。伊朗究竟是一個好戰勢力還是一個受害者?伊朗在傳統上是一個擴張主義國家,還是一個傳統上被動又防禦性的國家?伊朗的什葉派究竟是一群靜默主義者,還是一群暴力、持有革命性和新紀元幻想主義的人?這些問題的答案,只有從歷史中才能得到一些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