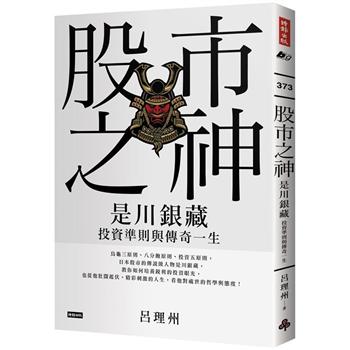2019年過世的國際知名指揮大師馬利斯.楊頌斯(Mariss Jansons),一生與諸多國際知名樂團合作共演出眾多經典演奏,指揮風格清晰且富有感染力,音色細膩、結構細緻,有「聲音的魔術師」之稱,更曾三度率巴伐利亞廣播交響樂團來臺演出。作者長年跟隨楊頌斯巡迴演出,兩人間密切的對談、與楊頌斯身邊眾人的交流觀察等,紀錄出楊頌斯最真實、生動的一面,精華呈現出楊頌斯傑出指揮家的光輝形象,以及樂壇大師對藝術的永恆熱愛與不滅成就。
紀念因熱情而生的音樂工作者、永遠的指揮明星
見證大師.楊頌斯 奉獻藝術的精彩一生
珍貴照片、生平、錄音作品資料全收錄
★繁體中文版獨家內容
巴伐利亞廣播交響樂團品牌總監
彼得.麥瑟(Peter Meisel)
精選臺灣巡迴演出照片
親撰懷念楊頌斯私房隨筆
馬利斯.楊頌斯曾經表示,比起蕭斯塔科維契、柴科夫斯基、普羅高菲夫與理查.史特勞斯這些作曲家,像他這樣子的一個樂團指揮,是不需要一本傳記的,在書中也沒什麼特別好說。然而,對於持續不斷徵求出版傳記同意的作者、或是著迷於他所創造詮釋音樂的世人,楊頌斯卻是無比值得一本傳記的——除了刻劃他傳奇指揮生涯的經歷軌跡,更流傳下他對藝術與音樂的堅持與精神啟發。
對樂團來說,楊頌斯始終以謙遜並平等的態度、與樂手們共同雕琢出更完美的音樂;對聽眾而言,楊頌斯詮釋的音樂有著自然鮮明的獨特魅力;從市場來看,楊頌斯卓越的帶團能力與攜手眾多名團的經歷,已是不敗的票房保證。這些都讓他成為受人尊敬與喜愛的指揮名家。
本書作者提爾為《慕尼黑信使報》資深音樂編輯,自二○○三年起數度參與楊頌斯率領的樂團巡演,藉由貼身觀察及多次與楊頌斯和相關人士訪談,呈現出楊頌斯臺上臺下、真誠鮮明的多樣相貌,以此本傳記展示於世,紀錄、也紀念這位指揮大師為音樂奉獻熱情的一生。
作者簡介:
馬庫斯.提爾(Markus Thiel)
生於一九六五年,《慕尼黑信使報》(Münchner Merkur)的音樂編輯,也擔任雜誌《歌劇世界》(Opernwelt)的撰稿者以及《德國唱片評論家獎》(Preis der deutschen Schallplattenkritik)的評審成員。馬庫斯.提爾自二○○三年起陪同參與馬利斯.楊頌斯與樂團的巡迴演出,期間藉由兩人的多次對談與親身觀察,深入認識見證了這位指揮名家的不凡為人與偉大的藝術成就。
譯者簡介:
黃意淳
臺灣大學哲學系畢業、德國弗萊堡大學音樂學碩士、德國弗萊堡大學藝術史博士,目前於大學任教。譯有:《一生如寄》、全球經典繪本系列:《勇敢的小裁縫》、《龍的羽毛》、《可口小圓餅的故事》、《紐約時報嚴選一百張值得珍藏的古典音樂專輯》、《棕色童話》等書。
章節試閱
第1章
第二次的誕生
就只有四個小節,就在這個著名的動機頭一次在音樂廳中精雕細琢地奏出之後不久,因為不像他自己所想像的那麼順利,這位穿著深色套頭毛衣、頭髮稍微往上梳高的年輕人,乾脆就在大家面前唱起這個樂段:「嗒、嗒、嗒、嗒——滴、滴、滴、滴——嗒、嗒、嗒、嗒——。」彷彿音樂家們不知道這段樂曲一樣;直到樂團全體合奏爆發之前,這個動機經由小提琴游移至鋼琴,之後由中提琴接手。樂團成員曾經在許多指揮家的帶領下演奏這些小節,可想而知,他們現任的音樂總監洛林.馬捷爾(Lorin Maazel)也曾這麼做過。他們曾在數不清的錄音中聽過這些小節,多半也都在求學時期曾經反覆練習。而現在,這位臉上表情嚴肅的二十八歲青年站在那裡,對於這首膾炙人口的樂曲確實地針對基本功作要求。
「這是最重要的。」他強調:「假如這三拍一起的話,一切都很妥當,請保持所有的節奏都一致,不要有一拍過快,請您們互相傾聽彼此。」馬利斯.楊頌斯對著當時的柏林廣播交響樂團(Radio-Symphonie-Orchester Berlin),也就是今天的柏林德意志交響樂團(Deutsches Symphonie-Orchester Berlin),解釋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第五號交響曲的開頭。還有,他對部份資深團員要求準確度:「請再來一次。」他的目光隔著樂團,望向斜對角上方,然後表情堅定地再一次演奏出短暫、幾乎沒有起奏的開端:「嗒、嗒、嗒、嗒——。」
就算名聲或許還無法完全跟得上同一座城市中的愛樂管弦樂團,輔導一個已經佔有一席之地的樂團有必要嗎?楊頌斯可以這麼做,甚至被期待這麼做。一九七一年九月,楊頌斯參加國際卡拉揚指揮大賽(International Herbert von Karajan Conducting Competition), 這位古典音樂界的巨擘已經關注他很久了,如今楊頌斯在柏林應該滿足大家對他寄予的厚望。比賽總共安排了五輪,部分曲目難度特別高。比賽的前面幾輪,後來的柏林交響樂團(Berliner Symphoniker)也投入參與。評審席中坐著知名人士,例如英國人華特.李格(Walter Legge),他是EMI 唱片公司深具影響力的製作人以及倫敦(London)的愛樂管弦樂團(Philharmonia Orchestra)的創立者;或者來自奧地利的漢斯.史瓦洛夫斯基(Hans Swarowsky),是那個時代最重要的指揮家導師之一。史瓦洛夫斯基在考試記錄中,對於楊頌斯以及他對於莫札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貝多芬以及史特拉汶斯基(Igor Stravinsky)的詮釋如此寫道:「《朱彼特交響曲》(Jupiter)不錯,三連音的某些部份流暢且分明,《英雄交響曲》(Sinfonia Eroica)非常好;《春之祭》(The Rite of Spring)非常好;巴爾托克(Béla Bartók)特別好。」他的總評:「與生俱來的音樂家。」
第一輪比賽中的其中一場,楊頌斯提議了選自拉威爾(Maurice Ravel)《達夫尼與克羅埃》(Daphnis et Chloé)芭蕾舞曲中的片段,雖然他對此也有所疑慮:如此棘手的樂曲比較不適合這個時候,所以有人推薦貝多芬的第五號交響曲;作為妥協,楊頌斯可以在大賽的閉幕音樂會指揮拉威爾的這首作品。一九七一年秋天的影片拍攝中,不只顯現了彩排時、還有音樂會上的楊頌斯。他以極度的明朗與最強的專注力,成功掌握了貝多芬這首作品從第三樂章至第四樂章難以處理的過渡。片中一再出現他駕馭樂團的眼神,不光只是打拍子、對於兩個樂章明顯的敏銳度、以及對於樂團的持續調整。
閉幕音樂會時就是《達夫尼與克羅埃》這首曲子。「我當時非常緊張,」馬利斯.楊頌斯後來回憶說:「卡拉揚(Herbert von Karajan)就坐在音樂廳裡,我對於自己當天指揮的音樂表現並不滿意,我想要在這個作品中表達的東西,並沒能夠做到。」
楊頌斯這樣的表現並沒有充分發揮他的實力。波蘭—以色列指揮家加布里耶.齊穆拉(Gabriel Chmura)贏得首獎,第二名則是由楊頌斯跟波蘭來的安東尼.維特(Antoni Wit)一起共享,第三名是由保加利亞人艾米爾.查卡洛夫(Emil Tchakarov)所奪得。然而,真正被許多大賽觀眾以及媒體所重視的結果卻是楊頌斯。他接受許多訪問、獲得善意的評論、給人最成熟的印象,再三有人稱說:「那個俄羅斯人楊頌斯,就算在音樂會中同時演出貝多芬第五號交響曲與《達夫尼與克羅埃》,也能出色過關。」一個電視報導強調:「這是一位懂得總譜以及指揮藝術的年輕高手。」
柏林的觀眾以他們自己的方式作出反應,一位聽眾對著攝影機說:「那個俄羅斯人很了不起。」頒獎典禮時,卡拉揚再次站上指揮臺,以守護者的表情,按了按他學生的肩膀。人們看得出誰才是他真正的心頭好;而且對於有希望成功的人來說,比起一枚銀牌,身體語言更能說明一切,這等於是第二次的誕生:「我不再是阿爾維茲.楊頌斯(Arvīds Jansons)的兒子。」他後來說:「我就是楊頌斯。」
楊頌斯第一次的誕生發生於二十八年以前,一九四三年拉脫維亞(Latvia)的冬天。可以確定的是當時沒有完善的照料以及相應的醫療設備,而是籠罩在死亡的危險之中。伊蕾達.楊頌斯(Iraida Jansons)出身於一個猶太家庭,因為里加(Riga)被德國人所佔領,而將自己藏匿在這個城市。她的兄弟與父親已被納粹親衛隊所殺害,她害怕自己也會被逮捕、被驅逐出境。在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那天,她在這個幾乎已經不存在的國家生下了她的馬利斯.楊頌斯。拉脫維亞自從一九四一年開始就被德國所佔領,這個國家卻在德國納粹國防軍進駐之前,已經因為蘇維埃占領軍而受盡精神創傷達一年之久。數以千計的拉脫維亞人被帶往西伯利亞(Siberia),遭受恐怖統治德國人被許多人視為救星而受到歡迎。有些人認為他們是較為輕微的禍害,另外一些人則視他們為希望;來自西邊的侵略者也可能仰賴賣國賊的協助。
不管是從外面傳入,還是在潛意識中已經存在很久,災難性的反猶太主義開始繁盛起來,這對於猶大居民等同是判了死刑。直到一九四一年晚秋,猶太教徒幾乎被滅絕,將近三萬猶太人在倫布拉(Rumbula)森林大屠殺中被殺害。就在這不久之前,里加才出現了強行規劃的猶太人區——所謂的「莫斯科城郊」(Maskavas Forštate),塞滿了成千的猶太人。因為從西歐被驅逐出境的猶太人也必須被安置在這裡,所以居住
條件急遽惡化。
共同生活變得讓人不堪忍受,於是許多人就從城市被運送到拉脫維亞的森林中處死。一九四三年六月,就在馬利斯.楊頌斯出生幾個月之後,納粹親衛隊全國領袖海因里希.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下令,在拉脫維亞也應該要建造集中營。里加的猶太人區逐步被解散,只有一小部份的拉脫維亞猶太人可以逃脫這可怕的命運;他們被藏匿、被包容、被仁慈的同胞援助,伊蕾達.楊頌斯與她唯一的孩子馬利斯就屬於這群人之中。
當時這位受迫害的女性嫁給了指揮家阿爾維茲.楊頌斯,這是一個音樂家聯姻:他是在指揮臺上受人尊敬的指揮,在那之前是歌劇院樂團的小提琴手;而她則是次女高音。戰爭終於結束,精神上的恐懼卻仍遲遲尚未獲得緩解,兩個人都受他們家鄉里加的歌劇院聘用。這對夫婦沒有能力、也不想僱用保姆,頂多只是請了清潔婦幫他們的公寓維持整潔,所以他們幾乎天天帶著小馬利斯到劇院去上班;這似乎沒有太困擾他,小馬利斯探索舞臺跟更衣間後面的那些神秘通道,總是被唱著歌、跳著舞以及拉著樂器的人們所圍繞。
(未完待續)
第2章
父親形象
沒有人知道這件事。有個人在擔任很長一段時間、同時不討喜的助理指揮的角色之後,在跟父親的戰鬥以及重複的侮辱之後,正式作為指揮的首次登臺演出——並非在大都會的市中心,而是在一座鄰近城市;不是跟重量級的交響樂團或者歌劇院合作,而是小歌劇院,演出節目表上則是卡爾.米爾洛克(Carl Millöcker)的輕歌劇《加斯帕羅內》(Gasparone);而為了不要讓父親與兒子受到姓氏困擾,這所有一切都以藝名進行。所以一九五五年二月「卡爾.凱勒」(Karl Keller)站上一家餐館的指揮臺,這間餐館作為波茨坦(Potsdam)漢斯.奧圖劇院(Hans Otto Theater)的取代演出場所。這些與卡爾——後來的卡洛斯.克萊伯(Carlos Kleiber),也就是令人非常尊敬的艾利希.克萊伯(Erich Kleiber)的後裔——有關的這件事,只有知情人士知道。
一段複雜並且搞砸的父子關係在此或許結了稀有的果實。在二十世紀,沒有其他懷著自己的音樂理想以及不凡天賦的指揮家後代,要經歷承受如此沉重的發展。只要提到另一個指揮世家事件,艾利希.克萊伯與卡洛斯.克萊伯的例子幾乎就會自動地浮出眼前。在馬利斯.楊頌斯的生命中,也有一個強勢、著名且鮮明的父親形象,這是一個就算他沒有走上藝術家的道路,也受他尊敬、讓他讚歎以及為其奉獻的榜樣,跟克萊伯父子之間有著明顯且決定性的不同。
阿爾維茲.楊頌斯於一九一四年十月十日出生於拉脫維亞的港口城市利耶帕亞(Liepāja),這座城市當時還屬於俄羅斯帝國。他有三個姐妹以及一位兄弟,而且是到目前為止,這個家族中唯一的音樂家。自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五年,他在市立音樂學院攻讀小提琴,也是為了能夠在經濟上支持家庭。五年後,阿爾維茲.楊頌斯已經是里加歌劇院管弦樂團的第二小提琴成員,有一次他也在艾利希.克萊伯指揮下演出;同時,他也另外跟著必須從德國移居國外的雷歐.布勒希(Leo Blech)研讀作曲與指揮。
二次世界大戰時,有超過百分之四十的拉脫維亞藝術家必須離開自己的國家,因此為了讓劇院生態可以運作如常,迫切地需要指揮家。三十歲的阿爾維茲.楊頌斯獲得屬於他的機會,他終於可以站上指揮臺;剛開始主要是指揮芭蕾舞劇,後來才加入歌劇。有別於今天的劇院系統,當時藝術界的美中不足並非是芭蕾舞劇指揮較不被重視,而是音樂總監幾乎對芭蕾舞劇首演不感興趣。
在那個時期,里加歌劇院每個演出季節會推出五場新製作,不是三場歌劇與兩場芭蕾舞劇,就是反過來。芭蕾舞劇這個表演類型很受佔領政權的蘇維埃士兵與其他公民喜愛,不只是因為比起以拉脫維語演出的歌劇、芭蕾舞劇,較沒有理解上的困難,也是因為拉脫維亞上流階級傳統上就喜歡芭蕾舞劇,阿爾維茲.楊頌斯於是迅速成名。
他被指定演出幾乎所有的芭蕾舞劇首演,但是同時也接下歌劇演出,大部份是首席指揮的劇碼。一九四五年,在他的行事曆上可以發現《托斯卡》(Tosca)、《奧泰羅》(Otello)、《茶花女》(La Traviata)、《黑桃皇后》(Pique Dame)、《卡門》(Carmen);更重要的卻是芭蕾舞劇《唐吉訶德》、《萊瑪》(Laima)、《睡美人》(Dornröschen)、《紅罌粟》(The Red Poppy)以及《玫瑰花魂》(Le Spectre de la rose)。多虧一九二○年的一條法律,國家歌劇院享有一個特
別的地位:國家的預算受到保障,公家支援資助歌劇與芭蕾舞劇作為國家文化的一部份,更多的是:作為國家認同的一部份。
就此而言,楊頌斯這個家庭不只是因為父親的職業而享有特權,也是因為他們在國家的眼中,一起參與了國家自我認同的保存與後續發展。他們因此與當時波羅的海三國只知道農業或者工業產品的社會真實狀況脫節,這樣的地位並沒有伴隨著政治的壓制一起發生。阿爾維茲.楊頌斯在蘇聯帝國中避免了政黨黨員身份,與此有關的公開以及官方表述對他來說完全陌生,而在四○年代的後半段直到史達林(Joseph Stalin)去世前的政治脅迫越發嚴重——對劇院界意謂著一段非常艱困的時間。
在他們的對話中,雙親不讓他們唯一的孩子受這種話題的困擾,他們寧可談論歐洲舞臺所經歷的魔幻力量與虛構世界,可以視為對於現實的逃避。「整體來看,我有一個愉快的童年。」馬利斯.楊頌斯證實。父母避免過於寵溺兒子,並且避免利用自己的地位。「假如所有的事情都過於順利成功——父母讓所有一切都變得可能,我認為這樣是危險的。」有一次,兒子無論如何想要一臺玩具車,這個希望卻被拒絕,楊頌斯回憶說:「我相當難過,卻也被教育:生命不是如此快活與簡單,像它有時對我們所顯示的這樣。」
在風格上,阿爾維茲.楊頌斯不是在作品中情感迷失的指揮家,也不會表現出特別的虛榮心。這個概念可能有點陳腐,他卻是音樂僕人的最佳代言人。直到今天還有紀錄可以證明:影片顯示出他絕對清晰、技巧熟練取向然而卻從不過於冷靜的手勢信號表達,這也反映在作品詮釋:例如柴科夫斯基《天鵝湖》的演出是如此清楚明確以及缺乏熱情,卻同時保持非常靈活的速度。阿爾維茲.楊頌斯避免冗長、模糊以及平淡乏味,非常注意細節、新鮮、帶有許多活力與攻擊效果所指揮的白遼士(Hector Berlioz)《幻想交響曲》(Symphonie fantastique),是對此最好的說明。一段莫札特《安魂曲》(Requiem)的錄音形成了一個近乎奇異稀有的特例。其速度甚至比塞爾吉烏.傑利畢達克(Sergiu Celibidache)所指揮的版本更加緩慢、更加極端。〈悲慘之日〉(Lacrimosa) 可能是演出歷史中最慢的版本,突然停頓、停止中斷,儘管如此,這獨特的魔力也訴說了許多詮釋者對於內容的反思以及宗教虔誠。即使在速度放慢的時刻,阿爾維茲.楊頌斯如何讓情感緊繃、控制它的堆疊攀升以及注意如歌的旋律性,這些透露了一些他技巧上的純熟穩健。
一九四七年至一九五二年之間,阿爾維茲.楊頌斯是拉脫維亞廣播交響樂團(Latvian Radio Orchestra)固定合作的客席指揮,一直到他在大戰後贏得第一次列寧格勒指揮大賽。他獲得了當時已經充滿傳奇性的列寧格勒樂團提供的職位,成為葉夫根尼.穆拉汶斯基(Yevgeny Mravinsky)的助理指揮。阿爾維茲.楊頌斯並沒有猶豫太久,就接受了這個職位,更換至列寧格勒。剛開始他是位列庫爾特.桑德林(Kurt Sanderling)之後的第二助理位置,後來桑德林去了東德,阿爾維茲.楊頌斯就晉升遞補其職位。
阿爾維茲.楊頌斯把妻子跟小孩留在里加,四年之後這個家庭才在俄羅斯的大都會再度團聚。在作出這個決定之前,夫妻兩人之間應該進行過很多的對話,然而可以確定的是,阿爾維茲.楊頌斯的人生座右銘也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對此他也曾跟兒子談過,而馬利斯.楊頌斯之後將這當成自己的信條,即使他無法總是依此行事:「我經常問我爸爸:要如何決定自己的生命?他總是會說:重要的是你要問問你的心,它會給你正確的答案。就在提出這個問題之後的第一時間,你就已經獲得答案,你必須傾聽它;晚了一秒鐘,就可能會太遲,因為你的頭腦已經啟動。」
在列寧格勒,阿爾維茲.楊頌斯在充滿傳奇性的愛樂管弦樂團旁擁有一間小公寓,妻子與小孩有時會來探望他,他們必須適應這擁擠的空間。這個如此困擾此家庭的突然改變有許多原因:其中一個原因是,阿爾維茲.楊頌斯知道在波羅的海的另一端,等待他的是高出許多的音樂水準,以及與其相應的機會;另一個原因是跟里加的首席指揮雷歐尼茲.維格納斯(Leonīds Vīgners)有著人際氛圍上的問題,阿爾維茲.楊頌斯深知自己在那裡無法繼續發展。他的辭職造成了負面的後果:幾個月後,伊蕾達.楊頌斯失去了在歌劇院的工作,對於妻子與孩子來說,開始了一段艱困的過渡時期。「許多拉脫維亞人當時嫉妒我父親。」馬利斯.楊頌斯說:「他們對他的離開覺得生氣,但是當他成名時,突然所有人都為他感到驕傲。」
即使發生了這一切, 父親這個榜樣的新職位仍讓兒子神往: 九歲時, 他就熟記列寧格勒愛樂(Leningrad Philharmonic Orchestra)兩百二十位成員的姓氏,即使他到這個時間點一次也沒去過涅瓦河(Neva)畔的這個城市。一九五六年,阿爾維茲.楊頌斯終於將他的小家庭接到他身邊,表面看起來,這是一個大團圓、是家庭關係的確定澄清;但對於兒子而言卻是一場災難,或許是馬利斯.楊頌斯生命中影響最為重大的一個階段。
(未完待續)
第1章
第二次的誕生
就只有四個小節,就在這個著名的動機頭一次在音樂廳中精雕細琢地奏出之後不久,因為不像他自己所想像的那麼順利,這位穿著深色套頭毛衣、頭髮稍微往上梳高的年輕人,乾脆就在大家面前唱起這個樂段:「嗒、嗒、嗒、嗒——滴、滴、滴、滴——嗒、嗒、嗒、嗒——。」彷彿音樂家們不知道這段樂曲一樣;直到樂團全體合奏爆發之前,這個動機經由小提琴游移至鋼琴,之後由中提琴接手。樂團成員曾經在許多指揮家的帶領下演奏這些小節,可想而知,他們現任的音樂總監洛林.馬捷爾(Lorin Maazel)也曾這麼做過。他們曾在數不清...
作者序
【自序】
前言
事情應該不是這樣的,我們還約好要講個長時間的電話,主要是想談論關於穆索斯基(Modest Mussorgsky)的歌劇《鮑里斯.戈東諾夫》(Boris Godunov),二○二○年夏天他打算在薩爾茲堡音樂節(Salzburger Festspiele)指揮這齣歌劇。終於他要這麼做了,因為對他來說,比起其他許多樂種,歌劇更為珍貴。而且,馬利斯.楊頌斯(Mariss Jansons)或許也能對於這本書提供一些細節或者修正,雖然他從未將自己視為不斷干預、審查每段引語的權威當事人。然而卻在電話之約的前幾天,二○一九年十二月一日的夜裡,他逝世於家鄉聖彼得堡(St. Petersburg)。正因為他還有這些計劃,另外也想逐漸從指揮臺上引退,他的過世來得如此突然,這是讓音樂界陷入震驚、頓口無言的一天。
儘管如此,剛開始他對於這個出書計劃懷著非常存疑的對立態度。德米特里.蕭斯塔科維契(Dmitri Shostakovich)值得幫他出一本書——在我們對話的初期他就這麼說過。還有彼得.柴科夫斯基(Pyotr Ilyich Tchaikovsky)、謝爾蓋.普羅高菲夫(Sergei Prokofiev)以及理查.史特勞斯(Richard Strauss)也是,整體而言就是所有那些、他會定期將他們的樂譜放在譜架上指揮帶領團員演出的作曲家。但是樂團指揮?或者是各種類型的普通藝術家?表演者、模仿者、一首由天才人物所創造作品的實現者,這樣的人不需要傳記——楊頌斯是這麼想、這麼說的,這樣一本關於他的書,究竟有什麼可告知那些相關者的?
人們可以將這類請求視為是奉承而覺得輕蔑,認為是諂媚而表示拒絕,或許也可以認為是源自恐懼的懷疑而想要放棄。楊頌斯對此卻是認真嚴肅看待,而且也花了很長的一段時間,他才同意出版傳記以及跟我合作。他很愛說:「我並沒有被說服。」這是所有跟他共事的人都聽過的一句話。音樂家就不用說了,不同樂團的行政工作人員、經紀人、劇院經理以及導演都聽過。這不是否定、不是肯定、不是也許,也不是「我不知道」。這個句子傳達出質疑,楊頌斯知道,這個保持懷疑的態度緘默、有趣且折磨人,卻同時也是重要、值得並有益處的,此態度是他職涯初始就在身旁的夥伴,他一直都沒有甩開它,因為他無法、也不願意。
因為這樣的一本書基本上根本不適合這位藝術家,就像這本傳記想要顯示的,楊頌斯是指揮家巨星之中極為自相矛盾的存在——一方面他有這麼如此筆直無礙的事業歷程,以讓人印象深刻的著名指揮家形象開始;繼續前進到一個較為次級的管弦樂團,這個樂團因為楊頌斯而變成一流;後來以一種漂洋過海的實驗方式繼續,最終在兩個世界級樂團的首席指揮位置獲得圓滿成功。最後,這位指揮家到達傳奇狀態,賽門.拉圖(Simon Rattle)曾經說過:他是我們之中最優秀的(順帶一提,這也不是奉承)。
另一方面,這所有的一切都在楊頌斯沒有玩弄外在形式的各種公關花樣狀況下發生;在他沒有操弄所謂的古典音樂市場需求的狀況下發生。楊頌斯的職業生涯發展過程並沒有伴隨著喧鬧雜音,這樣的雜音在其他人那兒慈悲地掩蓋他們的不足;而且當他有時候同意並且運用這樣的策略時,換來的就會是一個讓所有參與者經常感到精疲力竭的重新調整程序(「我並沒被說服」)。
除了他的生命歷程描述以及生平不同階段的確切闡述之外,在這本書中的全面觀點也應該被當作主題。儘管如此,這些敘述與意義都遵循楊頌斯的樂團歷程,因此有時候可能會出現侷限於主題的重疊、對比以及時間上的跳躍。假如這本傳記並不總是依照時間順序,那也是因為想要透過這樣的方式,強調穩定性與交叉引用。
例如,關於楊頌斯在他的樂團首席指揮角色中的指揮家自我認知的那些問題,屬於這裡主要討論的對象;作為表演者的問題也一樣,他在所有的音樂工作以及樂團指導教育方面觀念清楚,對於同事態度以及演出實務的其他方向保持開放態度。
此外,本書也要談論楊頌斯作為一位藝術家對於自我的認識。這位藝術家對於準備工作與分析簡直非常著迷,他的工作態度也影響了樂團:儘管楊頌斯在偉大、不可侵犯以及君主般充滿威嚴的音樂大師時代被社會化,他卻從未只為了貫徹自己的意志,而仰仗他的權威領導者工具。爭論就已經足以表現他在工作上所立下的生命榜樣,同時卻也損害了他的健康,在此還顯現了一個他生涯上的矛盾:他的生涯紮根於指揮主宰的時代,並且在指揮成為同類之首的時代得以實現,即使鶴立雞群——現在卻成為自信音樂家的夥伴,這是一個楊頌斯要去適應的變化,這個變化同時也改變了他。
楊頌斯為了他的工作而完全消耗殆盡,這也讓他成為被所有人所尊敬、崇拜以及愛戴的藝術家。也有人們充滿懷疑地站在他的對立面,其中也不乏音樂家。但是楊頌斯從未與開放且無法排除的否定交鋒,如同這本書想要表現的:他在全世界的音樂界中是個特例,因為他表現得全然經得住攻擊,而且有時候也遙不可及。楊頌斯擁有很明顯的個性特質,卻毫無習氣。這些不只在他作為演出者的角色,同時也在他作為熱心、無法動搖以及固執的文化政治家時顯現出來。不管是在匹茲堡(Pittsburgh),他爭取樂團的留存時;或者是在慕尼黑(München),他促使新音樂廳得以成功建造,這是馬利斯.楊頌斯從一開始就義無反顧地確認要達成的計劃(這跟許多參與者以及並肩作戰者相反)。或許這也因此成為他最重要的終生志業,即使他從未能踏上這座音樂廳的指揮臺。
【自序】
前言
事情應該不是這樣的,我們還約好要講個長時間的電話,主要是想談論關於穆索斯基(Modest Mussorgsky)的歌劇《鮑里斯.戈東諾夫》(Boris Godunov),二○二○年夏天他打算在薩爾茲堡音樂節(Salzburger Festspiele)指揮這齣歌劇。終於他要這麼做了,因為對他來說,比起其他許多樂種,歌劇更為珍貴。而且,馬利斯.楊頌斯(Mariss Jansons)或許也能對於這本書提供一些細節或者修正,雖然他從未將自己視為不斷干預、審查每段引語的權威當事人。然而卻在電話之約的前幾天,二○一九年十二月一日的夜裡,他逝世於家鄉聖彼得...
目錄
目錄
獨家.典藏照片精選
繁體中文版獨家內容——懷念楊頌斯 私房隨筆
前言
1 第二次的誕生
2 父親形象
3 走向指揮臺的第一步
4 與蘇維埃切斷臍帶
5 與奧斯陸的瘋狂婚姻
6 藉由柴科夫斯基的再度加速
7 俄羅斯的誘惑、國際性的勝利
8 英國與維也納的外遇
9 生命重大轉折——心肌梗塞
10 憤怒中的告別
11 適應匹茲堡
12 對峙與警報聲響
13 蛻變中的美國樂團
14 慕尼黑的啟程與變革
15 阿姆特丹皇家大會堂的騎士受封儀式
16 幫慕尼黑音樂會世界加些調味料
17 阿姆斯特丹的初步嘗試
18 新的音樂廳戰役
19 回歸歌劇
20 跟慕尼黑的樂團周遊世界
21 詮釋與坦誠
22 個人的最愛
23 維也納新年音樂會
24 慕尼黑的日常壓力與取消演出
25 在行程壓力下的阿姆斯特丹大師
26 慕尼黑音樂廳——終生志業
27 阿姆斯特丹終曲
28 柏林的誘惑
29 短暫訪問以及現代音樂作品
30 音樂節歌劇與舒伯特驚喜
31 災難性的柴科夫斯基
32 最後的登臺演出
尾聲
致謝辭
附錄——生平簡歷、錄音作品目錄
目錄
獨家.典藏照片精選
繁體中文版獨家內容——懷念楊頌斯 私房隨筆
前言
1 第二次的誕生
2 父親形象
3 走向指揮臺的第一步
4 與蘇維埃切斷臍帶
5 與奧斯陸的瘋狂婚姻
6 藉由柴科夫斯基的再度加速
7 俄羅斯的誘惑、國際性的勝利
8 英國與維也納的外遇
9 生命重大轉折——心肌梗塞
10 憤怒中的告別
11 適應匹茲堡
12 對峙與警報聲響
13 蛻變中的美國樂團
14 慕尼黑的啟程與變革
15 阿姆特丹皇家大會堂的騎士受封儀式
16 幫慕尼黑音樂會世界加些調味料
17 阿姆斯特丹的初步嘗試
18 新的音樂廳戰役
19 回歸歌劇
20 跟慕尼黑的樂團周遊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