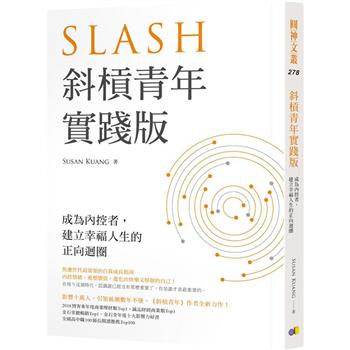2016全美最受矚目小說,美國筆會福克納文學獎、英國柑橘文學獎得主安.派契特最新力作
一個情不自禁的吻,把兩個婚姻吻出裂痕,卻也讓兩個家庭永遠結合
助理檢察官伯特,把最好的狀態獻給工作,原本期許自己將週末留給家庭,但面對三個活蹦亂跳的孩子以及懷孕的老婆,擁有自己的時間是一種奢侈。這天,他突然想起有一場受洗派對,派對主人是個警察,兩人在多年前因為工作有過一面之緣,雖然不熟,仍然從家裡帶了一瓶琴酒當作禮物,決定藉此享受一個悠閒的下午。
派對舉辦在陽光明媚的洛杉磯,警察的妻子貝芙莉是伯特見過最美麗的女人。淡淡香水味的誘惑,以及與家裡蓬頭垢面的老婆對比之下,他情不自禁地吻了手裡抱著剛出生女兒的貝芙莉。兩人一見鐘情、再婚、開始新的人生,而來自兩個家庭的六個孩子,用他們的一生學習適應這突如其來的改變⋯⋯
美國筆會福克納文學獎、英國柑橘文學獎得主安.派契特最新暢銷小說《完美家庭》是她的第七本小說,講述來自兩個家庭的六個孩子,面對父母離異、再婚、重組新家庭,往後五十年的成長故事。作者安.派契特首次將創作與自己的生活聯結,寫出扣人心弦、笑中帶淚的故事線,讓人翻開第一頁就停不下來。
得獎紀錄
✹ 紐約時報年度好書
✹ 時代雜誌年度好書
✹ 華盛頓郵報年度好書
✹ 美國主持天后歐普拉評選最愛小說
✹ 柯克斯書評最佳小說
✹ 全美書評人協會(NBCC)最佳小說決選
各界好評
「若父母當初沒有做出災難性的決定,而我們也沒有以災難性的方式回應他們,我們將會變成什麼模樣?可能會成為更靈活且活得更輕鬆的大人,也可能是相反的⋯⋯拿起《完美家庭》,根本不可能放下。」——紐約時報
「派契特寫下父母與手足的故事,何謂成長及放手。無法想像有比《完美家庭》更好的作品⋯⋯」——時代雜誌
「派契特透過帶有內疚及寬恕的家庭故事,引領我們前往奇蹟且真實的療癒之處。」——華盛頓郵報
「閱讀《完美家庭》就好像你一腳踏入作者那充滿柳橙汁的回憶,看著故事場景在眼前浮現、身歷其境般進入那發自內心的情緒。這是本與派契特最有關聯性的小說,也無庸置疑是她最棒的作品。」——洛杉磯時報
「派契特用《完美家庭》告訴我們,戲劇性不需要槍、洪水、火藥或是恐怖份子,光日常生活就足夠殺死我們了。」——美國全國廣播電台
「《完美家庭》觀察敏銳、銘心刻骨,讓人為年少時代感到疼痛,同時感激那甜蜜的痛苦都已經過去了。」——O:歐普拉雜誌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完美家庭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2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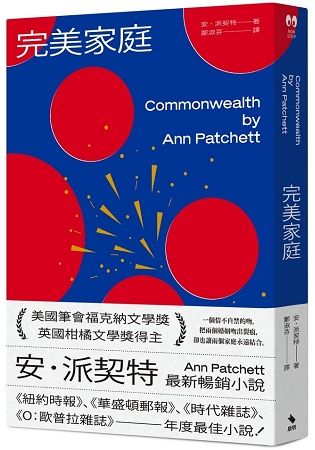 |
完美家庭 作者:安・派契特 / 譯者:鄭淑芬 出版社:啟明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8-07-13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10 |
二手中文書 |
電子書 |
$ 220 |
歐美文學 |
$ 300 |
美國現代文學 |
$ 300 |
小說 |
$ 342 |
中文書 |
$ 342 |
英美文學 |
$ 342 |
Literature & Fiction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圖書名稱:完美家庭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安•派契特 Ann Patchett
1963年於美國加州出生,作品首次刊登於《巴黎評論》,後來在女性雜誌《十七歲》擔任非小說類作家。曾於1990年擔任美國麻州普羅文斯頓駐市作家,1992年出版第一部小說《騙子的守護神》,並由電視台改編為電影。1997年入圍英國柑橘獎,2002年以《美聲俘虜》獲美國筆會福克納文學獎、英國柑橘文學獎,入圍美國國家書評獎,於全球譯為三十餘種語言。著有七本小說及三本非小說。《魔術師的助手》及《奇蹟之邦》皆入圍英國柑橘文學獎,現為田納西州納士維市Parnassus書店的合夥人。
2006年獲邀擔任年度美國最佳短篇小說(The Best American Short Stories)等文選的主編,也是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雜誌、哈潑雜誌、大西洋月刊、Gourmet美食雜誌、Vogue等媒體的固定撰稿人。現與丈夫居住在田納西州。
譯者簡介
鄭淑芬
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肄業(修畢學分),主修國貿、英文、翻譯。具備教育部中英翻譯能力英譯中證書,目前專職翻譯。譯有:《幸福大道》、《不抱怨的關係》、《真愛旅程》、《少女死亡日記》、《美麗的廢墟》、《我想離開你》、《夜行動物》、《別人不敢做的事》等書。
譯文賜教:ajanejane@gmail.com
安•派契特 Ann Patchett
1963年於美國加州出生,作品首次刊登於《巴黎評論》,後來在女性雜誌《十七歲》擔任非小說類作家。曾於1990年擔任美國麻州普羅文斯頓駐市作家,1992年出版第一部小說《騙子的守護神》,並由電視台改編為電影。1997年入圍英國柑橘獎,2002年以《美聲俘虜》獲美國筆會福克納文學獎、英國柑橘文學獎,入圍美國國家書評獎,於全球譯為三十餘種語言。著有七本小說及三本非小說。《魔術師的助手》及《奇蹟之邦》皆入圍英國柑橘文學獎,現為田納西州納士維市Parnassus書店的合夥人。
2006年獲邀擔任年度美國最佳短篇小說(The Best American Short Stories)等文選的主編,也是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雜誌、哈潑雜誌、大西洋月刊、Gourmet美食雜誌、Vogue等媒體的固定撰稿人。現與丈夫居住在田納西州。
譯者簡介
鄭淑芬
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肄業(修畢學分),主修國貿、英文、翻譯。具備教育部中英翻譯能力英譯中證書,目前專職翻譯。譯有:《幸福大道》、《不抱怨的關係》、《真愛旅程》、《少女死亡日記》、《美麗的廢墟》、《我想離開你》、《夜行動物》、《別人不敢做的事》等書。
譯文賜教:ajanejane@gmail.com
圖書評論 - 評分:
| |||
|
|

 2018/07/24
2018/0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