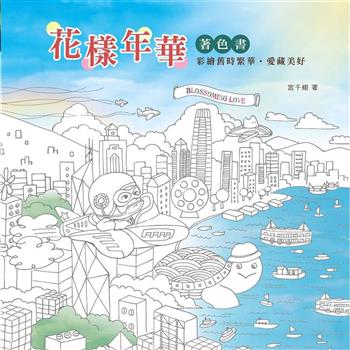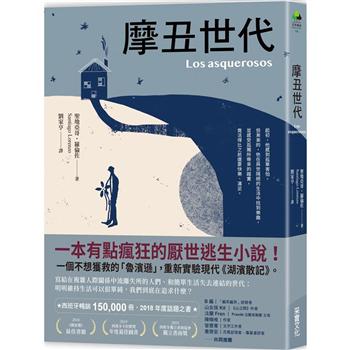害怕的我、生氣的我、孤單的我……
哪一天,我才能不感到絕望,不再受傷,
哪一天,星星才會真正為我而閃亮呢?
==本書特色==
★本書榮獲WeRead閱讀獎、《衛報》、英國書獎年度童書獎得主、大英帝國軍官勳章作者賈桂琳‧威爾森讚譽、英國水石書店讀者★★★★★評論
★陳安儀(親職作家)、邱慕泥(戀風草青少年書房)、陳品皓(好日子心理治療所執行長)鄭重推薦
★入選台北市立圖書館好書大家讀陳安儀老師寒假推薦書單、文化部第三十八次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推介的《泡泡紙男孩》作者新書
==內容簡介==
害怕的比利、生氣的比利、孤單的比利……
比利討厭吸毒的媽媽、施虐的繼父,更別說是不了解他的寄養家庭…
比利只想照顧自己的雙胞胎弟妹,讓他們能有一個完整的「家」,
但他連這個願望也無法完成……
比利討厭遵守規矩、上課學習,也厭惡四周的保護官。他忘不了繼父每一拳打在身上的時刻,每次大人說一套做一套的噁心假象,每次夢想落空的失望……
比利最在意的人是十歲的弟弟妹妹,他說故事,為他們烹煮一頓真正的晚餐。比利願意遵守育幼院的規矩,只希望大人別把弟弟妹妹送去寄養家庭……
另一位能讓比利冷靜的是育幼院的「上校」朗尼。比利認為朗尼和其他保護官一樣,只是因為領薪水才關心他。他不信任朗心的教導,直到朗尼為他打造了一間專屬的健身房,還讓比利可以盡情的揍他……
偶遇的黛西,是比利平凡的日子裡唯一特別的事。他總算能找到一個沒那麼討厭、沒有說話不算話的人。黛西送給比利一顆貼在房間會發亮的星星。比起房間裡那些已經陳舊、再也不會發亮的星星,黛西的禮物是比利個人專屬的,她讓比利的生活開始有了期盼,直到他發現黛西一個令人憤怒的祕密……
究竟哪一天,比利才能不感到絕望,不再受傷,
哪一天,星星才會真正的閃亮呢?
本書深度描寫少年當下處境,孤立無援的心情與祈求美好未來的心願,本書是一部探討自我成長、拯救迷惘青春,以及重擊人們心靈的感動故事。
==本書殊榮==
★肯定生命的價值,內容充滿救贖,實實在在是本好書。──《衛報》
★菲力‧厄爾以嚴厲的筆法描寫劣勢孩童的境遇,處理方式敏感細膩。這部精采引人入勝的小說讓我感動落淚。──英國書獎年度童書獎得主、大英帝國軍官勳章作者賈桂琳‧威爾森
★《等星星發亮的男孩》令人愛不釋手──內容真實赤裸。比利是個毫無畏懼的孩子……頑強、勇敢又富有同情心。──《16歲的最後心願》作者珍妮‧唐涵
★動人且充滿震撼力。我超愛這本小說。──《我想,我可能是瑪莎》作者蘇菲‧麥肯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