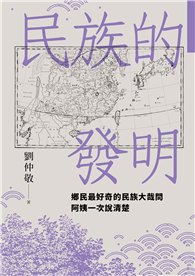伍 大門口的陌生人
西曆七月二日,英國遠征軍的先遣隊繞過牛鼻水道,進入舟山水域。先遣隊是由四條兵船、兩條火輪船和兩條運輸船組成的,艦隊司令伯麥準將和陸軍司令喬治.布耳利少將都在這條船上。
伯麥畢業於普利茅斯皇家海軍學校,在拿破崙戰爭期間,參加了墨西哥灣大海戰和特拉法加大海戰,還參加過英緬戰爭。十五年前,他被派往澳大利亞。澳大利亞是塊新開發的不毛之地,人煙稀少,生存條件十分惡劣。他奉命勘測、考察澳大利亞北部和西部海域,繪製詳細的海圖。
伯麥血性耐勞,辦事果斷,思維縝密,是個頗有主見的人。英國政府中有人認為澳大利亞北部是人煙罕見的戈壁灘,不宜建立殖民地,伯麥卻堅持己見,屢歷挫折而不悔,先後在梅爾維爾島和考伯半島建立鄧達斯要塞、威靈頓要塞和埃星頓要塞,為英國的拓土殖民事業立下汗馬功勞。
六個月前,他接到海軍大臣的書面命令,要他出任東方遠征軍的艦隊司令,他立即率領「威裡士厘號」、「都魯壹號」和「鱷魚號」駛往新加坡集結待命,他本人則親自趕往加爾各答拜會印度總督奧克蘭勛爵,商討組建艦隊事宜。
喬治.布耳利是一個六十多歲的老軍官,他也接到通知,要他出任東方遠征軍的陸軍司令。布耳利十五歲從軍,參加過西印度群島戰役、加拿大戰役和印度次大陸的麥蘇爾戰役,具有豐富的登陸作戰經驗。四年多前,他率領英軍第十八步兵團進駐錫蘭(今斯里蘭卡),被任命為可倫坡駐軍司令。
艦隊進入舟山水域後降低了航速。舟山水域海水較淺,列島林立、暗礁叢生,水情十分複雜。它距離大浹江(現在的甬江)出海口很近,大浹江水裹挾著大量泥土和腐殖質流入大海,把一百多里寬的水面染成一片渾黃。在渾濁不清的淺水中行船是非常危險的。伯麥雖然有海圖,卻是商用海圖,遠不能滿足軍事需要。他命令艦隊一面行駛,一面測量水流、水速和水深,探明所有暗礁和沙線,繪製出更詳細的海圖。
海面上有不少中國漁船,不期而至的外國艦隊引起了漁民的注意。多年的航海經驗告訴伯麥,任何國家都不會在情況不明時攻擊外國艦隊。為了不打草驚蛇,他命令全體官兵不得顯示出任何敵意,除非受到清軍水師的攻擊。他要製造一種假象─先遣隊是支迷途的外國艦隊,偶然經過這裡,需要補充淡水和食物。
旗艦「威裡士厘號」是排水量一千七百八十八噸的三級戰列艦,配有七十四位卡隆炮 和五百九十名官兵,儼然是座海上城堡。「馬達加斯加號」火輪船更惹人矚目,舟山漁民從來沒有見過冒黑煙的蒸汽機和旋轉的蹼輪,他們遠遠打量著這支奇異的外國艦隊,陌生、懷疑、好奇、驚歎、惶恐,議論紛紛。
舟山地處東海之濱,雖然不是開放口岸,但每年都有日本、朝鮮、荷蘭、琉球、越南和暹羅的商船從附近駛過,一旦天氣驟變,風高浪急,就會駛入港灣躲避海難,或者要求補充淡水和食物。
發現艦隊上的人偃旗息鼓,示以和平,一些膽大的漁民開始接近他們,兜售新鮮水果和蔬菜,艦上的官兵們面帶微笑、比手畫腳,以點頭或搖頭討價還價。漁民們見他們態度和藹、笑容可掬,便放鬆了警惕。
第一天,他們向英軍出售葡萄、蘋果、豆角和南瓜,第二天運去大量雞鴨、鮮蛋、活豬、活羊,那是航海者們最喜歡的新鮮食物。英軍支付的價格遠遠高於當地的市場價,漁民們賺得喜笑顏開,在岸上值守的清軍和漁民同樣放鬆了警惕,完全沒有想到戰爭近在咫尺。
在和平的偽裝下,英國軍官們仔細觀察和分析島上的軍事設施,水兵們在暗礁附近和潛流多變的地方敷設浮標。舟山漁民從來沒有見過浮標,滿心好奇地搖櫓圍觀,卻猜不透它們的用途,因為當地漁船吃水很淺,沒有擱淺或觸礁之虞。這一切偵測行動,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進行的,明目張膽,井井有條,平靜和諧。
經過兩天勘測後,伯麥和布耳利把衜頭碼頭確定為登陸點。第三天下午,「威裡士厘號」、「康威號」、「鱷魚號」和雙桅護衛艦「巡洋號」相繼駛入衜頭灣,悶聲不響地進入戰位。二十多條運輸船次第駛來,在衜頭灣附近下錨,船上載著三千八百名英印官兵。
直到這時,舟山的官員們才感到不對頭!定海知縣姚懷祥、定海鎮總兵張朝發與本地的文武官員們一起登上城頭,惴惴不安地注視著衜頭灣。定海城位於舟山西側,距離衜頭碼頭僅三里之遙。
張朝發是六十多歲的老軍官,長得人高馬大、虎背熊腰。他原本是臺灣鎮總兵,一年多前,原定海鎮總兵葛雲飛因為父親去世回家丁憂,他轉任定海鎮總兵。
姚懷祥五十多歲,一個月前從象山知縣轉任定海任知縣,對本地民情還不十分熟悉。他滿心憂鬱地說:「張總戎,舟山垂懸海外,八百里海域風波不定,常有日本、琉球和呂宋等國的商船遇風漂來,但是,紅毛番的這麼多兵船漂到本地卻是聞所未聞,我有種不祥之感。你在臺灣見過這麼多外國兵船嗎?」
張朝發狐疑地望著遠方的船隻,「姚大令,外國船遇到風暴漂到臺灣的情況年年有。我在臺灣時,有荷蘭兵船被狂風吹到基隆,要求靠岸買水買糧,還有葡萄牙和呂宋兵船因為風暴迷航,漂到臺灣,請求補充淡水、購買蔬菜。昨天我派了幾個人假扮漁民登船探望,夷兵們很和氣,還請他們喝外國紅酒。我估計是外國兵船被風吹散,迷航了,想在衜頭碼頭上岸,買水買糧買蔬菜,但他們不熟悉水道、不懂漢話,擔心撞上礁石或擱淺在沙灘上,只好瞎驢似的在海灣附近打磨旋。沒想到今天又來了二十多條夷船。」
姚懷祥道:「外國兵船駛入衜頭灣,引起百姓們的種種猜議,咱們還是過問一下吧,以免生出枝節來。」
張朝發同意,「也好。但是朝廷有章程,督撫提鎮大員不得與夷人直接交往。我是鎮臣,只好煩勞你帶幾個人去夷船看一看。」
姚懷祥轉頭對一個中年人道:「全福,咱們去一趟吧。」
全福應聲:「好。」他是定海縣典史 ,甘肅武威人,濃眉大眼,厚嘴唇厚胸脯,參加過新疆平叛戰鬥,因為作戰有功,晉升為典史。朝廷規定文官不得在家鄉任職,他就被指派到定海縣。
張朝發則對身旁一個軍官道:「羅建功,你陪姚大令走一趟,要仔細觀察夷船上有多少人馬、多少槍炮,問一問他們有什麼干求。」
羅建功是水師中營遊擊,聞令後靴子後跟一磕,打了一個立正,「遵命!」他右臉有一條疤痕,是與海匪打鬥時落下的刀傷,縫過七針,乍看之下像隻小蜈蚣。
姚懷祥、羅建功和全福一行出了城門,朝衜頭碼頭走去。他們在碼頭換乘水師哨船,駛向「威裡士厘號」。
「威裡士厘號」深艙巨舵,露出水面的船體又高又大,三支粗大的船桅高高聳立,兩側的炮窗全部打開,露出黑洞洞的炮口。姚懷祥和全福從來沒有見過如此龐大的兵船,忐忑不安地仰視著它。
羅建功數了數夷船的炮窗,多達七十四個!他的腦門子上全是詫異,定海水師的大號師船充其量只能安裝八位千斤小炮,同時發炮會震裂船體的卯榫。外國巨艦上有多層炮艙,安裝這麼多位巨炮,同時施放,船體如何承受得起?
幾個英國水兵放下舷梯,把他們彬彬有禮地迎上甲板。
一個身穿黑衣的人站在舷梯口,雙手抱拳行中國禮,講一口福建話:「艦隊司令伯麥爵士和陸軍司令布耳利將軍正在恭候閣下。」此人是郭士立,奉義律的命令擔任英軍先遣隊的通事,他根據補服和頂戴辨識出姚懷祥是舟山的主官。
兩位軍官向姚懷祥行西式軍禮。
「我是遠征軍艦隊司令伯麥。」
「我是遠征軍陸軍司令布耳利。」
姚懷祥行抱拳禮後,仔細打量。伯麥看來五十多歲,中等身材,寬額頭,尖下巴,天靈蓋上的頭髮脫落了大半,就像座禿了一半的小山,兩腮鬍鬚剛剛刮過,泛著黢青。身體很結實,深灰色的眸子閃著矜持。布耳利長著一雙鷹隼似的眼睛,鼻子略帶勾狀,臉頰佈滿捲曲的鬍鬚,穿一身紅色軍裝,黑色圓筒軍帽上有一顆亮晶晶的帽徽。
伯麥和布耳利也在暗暗觀察中國知縣。姚懷祥中等身量,山羊鬍鬚,紅纓官帽上有一顆素金頂戴,補服上繡著鸂鶒。眼神裡隱藏著驚異和困惑,但儀態端莊、鎮靜從容。
姚懷祥道:「本縣想打問一下你們來自何國?」
伯麥回答:「知縣老爺,我們來自英國。」
姚懷祥的心頭一動,英國就是不斷向大清輸入鴉片的國家!他迅速穩住情緒,「請問,你們來舟山是因為海上迷途還是另有所求?」
伯麥回答:「我們有重要事情相商,請。」他一展手,引著姚懷祥等人進入會議艙。
姚懷祥不卑不亢地撩衽坐下,羅建功和全福坐在兩側,幾個隨從站在他們身後。布耳利拿出幾只玻璃杯,斟滿酒,推到姚懷祥、羅建功和全福面前,然後與伯麥並排坐在對面,郭士立則居間翻譯。
姚懷祥看了看玻璃酒杯,酒汁呈綠色。
伯麥解釋道:「這是我國的杜松子酒,請品嘗。」
姚懷祥沒端酒杯,冷靜地問:「請問二位將軍,你們是想就地採買食物和淡水嗎?」
伯麥說:「我們寫了一份公函,本想派人送到貴縣衙門。既然知縣老爺親自登船問話,我們就當面交給你。」
在他頷首示意下,郭士立把一只大信套遞給姚懷祥,上面鈐著夷文紅泥封印。姚懷祥從信套裡抽出漢字公函展讀。
大英國特命水師將帥伯麥爵士、陸路統領總兵布耳利,敬啟定海縣主老爺知悉:
現奉國主之命,率領大有權勢水陸軍師前來定海,所屬各島居民,若不抗拒,大英國亦不加害其身家。
舊年粵東上憲林、鄧等,行為無道,凌辱大英國,國主特令正領事義律法辦。現今本國船隻及士兵,一切妥當,不得不行佔據。故此,本將帥統領招老爺投降,必須即將定海所屬與堡臺均降,致免殺戮。如不肯降,便用戰法奪之。
遞書委員,唯候半個時辰。俟諮覆不降,本將帥統領即日開炮轟擊島洲,並率兵丁登岸。特此致定海縣主老爺閱鑒。
廣東禁煙竟然禁出一場戰爭來!首當其衝的居然是定海!姚懷祥如遭五雷轟頂,受驚的臉皮變得煞白,手指尖微微打顫。他把公函遞給羅建功和全福,羅、全二人讀罷,唬得不知所措,眼珠子瞪得溜圓,好像要從眼眶裡蹦出來。
羅建功捏緊拳頭,恨不得一拳打出去,但他身在虎穴,不能造次,只能強壓著憤恨與怒火,「原來你們是來佔領定海的!」
伯麥輕輕搖動酒杯,綠色的酒液在裡頭優雅旋轉。他的眸子閃出不屑和陰冷的寒光,「很抱歉,本司令奉大英國主之命,先禮後兵,勢在必為!」這番舉止貌似文雅,實則咄咄逼人,就像剽悍的拳師向不入流的拳手提出要求,一點兒討價還價的餘地都不給。
會議艙裡的空氣萬分凝重,凝重得讓人喘不過氣來。
姚懷祥穩住情緒,指著公函上的「唯候半個時辰」道:「定海縣及周邊八百里水域是大清國土,版籍俱在,本官奉大皇帝諭令守土保民,出讓縣城事涉民瘼和國家版籍,不是半個時辰能定下來的。」
聽了郭士立的翻譯,伯麥和布耳利不約而同掏出懷錶看了看,與郭士立嘰裡咕嚕說起英語。郭士立拿過漢字公函查看,也講了幾句英語。
最後,布耳利轉臉解釋道:「知縣老爺,這是翻譯錯誤,我們的意思不是半個時辰,是半天。既然你說事關重大,不能馬上決定,我們可以等候。請你明天下午兩點以前,也就是貴國的未時二刻,給我們一個明確回答。」語速並不快,卻飽含殺機,讓人不寒而慄。
伯麥和布耳利敢毫不忌諱地把開戰的時間告訴對手,是因經過偵察與勘測,他們已經摸清清軍的兵力、陣地、戰船數量和火器配置,深信對手沒有任何準備,不堪一擊。除此之外,運載船隊剛剛抵達衜頭灣,也需要半天時間為登陸作準備。
伯麥的眸子閃爍著驕矜和自信,「我們大英國憑藉船炮之利威行天下,不打無把握之仗。我想請你們參觀一下本司令的兵船。如果你們認為能與我軍對抗,不妨試一試;要是覺得無力抗衡,那麼,識時務者為俊傑,貴軍不戰而降,定海軍民可以免受刀兵之苦,生命與財產也能得到保全。」
姚懷祥、羅建功和全福交換了眼神。羅建功頭一次登上外國兵船,負有偵察使命,順水推舟地道:「我倒想借機欣賞一下你們的兵船。」
伯麥微微一笑,「好,請!」他站起身來,引著姚懷祥、羅建功和全福離開司令艙。
到了甲板,伯麥對當值哨兵發下一道命令:「吹集合號!」
號兵把銅號吹得山響,四個鼓手把繃著鋼絲弦子的軍鼓敲得嗒嗒作響,六十個水兵像從船縫裡鑽出來似的,跑步來到甲板,迅速列隊成行,肩上挎著烏黑發亮的燧發槍。
接著,伯麥發出第二道口令:「上刺刀!」
哢哢一陣金屬相撞的鏗鏘聲,水兵們動作齊整,槍管上刺刀聳立,寒光閃閃。這是一場精心安排的表演,意在示以軍威,炫以軍技,不戰而屈人之兵。
姚懷祥腮幫子上的肌肉繃出幾道斜紋,他意識到,這是一支鋒牙利齒的強悍軍隊!
伯麥又道:「姚老爺,請你到駕駛艙看一看。」
姚懷祥一行人在他的指引下進入駕駛艙。伯麥指著一個輪盤,誇耀似的問道:「你們知道這是什麼嗎?」
姚懷祥從沒見過,搖了搖頭,羅建功和全福亦沉默無語。
伯麥回答:「這叫輪舵。它是一種重要的駕駛設備。貴國的船舵安放在艉部,使用垂直舵杆,舵柄轉角小,舵手的視線被甲板的建築物擋住,看不見前方。我們的輪舵安放在船艏,通過連杆和曲柄與艉舵相連,舵手站在船艏視野開闊,照樣能夠輕鬆操縱船舶。」
把輪盤安放在船艏掌控艉舵,聽起來如同天方夜譚,姚懷祥三人不僅沒見過,更沒聽說過連杆和曲軸,臉上一片懵懂。
「請三位老爺到炮艙裡看一看。」伯麥轉身引著他們沿梯而下。炮艙裡的卡隆炮排列有序,每個炮位後面整整齊齊碼放著球形炮子。
一個軍官見伯麥陪著中國人下來,雙腳一磕,發出一道口令:「立正—!」
全體炮兵皮鞋一跺,把船板跺得山響。
伯麥拍了拍炮管,炫耀道:「這是我們的艦載滑膛炮,可以發射三十二磅炮子,射程三千五百英尺,炸力一千二百千焦耳,能把你們的炮臺和堞牆炸得粉碎。」
聽了郭士立的翻譯,姚懷祥三人似懂非懂,他們對「滑膛」、「英尺」、「千焦耳」一點兒概念都沒有,但是,他們注意到英軍的炮子比清軍的炮子大得多。
伯麥發現自己在對牛彈琴,換了個較為形象的比喻,「我的意思是,這種炮可以打到你們的城樓上,把它炸得粉碎,而你們的刀矛弓矢、竹槍醜炮卻不堪一擊。」
羅建功壓抑不住內心的好奇,問了一句:「這麼多炮位同時開炮,不怕震裂船體嗎?」
伯麥翻起一塊木板,露出夾層,指著龍骨道:「軍官先生,我們的兵船有雙層船殼,鑄鐵龍骨,採用對角線支撐技術,即使所有巨炮同時施放,船體也不會震裂。而貴國兵船既小又醜,最多只能安放半噸重的小炮。說句不中聽的話,貴國兵船只不過是水上玩具。」
姚懷祥的臉色陰暗,完全被英夷的堅船利炮震住了。他雖然不懂軍事,但知道眼前的紅毛鬼子是群不速之客,一俟大動干戈,比豺狼還要兇殘十倍。羅建功和全福是行伍出身,雖然不懂這些現代兵器的奧妙,但深知自己的軍事實力遠不能與之抗衡,霎時腦子裡一片空白。
| FindBook |
有 10 項符合
鴉片戰爭 肆之貳:威撫痛剿費思量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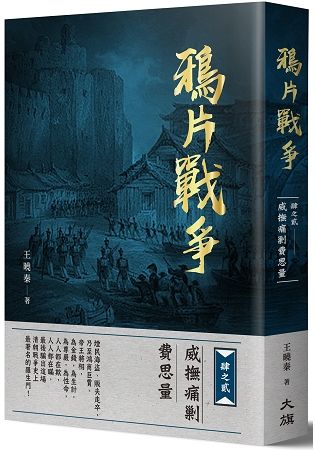 |
鴉片戰爭肆之貳:威撫痛剿費思量【金石堂、博客來熱銷】 出版日期:2018-07-15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鴉片戰爭 肆之貳:威撫痛剿費思量
【本書特色】
經過二百年的沉澱,這場戰役,早已退出英國人的記憶,卻依舊是中國人耿耿於懷的民族痛史,是什麼原因造成這等差異?憤怒,怨恨,悲傷,抑或是企圖遮掩內心濃濃的悔意?
專業引用海量中英兩國文獻成就的歷史小說,超過六十幅親眼見證動盪瞬間的畫作,
帶領讀者以帝相、軍民、官商的身分,以最自私自利的犀利角度,
見證一箱箱煙土,如何壓倒東方這條千年巨龍!
【內容簡介】
扣除勝者的餘裕,減去敗者的藉口,添加軍者的悲歌,增補商者的無奈,成就這部飽含詩意的民族痛史。
行商:「身為皇商,怎麼可能欠夷商錢,只是掛帳停息,分十六年還清。」
官員:「清朝關稅很便宜,就是手續費多了點,像是開艙費、押船費、丈量費、貼寫費,放關費、領牌費……」
將領:「英軍腿腳僵直,一仆不能復起,就是鄉間平民也足以置其於死地。」
道光:「英國人以肉為食,離了茶葉、大黃就消化不良,有一命嗚呼之虞。是朕懷柔天下,善待遠人,才賞你們一條活路。」
以上這些荒唐話,在道光年間,都被認定是真理,
如果不信,下場就是一個字──死。
被官憲層層剝削,拿不出錢卻又不能失了皇商的臉面,十三行只能撐;
上要賄賂,下要關照,左右還得交際應酬,官憲們只能詐;
開戰必定戰死,退守必定城破,皇旨「鎮」字壓頭,將領們只能欺。
或為金錢,或為尊嚴,或為性命,
他們不得不參與這場豪賭博弈,
贏了,就能活下來……
同時,輸去整個國家!
作者簡介:
王曉秦
高級教師。畢業於四川外國語學院,長期在內蒙古師範大學和北京印刷學院進行教學與研究工作。
多年來致力於文史類作品的寫作與研究;精通英文,善於挖掘國外的史料,並與中國史料進行對比研究,成果頗豐。出版過長篇歷史小說《李鴻章大傳》等七本著述和十本譯著(含合著)。
TOP
章節試閱
伍 大門口的陌生人
西曆七月二日,英國遠征軍的先遣隊繞過牛鼻水道,進入舟山水域。先遣隊是由四條兵船、兩條火輪船和兩條運輸船組成的,艦隊司令伯麥準將和陸軍司令喬治.布耳利少將都在這條船上。
伯麥畢業於普利茅斯皇家海軍學校,在拿破崙戰爭期間,參加了墨西哥灣大海戰和特拉法加大海戰,還參加過英緬戰爭。十五年前,他被派往澳大利亞。澳大利亞是塊新開發的不毛之地,人煙稀少,生存條件十分惡劣。他奉命勘測、考察澳大利亞北部和西部海域,繪製詳細的海圖。
伯麥血性耐勞,辦事果斷,思維縝密,是個頗有主見的人。英國政府中...
西曆七月二日,英國遠征軍的先遣隊繞過牛鼻水道,進入舟山水域。先遣隊是由四條兵船、兩條火輪船和兩條運輸船組成的,艦隊司令伯麥準將和陸軍司令喬治.布耳利少將都在這條船上。
伯麥畢業於普利茅斯皇家海軍學校,在拿破崙戰爭期間,參加了墨西哥灣大海戰和特拉法加大海戰,還參加過英緬戰爭。十五年前,他被派往澳大利亞。澳大利亞是塊新開發的不毛之地,人煙稀少,生存條件十分惡劣。他奉命勘測、考察澳大利亞北部和西部海域,繪製詳細的海圖。
伯麥血性耐勞,辦事果斷,思維縝密,是個頗有主見的人。英國政府中...
»看全部
TOP
推薦序
推薦序
史學家陳寅恪先生有「以詩證史」說,小說是廣義的詩,亦足證史。王曉秦先生這部新著《鴉片戰爭》,即是充滿詩意的歷史小說。他用如椽大筆,繪形寫神,潑墨重彩地勾畫出一幅鴉片戰爭全景圖:虎門禁煙,英酋遠征,突襲舟山,關閘事變,廣州內河戰火,廈門島上烽煙,浙江鏊兵,長江大戰,斡旋媾和,簽字《南京條約》等等。其場景廣闊,情節跌宕起伏,可驚可怖之衝突,可歌可泣之故事,紛至沓來,讓人不忍釋卷。
人物從中英兩國帝王將相,到鴻商巨賈、煙民海盜,乃至販夫走卒,個個刻畫生動,個性鮮活。
在宏大敘事中,作者激情迸射...
史學家陳寅恪先生有「以詩證史」說,小說是廣義的詩,亦足證史。王曉秦先生這部新著《鴉片戰爭》,即是充滿詩意的歷史小說。他用如椽大筆,繪形寫神,潑墨重彩地勾畫出一幅鴉片戰爭全景圖:虎門禁煙,英酋遠征,突襲舟山,關閘事變,廣州內河戰火,廈門島上烽煙,浙江鏊兵,長江大戰,斡旋媾和,簽字《南京條約》等等。其場景廣闊,情節跌宕起伏,可驚可怖之衝突,可歌可泣之故事,紛至沓來,讓人不忍釋卷。
人物從中英兩國帝王將相,到鴻商巨賈、煙民海盜,乃至販夫走卒,個個刻畫生動,個性鮮活。
在宏大敘事中,作者激情迸射...
»看全部
TOP
目錄
壹 明托家族vs大清帝國
貳 林則徐誤判敵情
參 東方遠征軍
肆 勸捐
伍 大門口的陌生人
陸 定海的陷落
柒 綏靖舟山
捌 浙江換帥
玖 隱匿不報的關閘之戰
拾 大沽會談
拾壹 紅帶子伊里布
拾貳 過境山東
拾參 癘疫風行舟山島
拾肆 浙江和局
拾伍 琦善查案
拾陸 鐵甲船與旋轉炮
拾柒 十三行籌資還債
拾捌 艱難抉擇
拾玖 互不相讓
廿 激戰穿鼻灣
廿壹 武力催逼
廿貳 虎門砲台臨戰換旗
廿參 騎虎難下
廿肆 中英兩軍弭兵會盟
廿伍 風影傳聞
廿陸 急轉彎
貳 林則徐誤判敵情
參 東方遠征軍
肆 勸捐
伍 大門口的陌生人
陸 定海的陷落
柒 綏靖舟山
捌 浙江換帥
玖 隱匿不報的關閘之戰
拾 大沽會談
拾壹 紅帶子伊里布
拾貳 過境山東
拾參 癘疫風行舟山島
拾肆 浙江和局
拾伍 琦善查案
拾陸 鐵甲船與旋轉炮
拾柒 十三行籌資還債
拾捌 艱難抉擇
拾玖 互不相讓
廿 激戰穿鼻灣
廿壹 武力催逼
廿貳 虎門砲台臨戰換旗
廿參 騎虎難下
廿肆 中英兩軍弭兵會盟
廿伍 風影傳聞
廿陸 急轉彎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王曉秦
- 出版社: 大旗出版 出版日期:2018-07-15 ISBN/ISSN:9789869656108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400頁 開數:25
- 類別: 中文書> 歷史地理> 中國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