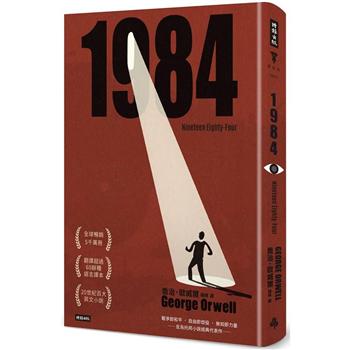前有英國的虎狼之師,後有鐵心剿夷的道光皇帝,
奉義侯琦善倒了,戰無不勝的老神仙楊芳也倒了,
究竟還有誰,能夠從英國炮口下拯救廣東?
抑或者該問,都到這般境地了,
有沒有誰,願意閉上滿口謊言的嘴,伸手把道光從井底拉出來?
扣除勝者的餘裕,減去敗者的藉口,添加軍者的悲歌,增補商者的無奈,成就這部飽含詩意的民族痛史。
更夫邊擊打梆子,邊喊著「平安無事囉——!」的喜悅尚在耳邊,
不想一字之差,中英弭兵會盟全面崩盤,和平之日似乎遙遙無期。
偏偏這當口,中國官員還在忙著自圓其說、摘清責任,
道光皇帝還在忙著抄家入官、調官換將,
誰也沒發現,英國最後的仁慈已然告罄,
一八四一年二月二十六日,戰火終於燃燒入境,
而這隆隆炮響,還將迴盪五百七十九天……
本書特色
經過二百年的沉澱,這場戰役,早已退出英國人的記憶,卻依舊是中國人耿耿於懷的民族痛史,是什麼原因造成這等差異?憤怒,怨恨,悲傷,抑或是企圖遮掩內心濃濃的悔意?
專業引用海量中英兩國文獻成就的歷史小說,超過六十幅親眼見證動盪瞬間的畫作,
帶領讀者以帝相、軍民、官商的身分,以最自私自利的犀利角度,
見證一箱箱煙土,如何壓倒東方這條千年巨龍!
| FindBook |
有 11 項符合
鴉片戰爭 :肆之參:海疆煙雲蔽日月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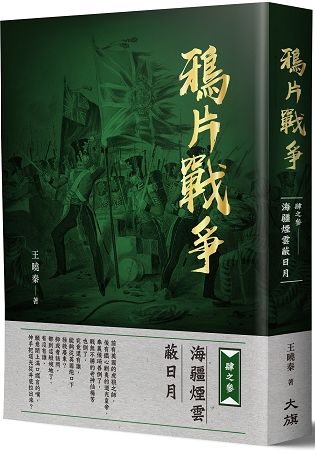 |
鴉片戰爭肆之參:海疆煙雲蔽日月 出版日期:2018-08-01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鴉片戰爭 :肆之參:海疆煙雲蔽日月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王曉秦
高級教師。畢業於四川外國語學院,長期在內蒙古師範大學和北京印刷學院進行教學與研究工作。
多年來致力於文史類作品的寫作與研究;精通英文,善於挖掘國外的史料,並與中國史料進行對比研究,成果頗豐。出版過長篇歷史小說《李鴻章大傳》等七本著述和十本譯著(含合著)。
王曉秦
高級教師。畢業於四川外國語學院,長期在內蒙古師範大學和北京印刷學院進行教學與研究工作。
多年來致力於文史類作品的寫作與研究;精通英文,善於挖掘國外的史料,並與中國史料進行對比研究,成果頗豐。出版過長篇歷史小說《李鴻章大傳》等七本著述和十本譯著(含合著)。
目錄
壹 抄家與出征
貳 虎門之戰
參 哀榮與蒙羞
肆 英中名將
伍 明打暗談
陸 兵臨城下之後
柒 盜亦有道
捌 聯手矇蔽聖聽
玖 靖逆將軍兵行險棋
拾 巨石壓卵之勢
拾壹 廣州和約
拾貳 三元里
拾參 刑部大獄裡的落難人
拾肆 炮癡
拾伍 斑斕謊言
拾陸 換將與第二次癘疫
拾柒 罪與罰
拾捌 他鄉遇故知
拾玖 夢斷中國與生死同盟
廿 水浸開封城
廿壹 廈門之戰
廿貳 天子近臣謹言慎行
廿參 驚滔駭浪
廿肆 文武鬩牆
貳 虎門之戰
參 哀榮與蒙羞
肆 英中名將
伍 明打暗談
陸 兵臨城下之後
柒 盜亦有道
捌 聯手矇蔽聖聽
玖 靖逆將軍兵行險棋
拾 巨石壓卵之勢
拾壹 廣州和約
拾貳 三元里
拾參 刑部大獄裡的落難人
拾肆 炮癡
拾伍 斑斕謊言
拾陸 換將與第二次癘疫
拾柒 罪與罰
拾捌 他鄉遇故知
拾玖 夢斷中國與生死同盟
廿 水浸開封城
廿壹 廈門之戰
廿貳 天子近臣謹言慎行
廿參 驚滔駭浪
廿肆 文武鬩牆
序
序
史學家陳寅恪先生有「以詩證史」說,小說是廣義的詩,亦足證史。王曉秦先生這部新著《鴉片戰爭》,即是充滿詩意的歷史小說。他用如椽大筆,繪形寫神,潑墨重彩地勾畫出一幅鴉片戰爭全景圖:虎門禁煙,英酋遠征,突襲舟山,關閘事變,廣州內河戰火,廈門島上烽煙,浙江鏊兵,長江大戰,斡旋媾和,簽字《南京條約》等等。其場景廣闊,情節跌宕起伏,可驚可怖之衝突,可歌可泣之故事,紛至沓來,讓人不忍釋卷。
人物從中英兩國帝王將相,到鴻商巨賈、煙民海盜,乃至販夫走卒,個個刻畫生動,個性鮮活。
在宏大敘事中,作者激情迸射,長歌當哭,把一部民族痛史演繹得迴腸蕩氣,著實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文學佳作,讀之不亦快哉。
好的歷史小說不唯文學性強、有可讀性,還必須有史學品質,即可以證史。這就要求作者具有三方面的準備:一要掌握充分的史料,二要目光如炬,有去偽存真的史識,三要獨立思索,對歷史有自己深湛的見解。
王曉秦先生是優秀的學者,研究並講授英國文學,學風嚴肅,已有多部學術著作面世。然其對清末災難頻仍的歷史情有獨鍾,二十年前即有「以詩證史」之夙願,欲揭示大清帝國崩潰之因由,以警後人。於是,傾盡心力廣泛彙集相關史料。
因其嫻熟英文,在國外得到許多國人罕聞的原始英文資料,且多具當時性和真實性,以是,其作品所涉及的時間、事件、人物、文獻、資料、插圖都有案可考,極具信史意義。如本書所配圖片,大多出自十九世紀畫家和參戰官兵之手,另一部分收集於中國、英國、美國、澳大利亞等國博物館和畫廊。這些圖片首次見諸國人,格外珍貴。在攝影尚不發達的時代,它們準確記錄了當時的事件,不獨可以以圖證史,亦可以增加閱讀的興味。本書史料的詳實,於此可窺一斑矣。
更值得稱道的是王曉秦先生的史見。他不崇權威,不墜時風,堅持獨立思索,敢於質疑曾經的歷史成見。在前幾年出版的歷史長篇小說《鐵血殘陽—李鴻章》中,他就洗刷了李鴻章漢奸、賣國賊的惡名。在學界雖有爭議,畢竟打開了一扇自由思索的窗。如今這部百萬字的新著中,思索的空間更大,識辨的問題更多,需要讀者去發現。
小說畢竟不是說教,乃以不說為說,陳述史實,以形象啟人,是禪悟的公案耳。讀這部小說,你會有傳統良史秉筆直書的感覺,這也正是作者的風骨所在。
歷史塵封在史料裡,不是人人願意翻閱;歷史要說的話,不是人人聽得懂;歷史默默地展示自己,不是人人看得透。這段話是作者的感言,猶如《紅樓夢》作者的一歎: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
史學家陳寅恪先生有「以詩證史」說,小說是廣義的詩,亦足證史。王曉秦先生這部新著《鴉片戰爭》,即是充滿詩意的歷史小說。他用如椽大筆,繪形寫神,潑墨重彩地勾畫出一幅鴉片戰爭全景圖:虎門禁煙,英酋遠征,突襲舟山,關閘事變,廣州內河戰火,廈門島上烽煙,浙江鏊兵,長江大戰,斡旋媾和,簽字《南京條約》等等。其場景廣闊,情節跌宕起伏,可驚可怖之衝突,可歌可泣之故事,紛至沓來,讓人不忍釋卷。
人物從中英兩國帝王將相,到鴻商巨賈、煙民海盜,乃至販夫走卒,個個刻畫生動,個性鮮活。
在宏大敘事中,作者激情迸射,長歌當哭,把一部民族痛史演繹得迴腸蕩氣,著實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文學佳作,讀之不亦快哉。
好的歷史小說不唯文學性強、有可讀性,還必須有史學品質,即可以證史。這就要求作者具有三方面的準備:一要掌握充分的史料,二要目光如炬,有去偽存真的史識,三要獨立思索,對歷史有自己深湛的見解。
王曉秦先生是優秀的學者,研究並講授英國文學,學風嚴肅,已有多部學術著作面世。然其對清末災難頻仍的歷史情有獨鍾,二十年前即有「以詩證史」之夙願,欲揭示大清帝國崩潰之因由,以警後人。於是,傾盡心力廣泛彙集相關史料。
因其嫻熟英文,在國外得到許多國人罕聞的原始英文資料,且多具當時性和真實性,以是,其作品所涉及的時間、事件、人物、文獻、資料、插圖都有案可考,極具信史意義。如本書所配圖片,大多出自十九世紀畫家和參戰官兵之手,另一部分收集於中國、英國、美國、澳大利亞等國博物館和畫廊。這些圖片首次見諸國人,格外珍貴。在攝影尚不發達的時代,它們準確記錄了當時的事件,不獨可以以圖證史,亦可以增加閱讀的興味。本書史料的詳實,於此可窺一斑矣。
更值得稱道的是王曉秦先生的史見。他不崇權威,不墜時風,堅持獨立思索,敢於質疑曾經的歷史成見。在前幾年出版的歷史長篇小說《鐵血殘陽—李鴻章》中,他就洗刷了李鴻章漢奸、賣國賊的惡名。在學界雖有爭議,畢竟打開了一扇自由思索的窗。如今這部百萬字的新著中,思索的空間更大,識辨的問題更多,需要讀者去發現。
小說畢竟不是說教,乃以不說為說,陳述史實,以形象啟人,是禪悟的公案耳。讀這部小說,你會有傳統良史秉筆直書的感覺,這也正是作者的風骨所在。
歷史塵封在史料裡,不是人人願意翻閱;歷史要說的話,不是人人聽得懂;歷史默默地展示自己,不是人人看得透。這段話是作者的感言,猶如《紅樓夢》作者的一歎: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
甲午戰爭百二十年紀念日於羊城四方軒遵囑 班瀾謹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