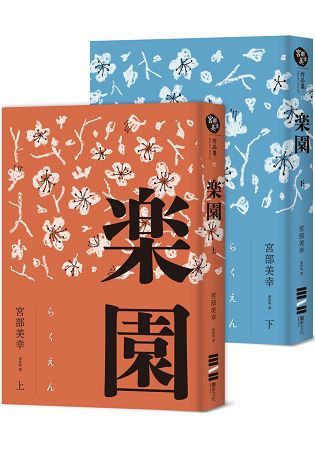人人都想進入樂園,
然而如果進入樂園的條件是必須捨棄摯愛的血親時,
又該如何抉擇? 【故事大綱】
歷經那樁慘絕人寰、震驚社會的連續殺人綁架案後,長達九年的時間裡,
前畑滋子一直活在那個案件帶來的陰影之中,無法面對自己和工作。
某日,一名遭受喪子之痛的母親萩谷敏子帶著獨子阿等生前留下的畫作前來拜訪滋子。僅僅十二歲便意外身亡的阿等有著令人驚艷的才能,然而作品中也有一些難以想像出自他筆下的拙劣畫作。其中一幅拙劣的畫作,竟然與他死後一個月才被媒體報導的死亡案件有許多不謀而合的地方。這也是阿等被認為可能擁有某種超能力的原因。
這場發生在和萩谷母子沒有任何淵源的東京老街的無名火竟燒出了案外案。多年前失蹤的不良少女──土井崎茜其實早已死亡,甚至被埋在家中的地板下。土井崎夫妻向警方自首,表示當年他們無力管教女兒,衝突之中動手殺了她。自此之後,土井崎家彷彿從未有過這個女兒似的,時間悠悠地過了十六年,直到案件時效過去……
活在母親哀思中的超能力少年。被父母刻意遺忘的不良少女。看似兩條平行線,因為一幅「不太正常」的畫作而有了交集。然而隨著滋子的追查,漸漸揭露出隱藏在土井崎夫婦背後晦暗的過去似乎還有更大的祕密存在……
土井崎茜到底是個什麼樣的少女,竟讓她必須死在父母手上?
萩谷等是否真有超能力,讓他可以看見那個早已死去的女孩?
滋子是否能真的找出兩個孩子背後的故事,並走出那個案件的陰影?
「我想知道那棟房子知道的一切。土井崎家為什麼選擇那樣的人生?
為什麼可以堅守祕密直至時效已過?為什麼萩谷等知道這一切?我想知道,我想解開謎底。」──前畑滋子
【名家推薦】
知名親子教養作家番紅花撰寫全新推薦文。
2017年改編日劇,由仲間由紀惠主演。
作者簡介:
宮部美幸
1960年出生於東京,1976年以《吾家鄰人的犯罪》出道,當年即獲得《ALL讀物》推理小說新人獎,1989年以《魔術的耳語》獲得日本推理懸疑小說大獎、1999年《理由》獲直木獎確立暢銷推理作家地位,2001年更是以《模仿犯》囊括包含司馬遼太郎獎等六項大獎,締造創作生涯第一高峰。
寫作橫跨推理、時代、奇幻等三大類型,自由穿梭古今,現實與想像交錯卻無違和感,以溫暖的關懷為底蘊、富含對社會的批判與反省、善於說故事的特點,成就雅俗共賞,不分男女老少皆能悅讀的作品,而有「國民作家」的美稱。
2007年,即出道20週年時推出《模仿犯》續作《樂園》。2012年,再度挑戰自我,完成現代長篇巨著《所羅門的偽證》。2013~2014年,「杉村三郎系列」《誰?》、《無名毒》、《聖彼得的送葬隊伍》接連改編日劇,2016年推出系列最新作《希望莊》。近著尚有《荒神》、《悲嘆之門》、《消逝的王國之城》等。
相關著作:《樂園(上)(全新修訂版)》《樂園(下)(全新修訂版)》《三鬼:三島屋奇異百物語四》《希望莊》《怪談:三島屋奇異百物語之始(經典回歸版)》《本所深川不可思議草紙》《獵捕史奈克(經典回歸紀念版)》《逝去的王國之城》《蒲生邸事件(經典回歸紀念版)》《悲嘆之門(上)》《悲嘆之門(下)》《哭泣童子:三島屋奇異百物語參》《荒神》《相思成災(上)》《相思成災(下)》《聖彼得的送葬隊伍(上)》《聖彼得的送葬隊伍(下)》《無名毒(獨步九週年紀念版)》《誰?(獨步九週年紀念版 )》《繼父(獨步九週年紀念版)》《落櫻繽紛》《所羅門的偽證Ⅲ:法庭(上)》《所羅門的偽證Ⅲ:法庭(下)》《所羅門的偽證Ⅱ:決心(上)》《所羅門的偽證Ⅱ:決心(下)》《所羅門的偽證Ⅰ:事件(上)》《所羅門的偽證Ⅰ:事件(下)》《附身》《忍耐箱》《暗獸─續三島屋奇異百物語》《天狗風─通靈阿初捕物帳2》《小暮照相館(上)》《小暮照相館(下)》《不需要回答》《英雄之書(上)》《英雄之書(下)》《怪談──三島屋奇異百物語之始》《顫動岩──通靈阿初捕物帳1》《孤宿之人(上)》《孤宿之人(下)》《終日(上)》《終日(下)》
譯者簡介:
張秋明
淡江大學日本語文學系畢業。結束十年上班族生涯後專事譯職,喜愛旅遊與閱讀。譯有:《父親的道歉信》、《回憶 撲克牌》(麥田)、《模仿犯》、《火車》(臉譜)、《雛菊的人生》(時報)、《有故事的昭和現代建築:東日本篇》、《愛沙尼亞 九日慢行:古城、森林、海邊葦草與尋訪鸛鳥蹤跡》(日出)等書。
章節試閱
那是在二○○五年五月中旬中午剛過的時候。一名嬌小的女子走在JR淺草橋車站附近的路上。
那是一條以一家專賣傳統人偶的老店而聞名的街道,附近也有許多的服飾、雜貨等批發店,在那一帶工作的人不少,年輕女孩尤其特別醒目。但是那名走在路上的女子顯然不屬於當地的人,像是來自外地,而且是頭一次造訪,一邊對不熟悉的街道感到困惑一邊尋找著目的地。
她看來年紀約五十好幾了吧?或許用「婦人」的稱呼會比「女子」更加恰當。
她穿著寬鬆的長袖襯衫,胸前扣子一絲不茍地直扣到領口,灰色的寬鬆長褲搭配著與其說是傳統不如說是設計稍嫌過時的黑色皮帶。由於身材臃腫,腰帶有些緊繃;腳上穿著舊運動鞋,鞋帶也顯得骯髒鬆垮。
左肩上掛著一個開口頗大、款式老舊的黑色肩背包,右手抱著紙袋,手上抓著白色紙片。那大概是前往目的地的地圖或是手抄地址吧。婦人時而東張西望,確認週遭的景色,時而抬頭觀望招牌,尋找顯示住址的標示。
沿著防護欄踽踽走在馬路上的婦人背後,跟著一輛亮著空車號誌的計程車。站在路中間專心看著手上紙片的她,被輕響的汽車喇叭聲驚嚇,連忙往路邊閃避。慢慢駛過的計程車司機臉上戴著墨鏡。今天是進入五月以來第幾個如此炙熱的炎日呢?
矮小的婦人打開肩背包取出手帕,擦拭前額和鼻頭,被陽光刺激不斷眨動的一雙小眼睛,透露出宛如大象般的溫和目光。
———大象這種動物,不管是野生時期還是被人類馴服飼養之後,眼神都不曾改變,始終都是那樣的安祥穩定。因為牠們很有靈性。據說找不到其他動物像牠們一樣的了。
那是幾年前呢?婦人的獨生子曾經說過這些話。那是兒子的朋友取笑說「你媽媽好像大象」時,他反駁的話語。兒子的朋友並非稱讚婦人的目光柔和,而是不懷好意地取笑婦人身材笨重有如大象。儘管如此,婦人的兒子依然滿臉笑容,甚至語帶驕傲地如此反駁。
踩著沒有自信的步伐,婦人的背影的確顯得動作遲緩,就像體型圓滾、柔順乖巧的小象一樣。若是向擦身而過的人們問起這名女子會是什麼樣的人,任何人都會稍微想一下後回答「總之應該是某個人的母親」吧?因為除了這個答案,很難想像她還能有其他的職業、境遇或頭銜。
事實上這個答案是正確的,只不過這名婦人的獨生子已經不在人世了。
走出車站的剪票口已然經過三十分鐘以上,矮小的婦人終於找到了目的地。她再一次確認手上的紙片,沒錯,是「金合歡大樓」,就在這裡的三樓。
那是一幢小巧的五層樓。雖然是出租的辦公大樓,門口出示的看板上儘管有五個空間,卻只貼出了三家公司行號的名稱。門扉不太乾淨的電梯位於外人不容易發現的深處,婦人沒有注意到,直接爬上了室外的樓梯。從她一邊扶著牆壁支撐身體,一步一步抬起膝蓋的上樓方式,可以看出其健康狀態。膝蓋的關節疼痛應該是婦人的老毛病。
婦人站在三樓狹窄的樓梯轉角調整呼吸、拭去汗水。她先將紙袋放在腳邊,檢查了一下全身上下,將頭髮梳整好,然後抬頭看著灰色油漆斑駁的鐵門,按下門鈴。
這裡的門邊設有掛公司門牌的欄位,上面掛著「諾亞出版有限公司」的門牌。在不影響開關大門的地方,放著一個有蓋的大型垃圾桶,桶身上貼著一張手寫的紙條。
(塞不進信箱的郵件,請放進這裡)
來訪的婦人在有人回應對講機之前,興味盎然地端詳著那張紙條和垃圾桶。
「來了,」對講機傳來回應,同時門也慢慢地開了。來訪的婦人更加蜷曲起圓滾滾的身體,很有禮貌地點頭致意。
「請問是萩谷女士嗎?」
前來開門、說話的是一名四十歲上下的女性。就女性而言,她算是高個子,身穿短袖襯衫和牛仔褲,一頭蓬亂的長髮隨意盤在後面,沒有化妝,腳上穿著室內拖鞋。
「是的,我是萩谷。不好意思,我遲到了。」
哪裡,妳不必在意。高個子的女性如此低喃後,將門完全敞開,招呼如小象般的婦人進入室內。由於室內的地板打掃得很乾淨,儘管對方說穿著鞋子進去沒有關係,但婦人不免還是很不自在地踮著腳走路。
房內滿是書架、書籍、報紙和雜誌,以及多半是這名沒有知識的婦人所不懂的各種有關書籍、雜誌等製造過程中所需的物品。眼前有五張桌子,其中兩張似乎只是用來作為堆放東西用的。從外面很難想像室內的空間如此寬闊,窗戶也很大,採光良好。電腦螢幕開著。除了出來應門的這名女性外,這裡的住戶或者該說是使用者大概外出了,看不見人影。
兩人面對面坐在設於房間角落簡樸的會客區裡。婦人從帶來的紙袋中取出點心禮盒,嘴裡不斷地道謝與道歉。
低頭致意的同時,婦人如大象般的眼睛迅速眨動,不是因為汗水沁入眼睛,而是淚濕了眼眶。
話說一個星期前。
某家雜誌社打電話給在這家「諾亞出版有限公司」上班的前?滋子。對方姓田口,是年紀比滋子稍小的一名編輯。兩人以前就認識,在滋子重回職場後又恢復往來,不過也只是偶爾打聲招呼的關係,沒有太深的交情。就這個業界而言,彼此知道聯絡方式卻沒有業務往來,是很平常的事。
「有件事想拜託妳,不是我們雜誌社的業務……嗯……應該也算是吧?」
說是希望滋子能和某人見面聽聽對方的故事。
田口所負責的雜誌既非女性雜誌也不是男性雜誌,或綜合雜誌,其發行宗旨是「為二十到三十來歲的東京人所編」。由於不是女性雜誌,所以不報導流行資訊;也因為不是男性雜誌,所以抽離了情色的要素。除此之外的內容則來者不拒,但又不像評論雜誌探討嚴肅主題。
該刊創刊之際,曾被讚頌是日本唯一不分男女性別的雜誌,但僅是如此程度的嶄新作法,實在很難從充斥坊間的各式雜誌、免費報中脫穎而出。後來發行份數每況愈下,老實說接到電話時,滋子還心想「哦,還沒停刊呀」。
「你的意思是說要我做個採訪嗎?」
「這個嘛很難說明清楚……」田口似笑非笑地說。「硬要說的話,也算是吧。總之我們雜誌社不能做什麼,於是想到或許前?小姐能夠幫上那個人也說不定。」
他說對方是因某起事件而來。
滋子從事文字報導的經歷很長,多半寫的都是適合女性記者採訪的家庭、教育、流行、旅遊等題材的報導。她最擅長的是職業主題,走遍全國各地採訪傳統工匠的系列報導連自己都覺得很滿意,甚至有人建議她出書。
當初如果聽從建議,現在的滋子說不定除了那本書,還會有其他幾本小作問世。而不管是否會被冠上報導文學作家的名號或是書暢銷與否,至少在業界還算是「工作穩定的文字工作者」,擁有一定的成績,頗受到信任吧。
可惜這樣的進程只因九年前牽扯到一個案子而整個變調。
沒錯,「只因牽扯到一個案子」。然而那件以女性為目標的連續綁架殺人案,犧牲者十指不能勝數。太多的生命被剝奪,也深深地傷害了倖存者的心靈。滋子和這個案件糾葛太深,一下子站在被害者、一下子站在殺人犯、最後又轉為告發人的立場,雖然能夠親眼目睹整起案件畫上句點,但相對地也承受了難以恢復的打擊。
會變成那樣的結果,不能怪任何人,問題出在自己過於輕率、準備不足、行動不夠謹慎。滋子自己很清楚,這件事不能責怪別人,只能怪罪自己。
也有很多人鼓勵她繼續寫下去。其中一人也是滋子最強力的支持者,就是她的丈夫前昭二。和老公的關係在連續殺人案方興未艾的時候,曾經一度破裂,好不容易又重修舊好之後,彼此感情比以前更加堅定。然而即便是心愛的老公不斷勉勵,也無法讓滋子重新振作起來。
有人勸她說為什麼不想開一點,只要不再碰社會案件、跟犯罪有關的題材,不就好了嗎?也有人開導說沒有必要為了一次痛苦的失敗就放棄全部吧?相反地也有人嚴厲斥責說放棄寫作就等於臨陣脫逃!他們說連續殺人凶手已經交由司法裁決,公審也開始進行中,繼續追蹤下去,仔細地觀察,留下文字紀錄,才是妳最好的謝罪方式、最負責的辦法呀!
不管是什麼樣的意見,滋子都無法順從。
她也嘗試過了,而且試過很多次。不管是社會案件還是其他題材,甚至連旁聽該案的公審,滋子都無法將紀錄寫成文字。滋子覺得很害怕,那股恐懼的陰風吹過心靈深處,影響之大超過了自己的預期。
除了法院要求出庭作證外,滋子是不會主動旁聽公審的。不知道是幸或不幸,滋子出庭的那一天,被告一開始就瘋言亂語,法官只好命令他退庭。儘管如此,滋子依然意識到被告席的空位,使得發言的過程中,好幾次痛苦地想要嘔吐,雙腳顫抖,幾乎都快站不住了。
輸了。已經難以恢復正常。不論是被斥責還是受到鼓勵都沒救了。自己的事業結束了。今後只能當個好妻子、好媳婦,甚至成為好媽媽。也許很沒責任感,很沒有骨氣,但已無所謂。滋子甘願如此接受所有的批判。反正我已經完蛋了,已經無藥可救了……。
不過即便是自己的人生,儘管已經下定決心也不見得就能如願。縱使夫妻感情圓滿、關係穩定,卻還是無法懷孕。兩人也去看過醫生,就是沒有結果。後來年事漸高的公公婆婆相繼病倒,只歷經短暫需要看護的時期便撒手人寰,繼承家業的丈夫扛起老闆職務後,自然忙碌了起來。過去從來沒有幫忙丈夫公司業務的滋子,如今就算想一起打拚,也不如打工的行政人員派得上用場。
結果每天就只能做家事等著丈夫回家。
因為時間太多,整天無所事事,漸漸地湧起了「想要工作」的心情。真是太隨性了!之前千方百計地就是想逃避責任,現在這又算是什麼?難道因為日子一久熱度降了,就開始覺得沒關係了嗎?開什麼玩笑嘛!不要太天真了。
肯定會被大家嘲笑怒罵的。何況,一旦真要提出重新成為文字工作者的想法,又有誰會提供工作機會呢?就在滋子半自暴自棄,抱著就算被拒絕也無所謂的心態問了幾個地方後,令人驚訝的是反應竟然不錯。
「花了好長的時間,不過太好了。歡迎妳回來。」有人如此安慰她;「就算是以後,妳依然會感到痛苦吧。滋子,妳會一輩子都活在那個案件的陰影之中,而且也沒有人可以代妳受苦。不過從事文字工作的人,本來就背負著那種宿命,雖然我們不像滋子的情況那麼受到矚目,但大家都是一樣的。」
我想繼續從事文字工作———當說出這個念頭時,丈夫也很為滋子高興。他說:這就對了,滋子,妳這樣做就對了。
「我的頭腦沒有妳好,不知道該怎麼表達。」失去父母,撥弄著明顯發白、剪成五分頭的短髮,他說:「滋子,我就知道總有一天妳必須再一次面對那件事。只是我也覺得受傷的心情應該永遠不可能回復。也許滋子活著的時候一直從事寫作,但直到生命結束也無法提筆寫出那個案件,不過只要繼續寫作,不就等於是一種面對嗎?這樣就對了。既然如此,我想就不會變成是逃避了。」
然後他又趕緊紅著臉補充說:「但也不是說不要忘了那件事。忘了也無所謂,我不是要妳太過執著。因為寫作是滋子喜歡的工作,妳只要繼續開始動筆就好了,什麼都不要多想,知道嗎?」
一種和事情鬧得正兇期間的夫妻吵架時、和解時、公婆出乎意料地早逝時都不同的情緒翻攪,淚水氾流過滋子的臉頰。
這麼說來,丈夫在那個案件剛落幕時好像也如此說過。滋子,妳有妳能做的事。如果有妳該做而又能做的事,妳就去做吧。不做的話,會丟女人的臉的!
其實一開始就知道初期的工作量不會太多,所以在家裡寫作。由於手上接的稿子是近年來成長迅速的免費報,寫起來倒也輕鬆。果然如事先預想的,大型雜誌社沒有來找滋子,滋子自己也無意主動上門。
後來是朋友開設專門編輯免費報的公司,詢問滋子願不願意簽約成為特約文案。滋子二話不說便答應,從此在「諾亞出版有限公司」有了自己的座位。那是三年前的事了。
說是免費報,可也不能小覷。既要做新產品的宣傳,也要採訪名人。性質則多是廣告資訊,因此滋子過去擅長採訪職業主題的經驗發揮了作用,現在甚至有人指名要她寫稿。
而今遞上名片時,幾乎不再有人會問「妳該不會就是那個前?小姐吧」。畢竟現代社會的變動很快,即便是轟動一時的重大案件,人們的記憶也逐漸淡薄。何況滋子並非主角,不過是個配角,而且還是丑角。世人並不如滋子預期地那麼緊盯著自己,早已不再關心那些陳年舊事了
那個案件的公審,一審共花了六年的時間才結束。判決結果是死刑。當然並非就此完結,被告又提出上訴,目前最高法院仍在審理當中。雖然媒體已不太關注了,但是在一審判決後曾有媒體以號外方式報導,由於被告的拘禁反應越來越嚴重,獄方考慮是否要做醫療上的處理。
拋開一審判決時的混亂心情不談,之後即使在滋子專心想做好家庭主婦的時期,還有剛開始恢復寫作的時期,不時總有記者之類的人彷彿突然想起似地跑來找她,不是要她「寫稿」,而是要採訪滋子本人。不管是什麼情況,滋子都很客氣地予以婉拒,直到進入諾亞工作後才有了轉變。
過去滋子總是回答「我已經沒有什麼好說的了」,不管對方如何死纏爛打,便將話筒掛上。然而現在不一樣了。
「不好意思,情況允許的話,這些東西我打算以後自己寫出來。」她會如此回答。
諾亞出版有限公司的社長,也是滋子長年以來的寫作同行野崎英治,第一次聽到滋子如此回答時曾說過:「嗯,看來這傢伙已經走出了隧道!」
然而這種不可以再逃避的覺悟和積極面對的宣言終究是兩回事。滋子的日常工作,就是平靜且穩定地受理諾亞公司內部的業務。因此她對這通電話突如其來的要求感到十分困惑。既然是社會事件,卻又說我可能幫得上忙,究竟是怎麼回事?
「對方名叫萩谷敏子,是個五十三歲的媽媽。」
那是在二○○五年五月中旬中午剛過的時候。一名嬌小的女子走在JR淺草橋車站附近的路上。
那是一條以一家專賣傳統人偶的老店而聞名的街道,附近也有許多的服飾、雜貨等批發店,在那一帶工作的人不少,年輕女孩尤其特別醒目。但是那名走在路上的女子顯然不屬於當地的人,像是來自外地,而且是頭一次造訪,一邊對不熟悉的街道感到困惑一邊尋找著目的地。
她看來年紀約五十好幾了吧?或許用「婦人」的稱呼會比「女子」更加恰當。
她穿著寬鬆的長袖襯衫,胸前扣子一絲不茍地直扣到領口,灰色的寬鬆長褲搭配著與其說是傳統不如說是設計稍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