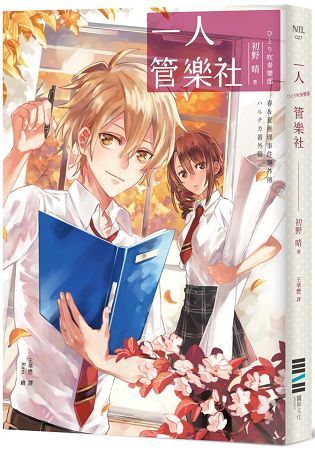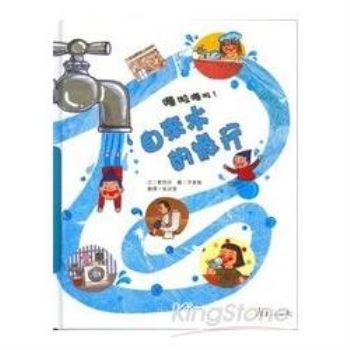奇妙的重逢
1
別以為父母和錢永遠都會在身邊。
上条春太
芹澤直子抬起特徵十足的細長眼睛,望著貼在社辦牆上的紙。以自來水毛筆寫著漂亮的字跡,悄悄釘在一堆獎狀和照片裡。之前,芹澤看到上条在思考社團的口號,隨口說了句「也幫我想一個」,希望能隨時鞭策自己,不輕易妥協。
這就是結果。惡狠狠刺進她最不希望別人觸碰的地方。
真是……
她的鼻子微微擠出皺紋,不太高興。這句話讓她想起,今早為了畢業後的出路和父親爭吵。
「這個月也好厭世。」
後藤站在旁邊一起看著。後藤是少數敢輕鬆向芹澤攀談的寶貴學妹。芹澤以為是在說她,嚇一跳。
「咦,什麼叫『這個月也』?」
「上個月是『男人只有兩種,懦弱的男人,和懦弱到不行的男人』。好像是一個叫河上什麼的人的名言。」
芹澤內心的悸動平息,「這、這樣喔……」
「上上個月似乎是『想求教生物社的烏龜,在這個艱困的世道活下去的祕訣』。」
那傢伙根本只是隨手寫下自身的苦惱吧?
「我懂了,那傢伙是白痴。」
「應該跟平常一樣,成島學姊馬上會撕下來。」
後藤在長桌鋪上毛巾,擺上低音長號,吹嘴對著自己。她以吹口管緣、喇叭口緣、主調音管支撐,避免重量壓在纖細的拉管上,調整成隨時可拿取的狀態,再打開盒子。這麼一提,今天的練習中,界雄的定音鼓和後藤的低音長號不光是悅耳,也十分賞心悅目。
星期六的社團活動在下午四點結束。整個上午都花在基礎練習上,中午隔一小時的休息,合奏完解散。三年級生已退出,社員剩下二十六名,但顧問草壁老師認為這個人數可仔細聽清每一個人的音。在老師細膩的指導下,人少反倒成為南高管樂社的優勢。
芹澤將單簧管收進盒子後,尋找穗村的身影。平常穗村總是幾乎要擒抱上來般邀芹澤一起回家,今天練習結束卻不見蹤影。
出去走廊一看,成島和馬倫走近,芹澤叫住他們。
「穗村同學呢?」
成島眼鏡底下的眼睛眨了兩、三下:「剛才跟上条同學一起,被地科研究社的人抓走了。」
芹澤想起地科研究社的社長,率領一群原本家裡蹲的學生的麻生。麻生那張有些冷峻的美貌,讓部分男生成為近似崇拜者的粉絲。坦白說,芹澤不太喜歡她。
「界雄呢?」
馬倫回望後方,回答:
「檜山同學還在音樂教室和美民(美國民謠俱樂部的簡稱,其實是重搖滾及重金屬同好會。成員目前全部身兼管樂社)的人在一起。」
不好打擾男生們聊天,芹澤低下頭說:「這樣……」
「要不要一起回家?」
成島邀約,但芹澤恭敬推辭。
直到不久前,她都是一隻孤狼。與夥伴一同經歷憧憬、哀傷、喜悅、痛苦──她害怕過度習慣與眾人共享這樣的陶醉。
偶爾一個人回家吧!芹澤在樓梯口換好鞋子,走向停車場。解開自行車鎖,踢開腳架。
時節已入秋。太陽下山得愈來愈早,芹澤踩著踏板,望著即將染上淡淡暮色的住家和行道樹。
加入管樂社後,她仍以星期一的鋼琴課和星期二的單簧管課為優先。鋼琴一對一課程最近剛換老師,今天是晚上七點開始,因此中間有一段不長不短的空檔。
芹澤想了想,將自行車掉頭。她用力踩踏板,朝鎮上的商店街前進。穗村雖然練習累到癱,卻老是跑去商店街閒晃,還發現一家很少人知道的厲害樂器行。芹澤有點羨慕她這樣的冒險。
當然,加入管樂社本身就是場大冒險。社團的管樂對報考音大沒什麼幫助,所以雖然大家都對她的社團活動表示包容,說她可以在比賽前參加就好,但芹澤想要盡量參與。
草壁老師曾告訴芹澤:不論是目不斜視地朝向音樂之路邁進,還是自我鑽研,都值得尊敬,但有不少人過度執著於音樂,落入窮途末路。追逐夢想以某個意義來說,是在自己的計算之中。而計算總有一天會變成算計,終至破滅。妳應該要把有限的時間拿來摸索妳的人生,而這個人生不是拋棄音樂,也不是在音樂之路上挫敗。
「意思是,叫我放棄成為職業音樂家嗎?」
「不是。」
「老師,那我該怎麼做?」
「趁現在開拓眼界。我認為妳選擇公立高中是對的。」
「我……不太懂。」
「記住,有時候總是在一起的人,會在某一天突然消失。」
「咦?」
「有時候以為天經地義的現實,會突然天翻地覆。」
「……」
「如果有一天妳的慣用手不能動了,而妳有知識、口才好,便可改行當教師或學者。我認識的音樂家轉換跑道,變成舞台監督和作曲家。他們絕非在音樂之路挫敗。因為他們依舊繼續身處音樂的世界。」
草壁老師這麼說,給了芹澤從未讀過的領域的書籍。他說在任何世界都是如此,只知道熱血蠻幹的英雄主義是很危險的。只想要抄捷徑,會失去想像力;但一直繞遠路,會失去目標。希望她能找到平衡,去感受往後的人生重要的那一面。學校就是學習這件事的地方。
芹澤以額頭承受著舒爽的風,踩著自行車踏板。
不知不覺間,她哼起喜歡的曲子。
在路肩寬闊的縣道輕鬆悠閒騎著。進入複雜的巷道後,沒有庭院的雙層連棟小住宅櫛比鱗次,其中有一家在管樂社蔚為話題的寢具行,長達十年都在倒店大拍賣。芹澤噗哧一笑。
她和一輛幾乎占滿狹小巷弄、直開進來的卡車擦身而過。開車的是界雄的父親,芹澤點頭打招呼。車身有被人拿硬幣刮出的傷痕。
太陽西斜,行人變少的馬路另一頭,有一家陰暗的小店。雖然是平房,但外觀是街上常見的住家兼店鋪。外觀極為滄桑,像歷經數十年歲月,芹澤煞住自行車。店頭擺著自動販賣機、冰品展示櫃和扭蛋機,店內雜亂陳列著各種糖果。
她的目光受到關東煮的廣告旗吸引。
那是什麼店……?
她想起還不到冬天,街上各處卻已賣起關東煮。穗村和界雄一聊到關東煮就停不下來,說小時候都吃關東煮當點心。吃關東煮當點心?芹澤不懂怎會有人這麼做。依他們的描述,高湯是黑色的,而且沾著味噌醬吃,不必擔心衛生問題或從什麼時候開始煮的。要是樂活族中的有機食物支持者聽見這番話,恐怕會暈倒。
店裡傳來「咚」、「鏘」等頗巨大的聲響,芹澤皺起眉,踢下自行車腳架、鎖好車,踏進小巧的店內。環顧一圈,只見塑膠容器裡塞滿貼有二十圓或三十圓標價的糖果、彈珠汽水和口香糖,每一種看起來都有害健康。但應該是吃這些東西長大的穗村,卻是個健康寶寶。
空氣的濕氣重,沒半個客人。
仰望垂掛的電燈泡,沒開。
芹澤正在納悶,像是代替櫃檯的展示櫃裡,無聲無息地冒出一個人影。那是白髮蓬頭、淡眉又三白眼的老婆婆,頭頂到眼睛之間的空白感令人印象深刻。老婆婆穿著淡褐色的裙子,撫摸脖頸。
芹澤內心有些驚恐,開口問:「呃,請問有關東煮嗎?」
老婆婆沒反應。
或許是重聽。芹澤提高音量,重問一次。
老婆婆默默伸出節骨分明的手指,指著外頭。要打烊了嗎?……芹澤死了心,準備離開,忽然發現前方有個附木蓋的方型鍋子,旁邊擺著一疊紙杯和紙盤。
老婆婆是指這個嗎?芹澤望向骯髒的告示。
關東煮三守則:
一、以串計價。一串六十圓。
二、撈了雞蛋要主動告知。
三、味噌醬只能沾一次。
紙張似乎貼了很久,細看快褪光的文字,約莫在說明是連二戰空襲都帶著逃走的祕傳高湯配方。「還有比搶救高湯更重要的事吧?」這樣的吐槽在腦中浮現又消失。
芹澤猶豫起來,但肚子竟在這時咕嚕咕嚕響,害她不禁臉紅。她走近方鍋,打開木蓋,水滴淌落,隔板之間塞滿一串串關東煮。從顏色來看,似乎已完全入味,但她預感可能煮過頭,味道繞了一圈,已進入新境界。最重要的是,居然有魚肉香腸,她頗為驚訝。
她挑選感覺不會吃壞肚子的料,拿了竹輪、蒟蒻、魚肉香腸放到紙盤上。鍋子裡有個小陶壺,盛滿疑似味噌醬的液體。
店門口擺著長椅,芹澤坐下,確定沒有行人,抓著竹籤吃了起來。高湯的顏色濃郁,她以為會很鹹,沒想到十分柔軟,淡淡甜味在舌頭上擴散。她咬一口沾上味噌醬的部分,滋味更香甜,升起一股讓全身溫暖的幸福感。
芹澤默默吃著。滿好吃的,或許可以拿來當成明天社團活動的話題。反正她不想見到吵架的父親,乾脆晚餐就地解決。芹澤又拿了魚板、黑色魚糕、油豆腐,狠下心撈第二顆蛋。
噗嗝……!不小心勉強吃太多,芹澤以面紙擦擦嘴巴。在紙盤上整理好竹籤,方便算錢,她走向老婆婆。
「多謝招待。」
因為毫無反應,芹澤看向老婆婆,只見她臭著一張臉。咦,在生氣嗎?難道我是在打烊前上門的不速之客?芹澤想快點結帳離開,說明自己撈了蛋,打開錢包,但沒零錢,只剩一張萬圓大鈔。
「啊,不好意思,我沒有零、零錢了……」
芹澤提心吊膽地遞出萬圓鈔票,老婆婆居然嘖一聲,她嚇一跳。老婆婆平板地說了什麼,捏著萬圓鈔,蹣跚走出去。約莫是找不開,去換錢,芹澤覺得做了很糟糕的事,坐在展示櫃旁邊的圓椅子,身體縮得小小的。
然而,不管再怎麼等,老婆婆都沒回來。
| FindBook |
有 10 項符合
一人管樂社(春&夏推理事件簿)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一人管樂社(春&夏推理事件簿)
打破幻想與現實之間高牆的魔法師──初野晴
超人氣「春&夏推理事件簿」番外篇‧翩然登場
好不容易喚來「相遇」的奇蹟,
如何才能笑著說「再見」?
不論是徬徨的夢想、終將分別的戰友、尚未萌芽的戀情,
解開你心中的謎團前,誰都不能輕言放手!
★融合《冰菓》的精彩校園推理&《吹響吧!上低音號》成長的苦澀與治癒
★日本暢銷60萬冊!連續入圍「日本推理作家協會獎」!
★影視化不斷!2016年改編動畫,2017年電影由《銀魂》美少女橋本環奈主演
橫溝正史推理大獎出道‧
打破幻想與現實之間高牆的魔法師──初野晴
超人氣「春&夏推理事件簿」番外篇‧翩然登場
【故事介紹】
「看來我跟妳,還是得在畢業前做個了斷。」
直到去年為止,都在廢社邊緣的南高管樂社,因著一個「將心愛的指導老師送上全國級音樂殿堂」的執念,宣告復活!昔日的青梅竹馬、現在進行式的情敵──穗村千夏和上条春太協議停戰,使出渾身解數,挖掘棲息於校園角落的奇才,聚集一群不可或缺的夥伴。今夏,他們在預賽舞台上傾注所有熱情,踏出夢想的第一步。
然而,秋高氣爽的天空下,摻雜寂寞的涼風吹拂,幾乎燃燒殆盡的成員,偶然與各自的剋星狹路相逢,這會是決鬥的信號?還是,一段美好關係的開端?
「暴衝小動物」一年級新生的朱里,偏偏拉著玻璃心的界雄,要替流浪狗找個家;
「孤狼」芹澤嘴饞買關東煮,卻被困在柑仔店,救命稻草唯有最看不順眼的學長;
「新任管樂社長」馬倫,懷疑戲劇社好友利用打工詐財,莫非死黨也有拆夥的一天?
「認真的結晶」成島,巧合翻開十年前的活動日誌,當時的管樂社只有一人……
我們偶爾會咬牙切齒,不給對方一記誠懇的上鉤拳不痛快,
但在青春的交差點上,多麼幸運彼此能夠同行。
總有一天草壁老師會離開,身旁的夥伴也只剩一年相聚的時間,
接下來南高管樂社會潰不成軍嗎?
希望每一塊細碎的相處切片,都會築起通往下一扇大門的階梯!
【來自作者的話】
十幾歲接觸的書籍、電影、音樂,往往會形成一個人的品味。在這段時光中,將所有注意力放在智慧型手機上,總覺得有些浪費呢。網路上能獲得許多資訊,但很難加深我們的思考,電視節目也有種種限制。然而,小說的世界不受類別,也不受表現方式的制約,頗有一讀的價值,我想傳達出這一點。如果覺得不夠有趣,請不用看到最後,接著拿起下一本書沒關係。等哪一天你需要這個故事,屆時再讀就好了。──初野晴
作者簡介:
初野晴
2001年參加橫溝正史推理大獎,首次投稿便進入最終審查;次年作品《水之時鐘》奪得大獎並於出版後正式出道。著作多冊,高中管樂社作為舞台的「春&夏推理事件簿」系列在日叫好叫座,一舉改編成動漫及電影,男女主角由佐藤勝利和橋本環奈飾演。目前已出版《退出遊戲》、《初戀品鑑師》、《幻想風琴》、《千年茱麗葉》、《行星卡農》,持續連載中。
初野晴不僅揹負作家身份,同時擁有正職,深知現實艱辛,希望在「春&夏推理事件簿」中為讀者帶來快樂,因此謎團不講求龐雜困難,重點在真相及人物成長與改變。他塑造人物時並非以「寫實性」為首要考量,而是「有這樣的人在身邊應該會很有意思」,創造深具趣味和特色的可愛角色。此外雖以校園當舞台,但描繪「非日常世界」一向是他作品主軸,巧妙藉著異想天開的謎團,將尚是高中生的視野延伸至全球局勢、社會議題及世界歷史,擄獲不分男女老少的讀者,為當今日本日常推理小說注入一股嶄新風氣。
相關著作:《行星凱倫(春&夏推理事件簿)》《千年茱麗葉(春&夏推理事件簿)》《幻想風琴(春&夏推理事件簿)》《初戀品鑑師(春&夏推理事件簿)》《退出遊戲(春&夏推理事件簿)》
繪者
Rum
自由插畫工作者,喜歡貓、茶飲和各種有特色的東西。
最近也在嘗試繪畫以外的領域,世界真是充滿挑戰!
http://rum3307.weebly.com/
譯者簡介:
王華懋
嗜讀故事成癮,現為專職日文譯者。近期譯作有《所羅門的偽證》、《邪魅之雫》、《渴望》、《再見,德布西》等。
譯稿賜教:huamao.w@gmail.com
TOP
章節試閱
奇妙的重逢
1
別以為父母和錢永遠都會在身邊。
上条春太
芹澤直子抬起特徵十足的細長眼睛,望著貼在社辦牆上的紙。以自來水毛筆寫著漂亮的字跡,悄悄釘在一堆獎狀和照片裡。之前,芹澤看到上条在思考社團的口號,隨口說了句「也幫我想一個」,希望能隨時鞭策自己,不輕易妥協。
這就是結果。惡狠狠刺進她最不希望別人觸碰的地方。
真是……
她的鼻子微微擠出皺紋,不太高興。這句話讓她想起,今早為了畢業後的出路和父親爭吵。
「這個月也好厭世。」
後藤站在旁邊一起看著。後藤是少數敢輕鬆向芹澤攀談的寶貴學妹。芹澤以為是在說...
1
別以為父母和錢永遠都會在身邊。
上条春太
芹澤直子抬起特徵十足的細長眼睛,望著貼在社辦牆上的紙。以自來水毛筆寫著漂亮的字跡,悄悄釘在一堆獎狀和照片裡。之前,芹澤看到上条在思考社團的口號,隨口說了句「也幫我想一個」,希望能隨時鞭策自己,不輕易妥協。
這就是結果。惡狠狠刺進她最不希望別人觸碰的地方。
真是……
她的鼻子微微擠出皺紋,不太高興。這句話讓她想起,今早為了畢業後的出路和父親爭吵。
「這個月也好厭世。」
後藤站在旁邊一起看著。後藤是少數敢輕鬆向芹澤攀談的寶貴學妹。芹澤以為是在說...
»看全部
TOP
目錄
〈波奇犯科帳〉長號閃亮女孩X打擊樂畏光男孩,該怎麼攜手替流浪犬找主人?
〈奇妙的重逢〉單簧管孤傲天才X小號浪子學長,天敵卻被迫待在一起四小時?
〈象形符號事件〉薩克斯風溫柔少年X戲劇社鬼才,害友誼破裂的果然是金錢?
〈一人管樂社〉雙簧管毒舌少女X 管樂神祕前輩,不孤軍奮戰的魔法存在嗎?
意想不到的組合,跨越彼此的「國境」,獻上最率真的歡樂和感動!
〈奇妙的重逢〉單簧管孤傲天才X小號浪子學長,天敵卻被迫待在一起四小時?
〈象形符號事件〉薩克斯風溫柔少年X戲劇社鬼才,害友誼破裂的果然是金錢?
〈一人管樂社〉雙簧管毒舌少女X 管樂神祕前輩,不孤軍奮戰的魔法存在嗎?
意想不到的組合,跨越彼此的「國境」,獻上最率真的歡樂和感動!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初野晴 繪者: Rum 譯者: 王華懋
- 出版社: 獨步文化 出版日期:2018-08-04 ISBN/ISSN:9789869660341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48頁
- 商品尺寸:長:210mm \ 寬:148mm
- 類別: 二手書> 中文書> 類型文學> 推理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