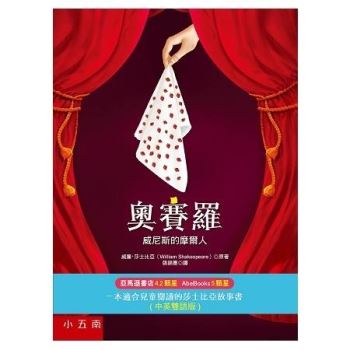40多年來,法國哲學家、希臘學學家和漢學家朱利安(François Jullien),運用了中國語言的思想資源,重新審思並拓展歐洲思想。迄今,他出版了40多本論著,這些書已被譯成25種語言。他所建構的哲思概念已在法國、歐洲以及歐洲域外產生影響,不僅在思想領域,也在其他領域:藝術創作、企業管理、精神分析等等……引發了眾多迴響。
「去相合」藝術與暢活從何而來
在兩邊上,隨著一條不明顯的線,這張圖並沒畫(請看年輕的畢卡索在巴塞隆納所畫的那張小圖)。在歐洲以前的繪畫當中已經有畫家留下沒畫的部分。然而這一次,整幅圖畫相較於它的畫布,顯得有落差:因為按照相合最初的——幾何——定義,線條或者表面是完全恰合的,但是這圖畫不再與畫布相合了(ne coïncide plus)。此處就還相當含蓄地透露了一種新的可能性,使之前的整座繪畫建築物開始衰弱:期待中的合宜銜接被拆解了,某種沒構想的意料之外的東西含蓄地湧現而存在。这就是「去相合」(dé-coïncidence)要開展的大能。
藝術家自此之後就堅持地實踐「去相合」。他們致力拆解「相合」力(coïncidence),這種相合力之前是藝術構作的核心,而首先就拆解「再現」的構作之相合力,揭發「再現」的構作是幻象:尊重形式和比例﹑透視法的要求﹑色彩之再造和一切產生相似的。然而,那不只是導入一個斷裂,從限制和規範裡自我解放出來,做出偏航或者確認某種異議;就是說,那不在於揭發某種因被懷疑是循規蹈矩的「相等」(adéquation)。「去相合」確實是一種上溯到更靠近製造了現代性的「湧距」(l’écart)出發之處的概念,並且在「湧距」的原則上照明了「湧距」。那凸顯出進入完美相等的「相合」是令人滿意的,甚至可以是一項英雄偉蹟;但是行不通的並且究竟是缺乏嚴謹要求的,「相合」既是矯作的也是毫無孕育力的。由此,「去相合」讓人重新聽見「coïncidence」的另一個意思,並且給予它合理性:純偶然的巧遇(「純偶遇」)而且沒有任何事物似乎可證明其合理性。在「coïncidence」那兩種相反的意思──偶遇或符合,偶然的或調整順應的──所打開的「間遊」(le jeu)當中,我們難道沒偵察出那產生藝術與暢活(existence)的更原初的可能性嗎?
正如「去相合」拆解了歐洲以前的藝術賴以建立(並且憩於其上)的「相合」(不過,偉大的畫家們倒是暗地裡感覺到「去相合」及其嚴謹要求,不是嗎?),「去相合」也同樣地拆解了那把真理看作(「物」與「心」)相等的本體論的工作。「去相合」還拆解了「順從大自然而生活」這種聖人之道的道德。現代性的確就安營在這個新起的懷疑之上,就是不再有「大自然」或「存有」作為可能載體和根本秩序。與之不同的,「去相合」乃針對一個不再具有「間遊」和「主動性」的合宜性,打開「湧距」;這是從一種井然有序當中抽身出來,該井然有序因填滿自己而阻擋了多種可能性並且造成貧瘠。相合就是死亡:相合是沈溺萎縮(enlisement),「去相合」反倒是推動(promotion)與脫展(dégagement)。
那提升為「人」者,早已與人的動物性(「人科」hominidés)從前的種種表現形式有了「去相合」,而且在面對他們之前的調適時(我們也許可以說通過「脫除調適」« ex-aptation »)導入了「湧距」。相合埋藏了人有意識的可能性,與之相反的,人的意識乃因「去相合」而能夠通過除掉附著去開拓它的能力──「禪」也運用這種作用。或者換個說法,那是經由與他所整合入的世界「去相合」來自我推動的主體。如果「ex-ister」正表示「挺身於……之外」(« se tenir hors »),它首先就表示挺身於形成世界的相合之外,亞當和夏娃正是因為被放逐而走出了地上樂園那完美相合的秩序,才開始以作為主體存在並且才可能進入一個歷史過程。如果「只有人可以暢活」,這是只要人可以與世界「去相合」,為了在世界裡面導入主動性或自由的餘地。藝術的任務,不是表達而是實現「去相合」。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去相合:自此產生藝術與暢活的圖書 |
 |
去相合:自此產生藝術與暢活 作者:朱利安(François Jullien) / 譯者:卓立 出版社:開學文化 出版日期:2018-08-31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160頁 / 10.6 x 17.2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149 |
法國哲學 |
$ 198 |
西方各國哲學 |
$ 198 |
社會人文 |
$ 225 |
西方各國哲學 |
$ 225 |
社會人文 |
$ 232 |
中文書 |
$ 233 |
西方哲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去相合:自此產生藝術與暢活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朱利安 François JULLIEN
François JULLIEN, philosopher, hellenist, and sinologist, is professor and chair of the Department of Oriental studies at Université Paris-Diderot and chair of alterity at the Fondation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 He is one of contemporary philosophy’s most widely translated thinkers.
朱利安是哲學家、希臘學學家暨漢學家,是巴黎迪特羅大學特級教授,也是巴黎人文之家基金會世界學研究院他者性講座教授。他是最常被翻譯成外文的當代思想家之一,其論著已經被譯成二十五種語文。
譯者簡介
卓立
國立臺灣大學外文系畢業,巴黎索邦第四大學比較文學博士。2000年代研究中國當代文學和臺灣文學(其論文收入France – Asie, un siècle d’échanges littéraires, 2001 ; Orient – Occident : la rencontre des religions dans la littérature moderne, 2007 ; Les belles infidèles dans l’empire du milieu. Problématiques et pratiques de la traduction dans le monde chinois moderne, 2010),近年來將其翻譯工作與研究結合,探究概念性詞彙的翻譯問題,特別以法國哲學家、古希臘學學家和漢學家朱利安為研究課題(其論文見於Des possibles de la pensée. L’itinéraire philosophique de François Jullien, 2015 ; François Jullien, L’Herne, 2018)。她所出版的多種翻譯作品當中有文學性的(如謝閣蘭的《古今碑錄》Stèles、佛樓定的《作家們》Ecrivains、舞鶴的《餘生》之法文版Les Survivants)、精神分析專論(如侯碩極的《犧牲:精神分析的里程碑》Le Sacrifice. Repères de la psychanalyse)、朱利安的哲學論著(如《淡之頌》、《山水之間》、《從存有到生活》等8種),以及多位法國漢學家的漢學專論的中文翻譯。除了在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圖書館任職之外,她也是巴黎人文之家「他者性講座」的合作研究員,並且負責「朱利安哲學基金會」(Fonds philosophique François Jullien)的聯絡工作。
朱利安 François JULLIEN
François JULLIEN, philosopher, hellenist, and sinologist, is professor and chair of the Department of Oriental studies at Université Paris-Diderot and chair of alterity at the Fondation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 He is one of contemporary philosophy’s most widely translated thinkers.
朱利安是哲學家、希臘學學家暨漢學家,是巴黎迪特羅大學特級教授,也是巴黎人文之家基金會世界學研究院他者性講座教授。他是最常被翻譯成外文的當代思想家之一,其論著已經被譯成二十五種語文。
譯者簡介
卓立
國立臺灣大學外文系畢業,巴黎索邦第四大學比較文學博士。2000年代研究中國當代文學和臺灣文學(其論文收入France – Asie, un siècle d’échanges littéraires, 2001 ; Orient – Occident : la rencontre des religions dans la littérature moderne, 2007 ; Les belles infidèles dans l’empire du milieu. Problématiques et pratiques de la traduction dans le monde chinois moderne, 2010),近年來將其翻譯工作與研究結合,探究概念性詞彙的翻譯問題,特別以法國哲學家、古希臘學學家和漢學家朱利安為研究課題(其論文見於Des possibles de la pensée. L’itinéraire philosophique de François Jullien, 2015 ; François Jullien, L’Herne, 2018)。她所出版的多種翻譯作品當中有文學性的(如謝閣蘭的《古今碑錄》Stèles、佛樓定的《作家們》Ecrivains、舞鶴的《餘生》之法文版Les Survivants)、精神分析專論(如侯碩極的《犧牲:精神分析的里程碑》Le Sacrifice. Repères de la psychanalyse)、朱利安的哲學論著(如《淡之頌》、《山水之間》、《從存有到生活》等8種),以及多位法國漢學家的漢學專論的中文翻譯。除了在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圖書館任職之外,她也是巴黎人文之家「他者性講座」的合作研究員,並且負責「朱利安哲學基金會」(Fonds philosophique François Jullien)的聯絡工作。
|